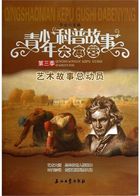十五
卢安远正和贱妹在灶屋里吃着晚饭,钱洪军跑了来说:
“安远,去打牌,去打牌。”
贱妹笑着说:“他还没吃饱饭哩,干啥这么急着去打牌?”
“是金宝叔急,不是我急。”钱洪军道。
“要急也得等安远吃饱饭啊!不然饿着肚子怎么打?”
“好,等他吃饱饭,等他吃饱饭。”钱洪军又说。
卢安远瞧向钱洪军:“你们想什么时候打啊?”
“再过半小时,再过半小时。”洪军说。
“时间还早哩。”贱妹又道。
“对,对,还早。”卢安远也说,把钱洪军拉到了火炉边坐下,和他亲热地谈起来。“你姐很快要走了吧?”
“是啊,可能过两日就走了。”
“她读完大学后可很久没回来了,干啥这次也要那么急着走呢?”
“怕她单位开除啊,不快走不行。”
“这样啊?”
“是的啦,人家有单位的人,哪象我们农村人这么随便呵。”贱妹插进话儿来说。
“是,不能随便。新莲她不能随便。”卢安远点点头。
他们又说了一阵话儿后,卢安远把饭吃饱了,就站起身来。
“走,现在我们去打牌吧。”
“是,我们现在去。”钱洪军也赶快站起身来说。
“你要不要带个火?”贱妹在背后问。
“不用了。”卢安远回答。
然后卢安远就和钱洪军一起离开了家。
儿子一不在家,贱妹的心中就会出现一种没有着落的感觉,就象原该饱满的正在灌浆的稻谷,因为缺少雨水的滋润,突然就干瘪、枯萎了,叫她干什么事儿都容易丢三落四。象现在就是这样,安远一出去,本来她还该吃半碗饭的,结果她却丢下自己的碗去收拾碗筷。可碗筷还没收拾完,她又跑出门口去往外望了,似乎要看看安远还在不在屋外。
“贱妹,你家安远出去打牌了呀?”杜淑青从她屋里走出来收她晾在门外的衣服,结果发现了贱妹,向她问。
“是啊,刚出去。”贱妹回答。
“唉,年轻人啊,就记着自己出去打牌,寻快活,就不知道在家陪陪妈妈。”杜淑青说。
“没关系啊。他想玩就由他去玩他的好了。他要陪着我他也闷呵。”
“那也总得陪陪。”
“不用了。”
杜淑青笑笑,收了衣服就进屋去了。
后来贱妹在火盘子四周搭起了一个比较高的木条架,将那木条架的每两根木条交接处都用草绳子绑紧,然后就将一些洗过还没干的衣裤围着那木条架挂在上边,就这样去烤衣裳。
烤了一阵,贱妹觉得自己肚子还不饱,便又坐回桌前去再吃半碗饭,一边吃她一边再走到门外,见不到儿子的影儿,她就由不得叹了一口气儿。
这时温桂珍悄没声息地从外边走了进门来。
“你怎么来了?”
贱妹看见她时既很吃惊又很紧张,由不得带上了戒备。
“我到你这儿来说件事儿。”温桂珍放低声说。
“要说你快说,说完马上走。”贱妹一边说,一边赶快去先关上门。
“是这样。”温桂珍套近乎似地凑近贱妹跟前说:“贱妹你人最好了,老实、本份、温柔、贤惠。现在你可要帮帮我,我已经两日没吃饭了。”
“你不是有儿子吗?他们不管你么?”贱妹道。
“他们哪管得了我,他们连自己都自身难保啊,谁还管我。”
“你家是地主成份,确实是很难。象你现在这样,给人看见也会给我带来很大晦气,别人以后会跟我过不去的,我都怕哩。”
“我知道这些,所以我就选了晚上的时间才来,没让人看见,这个你放心。”
“你知道我也没很多吃的。你要是向我要吃的呢,我也给不了多少给你。”
“随你给多少,只要你肯给我就行了。”
“我最多给你一斤半斤蕃薯、芋头啊。”
“米不能给吗?”
“我家一季米也分不到多少,自己都很不够吃哩。”
“你就给我一斤米吧,蕃薯、芋头我吃不惯。”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吃不惯蕃薯、芋头。”
“我是吃不惯。”
“吃不惯也要吃啊,难道你真的在没得吃时情愿去饿死么?”
“我不情愿去饿死。但我就是吃不惯。”
“那你就什么都得吃罗,吃不惯也要吃。”
“我吃不进。你还是给米我吧。我求求你,求求你。”
“唉,你啊你。我不帮你呢,你会说我没人情,摆架子;帮你呢,你又这么挑剔,要米不要蕃薯、芋头,害我自己都没好日子过——以后我还不知有没人抓我去游街示众哩……”
“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呢,你家只是中农,不是地主、富农,是属于贫农团结的对象。”
“难说哩。”
“不管怎样,还是求你给一点儿米给我吧,我吃米才吃得下饭啊。”
“我最多给你半斤米。”
“多也不给?”
“多我也给不出啊。”
“好吧,那你就给我一点儿米吧,另外再给我一点儿蕃薯、芋头。”
“行,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屋去拿给你。”
贱妹赶快走进卧屋去,给温桂珍舀来了半斤米和一些蕃薯、芋头,等把她打发走后,她看外边没人开门往外望,这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