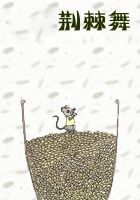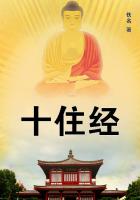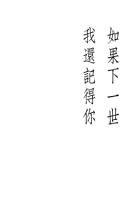0极世界·升起的天空
一夜星空。徐鲚站在吴老师的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寂静,朵朵云霞拼成完整的形体,那仿佛是给他第二次生命之人的面容。敬仰着凝视着,他对这熟识的脸孔说谢谢。
其实很多事情,只是没有勇气去迈出第一步,并非没有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某个方面的天才。
今后的日子里徐鲚很少发呆,也很少在自己不需要睡觉的时候强制自己入眠。但是,他始终也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那些拥有父母与朋友的人,还总是在种种场合呆滞和沉眠,就像当初一无所有的自己……
午后的艳阳把空气加热得活力四射,徐鲚和孙蔑一起去山上远足。登山远足对于海边人徐鲚可是新鲜事,所以他为这一天准备了满满一周的期待。
半山腰上,林木葱茏,溪水分流,偶尔飘飞的树叶闪耀着鲜亮的绿色落入水面,晕开一圈圈的波纹。谈天说地,环顾山色,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总能没有一秒钟倦怠地流动着,维持恰到好处的默契。突然,一群全身脏兮兮、头发凌乱的成年人从四面的树丛中咂着嘴围过来,圈住了两人之间的默契。
这是学校里的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虽然已经成年,个别甚至二十出头,但却只比徐鲚高两年级。也是说,他们被初中这个阶段刑事拘留了。
对于眼前这几个人,徐鲚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作为学校里资历最老的留级生,曾经为难过刚来的自己,可惜被一群过路的老师撞到。在这个战争年代,教师职业跟暴力机关只差着军事武装而已,所以后果可想而知。
凭借上次被保护的经历,徐鲚照葫芦画瓢一步上前,扬着理直气壮的脸说:“你们几个,上次还没得到教训吗?”旁边的孙蔑一听,顿时浑身哆嗦。上次?今时不同往日啊,我的优等生,难道能指望这种荒山野岭会跳出几个板着脸的老师?还过来对着一群顽固子弟谆谆教诲或拳脚相向?
徐鲚的博览群书是与世隔绝的,所以对于人与人的交流,他还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思维层次,只会套用已出现过的固定模式。
一如孙蔑能想到的,对面的人成了被点爆的炸弹。几个人二话不说,提起“家伙”就砸过来。孙蔑挡在前面强笑:“大哥哥,有话好商量……”结果话没说完就被推倒在地。体质瘦弱的徐鲚在后面挨了两棍,全身颤颤巍巍地向后退着,连站都站不稳。
一无所知的徐鲚大概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在他心中一群人提着棍棒围着几个人喘息如牛的情景只会在文字里出现。
脑袋嗡嗡响的时候,孙蔑已经站起来了,毫不犹豫地将高举棍子的成年人推倒在一边,用一口不切合年龄的语调叫嚷着:“他妈平常一副不知死活的嘴脸,我已经看你很不爽很久了。你还真以为你他妈把你早生出来几年就嚣张了?”话音未落,全场寂然,所有的人都木头了。因为以往低头做人、闷声闷气的孙蔑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稍后,徐鲚听见自己更加粗重的呼吸和高大的成年人站起来的声音。再稍后,他听见“咳——呗”地向着地面吐痰的声音,力气十足得像是把什么东西砸碎在地上。到最后,就是一群成年人张狂的笑如同那天的海啸一样轰击着自己的耳膜。
徐鲚不明白孙蔑想干什么,惊恐地去确认:“孙蔑?”
孙蔑转身拍拍徐鲚的肩膀,拉他起来,笑道:“你先去山顶吧,我跟这堆人有一笔账算了。等我放倒了他们我来找你。你留在这里会妨碍我的……但是别走得太快哦,兴许我动作快点还能追上你。”
“呀!原来你这么厉害。”徐鲚歪着头,惊讶地笑。周围的人很配合气氛地寂静了一下。
“当然,我父母都是军人。”孙蔑志得意满地宣布。徐鲚崇拜地仰起脑袋,重新发觉他比自己大上一岁,乐呵呵地回应过去笑容,信赖地挥着手离开。
“快点哦,我们要一起去山顶!”
“笨蛋,要撞树上了!看路!”
徐鲚走远,成年人的笑声也渐渐消停。刚才被推倒的人依然挂着先前的嘲笑,尽管已经没有了笑声。他凑到孙蔑耳边,悠悠地念叨:“你可真够仗义啊。自己一个人挨揍,让朋友先逃。”言语间,满是拷问勇气的威胁。
当然,此时孙蔑已经被钢管砸倒在地。成年人横眉竖眼,看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孙蔑,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要让他别走太快呢?这似乎和你的原意矛盾啊。”
孙蔑又恢复了低眉顺眼的样子,艰难地回答:“我说让他快跑,他反而会起疑心,尽管他是个笨蛋……可是你既然知道我装腔作势,那为什么还要放他走?”
另外一个成年人蹲下来,灼热的呼吸贴着孙蔑的脸:“好歹我们也和你在一个学校半年了,你有几斤几两我们不清楚?但是你要做英雄,我们当爹的,怎么会不成全呢?但是……”停顿了一下,成年人咧着一张嘴怪笑:“当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你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父母,啊?是不是?”话落,一群人围上去手脚并用。
“让你还能把死人搬出来?”
“你恨不恨他们啊?他们不是像你一样逞英雄,也不会需要你今天在这里逞英雄哈!”
“你恨不恨战场啊?你父母死的那里是战场,这里也是战场呐!这个世界已经到处都是战场啦——谁让你还敢去当英雄?!当英雄爽不爽啊?!”
徐鲚向着山顶走,沿途欣赏着平常不多见的风景,思绪却停泊在回忆中。
期中联考刚结束不久的课堂,放学铃声打响,所有人都先先后后地离开,只有他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教室,和被夕阳遗弃的光共处。这样不知已经是多少次了,在海啸以前的学校……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因为他不喜欢和同学们一起离开。别人回家的路途总有终点,而他却只是一直在外面游荡,饿了就买点什么吃吃,困了回教室里来睡。现在的他还没有寄宿家庭,就算有那也只是一个客栈,还不如睡教室……一如既往地,他独自坐在教室里,拿出一本似乎比他还要沉重的书……
“要一起回家吗?”一个清秀的男孩已经站在桌前,问道。徐鲚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就像所有的海水都粉身碎骨成了浪花。在他的生活计划里没有这条选项,因为从来没有同龄人会和他主动说话。一时间,局面尴尬,男孩怯声怯气地道:“对不起,打扰你了。”说完,男孩转身要走,像逃跑似的。那一瞬,徐鲚觉得他和自己很像,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口:“等等……那就一起走吧。”
两人漫步在昏暗的街道上,路灯所散发出来的微光似乎被夜色压得很低。两人从出校到现在已经有快一个小时了,却根本没有一句对话,就像是在漫无目的地瞎逛。突然男孩小心翼翼地问道:“徐鲚,你家在什么地方?”“家啊……你先说你家在哪吧,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徐鲚支支吾吾地应付,“我没有家”这种话他实在说不出口。
男孩的表情突然变得沉重,低声道:“我没有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但是徐鲚听起来却如雷贯耳。
没有太多隐瞒,男孩继续说道:“我叫孙蔑,是孤儿。晚上就睡在教室里。”说话的声音带着微微的哽咽,男孩的声音忽地提高起来,像是重重地吸了一下鼻涕:“哈——很久以前还有学生宿舍,现在学校都怕出事故,学生宿舍都拆了。”
徐鲚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去安慰,得到安慰的却是自己:“其实我也是孤儿……”然后他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停顿了一会儿,突然笑起来大叫:“太好了,终于有人陪我过夜了。”
孙蔑抬头看他,不敢相信:“真的么?”徐鲚点头。下一刻,两人抱成一团,脸上还带着忘我的笑。昏暗清冷的灯光打在他们身上,似乎变得温暖了……
徐鲚还在往山上走,他真不敢相信,那样的孙蔑居然深藏不露。突然间,他很好奇,想看看那些高个子被揍得狼狈不堪的表情。徐鲚稚嫩的心中闪过一个想法:“回去躲在树丛中看看。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会影响孙蔑发挥吧。”这么想着,徐鲚调头回折。
“这小子装什么死啊。”
“不会真出事了吧。”
“有那么脆吗?这两下就起不来了。”
高大的人们看着倒地不起的男孩七嘴八舌。领头的蹲下去,把食指放在男孩鼻口。“没气了。”他震惊地吐出这几个字,像是很费力。
空出几秒钟的寂静,接着有人惊叫道:“喂,还是快走吧。”一群人便窸窸窣窣地窜回了林子里。而树丛另一边,徐鲚全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躺在地上的,是满身血迹青斑的孙蔑。
此刻他完全不顾那些人有没有走远,疯了似的地冲出去,蹲下,伸手,抱起孙蔑僵硬的身体,愣愣地看着那张死灰般的面孔。然后,撕扯阳光的哭吼拉长在晴空下。
感觉,就像匕首,捅进心口。刺痛,毒素一样,经过所有血液可以流过的地方——海啸又来了。
——为什么还是这样?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人,渐渐离我而去,让我再一次接近……一无所有。
——海啸,我没有办法;这些人,我还是有办法的……可为什么,我还是什么都留不住,就连自己也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堕入,一次又一次地下坠。
——企图拯救我的人,和我一起……堕坠?
徐鲚沉着脸,双眼隐没在烈日的阴影中。他听见有人在吼叫,他听见步子踩碎树叶和灌木的细密,他听见自己蕴含悲伤的冷冷的声音:“杀了人……就想走?”一个一个的字都仿佛冻成了坚冰,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坚强地屹立着。
“喂——这里是山上,慌什么?他也死了,就谁也不知道。”成年人站在早就移换了的场景里,“一起上!谁让他看见了,还抱着尸体追上来!”他们指着身前的徐鲚喊叫,于是所有人一拥而上。
钢管和棍子举起来的声音,呼吸提起来的声音,有人冲过来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穿透在徐鲚的脑海里。果然鱼类比人类更能体会声音,但人类又是生活在脑海里的鱼类。徐鲚此刻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鱼,看不到没有水的世界发生着什么,只有愈加清晰的声音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脑海中穿梭不停。
乱棍即将临身,浮空的水流似乎是从自己脑海里翻卷出来的,就像那天的海啸。没有夺走自己生命的它们,出现在周围形成了巨大的壁障。所有的嘈杂都被这层壁障隔开了,人类的喧闹在自然的咆哮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徐鲚垂着头,慢慢走,眼中蕴含着饱满的杀机,寒声道出陌生韵调:“汝等人渣……当除!”
话音刚落,海的舞蹈仿佛在执行他的意念,从壁障中分离而出,雀跃着欢腾着奔向“当除”的对象。几个人被水花卷上天空,映接白云;另外几个人被揉进粗糙的树干里,四分五裂。他们和地面亲吻的时候,鲜血以白骨为茎开出了漂亮的花……
还剩一个人!深海鱼类一样的徐鲚能通过呼吸声判断他的存在,然后像个没有灵魂的死尸一样摇曳着躯体逼近。而这时的幸存者已经成了一尊凝固在恐惧中的雕塑。终于,水浪将它冲入了溪流里。
“呜啊”他浮了上来,大口喘着粗气,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然而溪流也是海的一部分,水像疯长的植物一样将他缠住,只留出头在外面。下一刻,水压将他的身体扯得支离破碎。仅仅完好的头颅被高压抛上晴空,鲜血成了缝补破碎的线,密密麻麻地织在溪流和天空之间。
最终,那颗头颅带着凝固了的恐惧坠落,夕阳透过飘洒在空气中细密的血珠照耀这红侵的溪流、赤染的大地——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海啸安分地回到了脑袋里,徐鲚又重新回到陆地上生存。他失落地背着受伤的同伴走向山顶,动作僵硬,像是一具器械。他坚信他只是受伤。
山顶上,冷风吹乱了徐鲚的头发,但他却无意理睬,涣散的目光愣愣地望向远方的晚景。残日映着血色的余晖沉入地平线,落叶带着沉闷的颜色飘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孙蔑,我们已经在山顶了……”
黑暗覆压着一切的轮廓,渐渐笼罩过来,像是给这个凄艳的舞台落下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