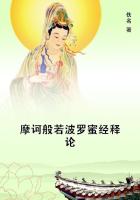李耳没有回答尹喜和文子的问话,而是陶醉在范蠡写的帛书中,边看边摇头晃脑地大声念道:“……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真是写得太好了!”
尹喜走过来,伸头望着帛布道:“写得是不错,这不正和老师您前些日子给我说过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同出一辙吗?”
“你瞧瞧,下边说得更好。”李耳又大声念道,“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长。柔而不屈,强而不刚。”
文子纳闷了,这么远的路程,又没有通信,两个人的看法怎么会完全相同呢?“范蠡怎样抄老师的话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连连摇摇头,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
“这叫耳听、心听和神听?”李耳望着文子疑惑的神情,又解释道,“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蓄,内意盈并,得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之之。”
李耳话音刚落,文子就从衣襟下取出刻好的木简,称赞道:“老师,您说得这段话太精彩了!我全给速刻了下来,您看有没有刻错?”
李耳真是佩服文子的这道绝活,看了一下,一字不拉地全刻了下来。“我刚才说过了,对待学习有三种态度,那就是耳听、心听和神听。你俩能不能讲个这方面的故事,算是领会了我这个精神。”
文子首先讲了起来,他讲范蠡过去在卢氏如何行医和收集整理《卢氏本草经》的事,李耳点头称是,连连称赞范蠡对待学习是“神听”。
临到了尹喜,尹喜一下说不出来,用手抓了抓头发,“这样吧,前些日子我到郑国,听我的好友列御寇给我讲过造父习御的故事,我看造父就是神听。”于是他讲了起来:
造父刚开始跟随老师泰豆氏学习驾车时,对老师非常有礼貌。泰豆氏过了三年也没有教给他驾车的技术,但造父对老师却更加有礼貌,更加恭敬。泰豆氏这才告诉造父说:“古诗云:‘擅长造弓的人,一定要先学会造簸箕;一名优秀的冶铁匠,一定要先学会缝皮衣。’你先看我是如何快步紧走的,然后再学我那样快步走,掌握这一功夫后,就可以手握缰绳,驾驭六匹马了。”
造父回答道:“我听您的。”
泰豆氏便在地上竖了很多木头,作为道路,每根木头仅可容得下一只脚,并按驾车步伐的设计竖立木头的位置,让造父踩在木头上行走。
要求他来回快步紧走,而不失足跌倒口造父学习走这条木头路,三天就完全掌握了这种技术。
泰豆氏赞叹道:“你真是太机灵了,竟掌握得如此之快。大凡会驾车的人也都是这样的。早先你在木头上行走,脚步怎样迈动,心就怎么相应地运动。把这个道理推广到驾车上,要使马走得整齐而协调,就要掌握好马缰绳和嚼口的技术,勒得缓慢要适中,既要在心中掌握好调整马的速度,还要支配好你握缰绳的手,与之密切配合。这样才能在内得之于心,而在外也合乎马的脾气,因而能使马车行驶起来进退合乎标准,旋转拐弯合乎规则,上路跑向远方的目的地,而气力还绰绰有余。真正谙熟驾车技术的人,应该是得之于马嚼口,而应之于马缰绳;得之于缰绳,而应之于手;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的。能做到这样,那么驾车时就可以不用眼睛去看,不用马鞭去赶马;而是心中悠闲自在,身体端端正正,手中的缰绳不乱,而且二十四只马蹄没有一点差错,回旋进退,一举一动都合乎音乐节拍。然后即使车轮在外面,再也没有空地可容车轮;马蹄之外,再也没有余地可容马蹄,也不会感到山谷如何险阻,原野如何平坦,这在驾车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我的驾车技术讲完了,你记住吧!”
在尹喜转述完列御寇收集的“造父学车”的故事以后,又引起了李耳对列御寇的回忆。他对列御寇非常熟悉,有一年深秋,列御寇去看他,只见列御寇穿着像叫化子一般的衣服,两个袖子像被狗咬过,紊紊拉拉掉着,裤子也破了,露出流着血的膝盖。李耳见了实在于心不忍,就找了一套衣服送给他,他道谢一声便穿上了。李耳看他饿得面黄饥瘦,又端出食物给他,谁知他只吃了半饱,就把食物收放到一个竹筒里,说道:“这顿不能吃得太饱,给下一顿留些吧!”他收拾完食物,又向李耳伸手。李耳当是食物不够,又想取些给他,被列御寇挡住,“我要的不是食物,我要的是——”他指了指李耳的口。李耳恍然大悟他知道列御寇有一个习惯,哪怕觉不睡,饭不吃,只要给他讲个故事,他马上就会记下,而且把它看得比吃饭和穿衣都珍贵。李耳便说:“我知道你是个故事篓子,你先给我讲个故事,我再给你讲。”于是,列御寇舔了舔嘴角,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学艺的故事:
列子拜老商氏为师,与伯高子交友,学得了二位先生的道术,驾御风云返回。有个名叫尹生的人听说了,便去伴随列子居住,好几个月都不回去探望自己的家园。他趁机向列子祈求道术,跑了十回,但十回都得不到列子的真传。尹生满腹怨恨,请求离去,列子又不表示意见。尹生返回家中,过了好几个月,他想学道的念头实在难以打消,于是又前去跟列子。列子问:“你为什么来来去去这样频繁?”
尹生回答道:“以前我向先生请教,您不肯相告,我当然对您心怀不满。现在我的怒气消了,因此又回来找您啦。”
列子道:“从前我还以为你通达事理,没想到现在你竟浅薄到这种地步?坐下,我要告诉你我从先生那儿学来的东西。自从我事奉先生,与伯高子为友,三年之后,心中不敢存念是非,口里不敢言说利害,才得到先生斜看一眼罢了。五年之后,心中转而有意识地思考是非,口里转而有意识地言谈利害,先生才开始松下面孔对我笑笑。七年之后,任凭心中所想,更加没有是非,任凭口里所说,更不涉及利害,先生才开口让我和他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放纵心思去想,放纵口头去说,也不知道我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也不知道别人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也不知道先生是我的老师、伯高子是我的朋友,内心的存念和外界的事物一切都穷尽了。”
“这以后,我的眼睛作用像耳朵,耳朵的作用像鼻子,鼻子的作用像嘴巴,全身各部位没有什么不相同。于是心意凝聚,形体消散,骨骸血肉与自然融为一体,感觉不到身体所倚靠的,脚下所踩踏的,任凭风吹而东西飘荡,就像一片树叶变成干枯的谷皮一样,竟然不知道是风乘着我,还是我乘着风呢?”
“而你如今在我的门下求学还没多少时问,就再三地怨恨遗憾。这样的话,你小小一个身躯灵气也不能接受,你短短一节骨头土地也不肯承载,想要乘风凌空,怎么能办得到呢?”
尹生听罢,十分惭愧,好久连大气也不敢出,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李耳在尹喜刚把“造父学车”的故事讲完,就接着把列御寇学艺的故事续着讲。他讲完后加重语气道:“我看列御寇学艺的事,正是由耳听、心听到神听的。你们两个说是不是这样?”
“是的!”尹喜和文子都点头称道。不过仍觉得老师既然说出学习的“耳听、心听和神听”的经验之谈,一定有他亲身的体会,不然不会这么深刻而富有哲理。于是,两个人又问:“老师,您能不能把您学习耳听、心听和神听的故事给我们讲讲?”
“我过去那学习的事,早成了陈芝麻烂豆子,不值一提了。”李耳拉着自己的白胡子,在牵(谦)须(虚)!
这话一下提醒了尹喜,他马上从桌子上拿起自己过去整理的《李耳随行录》道:“我刚才真是舍本求末,这上面不是记着老师的神听之事?”又对文子说,“我念几段,你听听。”
七岁的李耳就要离家到较远的书塾去读书,他妈妈益山女别提有多难过了。一大早起来,她就为儿子烙煎饼、煮鸡蛋、缝书包,当这一切都做好后,准备去叫李耳起床吃饭,可是一想到这些天来,真把他忙坏了,就让他再多睡一会儿。等了好一会儿,看着太阳老高了,心想再不叫,恐怕赶路就来不及了。谁知她刚站起身来,就见李耳背着一捆草回来,连忙上前去接,嗔怪道:“谁叫你早上起来去割草的?”
“我要去上学了,也不能让妈妈太辛苦!”李耳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我就割点草喂牛,替妈妈减轻一点负担。”
“真是我的好儿子。”益山女放下草捆,拉着儿子的脸亲着,眼泪不由得掉了下来。真是穷人冢的孩子早当家,这么小就知道疼爱妈妈了。
李耳看到妈妈哭了,连忙用手给妈妈擦眼泪,“妈妈,我上学去后,您在家里要注意身体,要是累得实在干不动了,就等我抽空回来帮着您干。”
“孩子,你上学时千万不要挂念在家的妈妈。”益山女拉着李耳的手叮嘱道,“上学可是你这辈子的大事,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多识几个字,就等于帮着妈妈在家干了一件大事,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李耳朝妈妈重重地点了点头,娘俩吃过饭就上路了。
益山女带着李耳走过两个村庄,前边就是他姨妈益今今联系的那家书塾了。谁知这时天突然变了脸,刮起了暴风雨,益山女就拉着李耳跑到附近的一栋屋檐下避雨。原来这是一家书塾,一位老先生正领着十几个学生在作诗。墙壁的石板上写着题目《风雨》,这位老先生正摇头晃脑地写着他吟出的诗,在做着示范:
风吹涡河千层浪,
浪浪波涌百花撒;
雨打沙洲万点窝,
窝窝垒起十堆沙。
老先生对自己作的诗十分满意,脸上不断露出得意的神情,用手指着石板解释着,学生们都异口同声赞颂老师的诗作得好。
李耳虽在外檐下避雨,一听到读书声就深深被吸引住了。他睁大眼睛朝屋内的石板上看去,看着看着眉头紧皱起来,伸出右手蘸着唾沫在自己左手心划着,划着划着不由得脱口而出:“这首诗作的不对,我要给他改改!”说着就要冲进屋里。
益山女赶紧拉住他:“你这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老师作的诗能改吗?”
李耳挣脱了妈妈的手,“他作的不对,为什么不能改?”
“走!”益山女狠狠地对李耳下着命令,“快走,不然你就要在这里闯乱子了。”她强拉着李耳要走。
李耳噘起小嘴,拖着屁股不走,“妈妈,您这是怎么了,难道上学看到不对的诗就不能改吗?”老先生听到屋外有人喊闹,走了出来。看到这个孩子清秀端正,气宇不凡,刚才说的话,他也全听到了,就问:“你说这诗作的不对,需要改动,你敢改吗?”
“怎么不敢改?”李耳蹭蹭走进屋内,拿起石笔,伸手就去改诗。由于个子低,手怎么也伸不到写诗的地方,于是就从屋外搬了块石头,垫到脚下,才够得着改诗。片刻他把这首诗改成:
风吹涡河重重浪,
浪浪波涌层层撒;
雨打沙洲点点窝,
窝窝掀开粒粒沙。
老先生被这孩子勇于改诗,而且改得这么好所折服,连忙拱手问道:“你说为什么要这样改?”
“您这首诗,写得太实了。”李耳伸手指着改动的地方,“您把千、百、万、十嵌进诗中,本意是不错的。可是要有人按数字去数,您能说准确吗?何况诗要给人以想象的余地,不能写的那么死。老师,您说我用重重、层层、点点、粒粒代替数字好不好?”李耳这时瞪着浓眉下的问号眼,骨碌碌转着,“改得不对的地方,请老师指出!”
“改得非常好!”老先生击节称赞,“没想到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文采,真是不可思议,何况你还有这种敢于改老师错的精神!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能这样做。了不得!了不得!”于是,详细询问了李耳的情况,李耳如实作了回答。
在一旁的益山女连忙向老先生谢罪道:“老先生,这孩子不懂事,冲撞了您,请您不要见怪。”她拉着李耳要走,“他是狗咬星星,不知稀稠:”
老先生从益山女手中拉过李耳,紧紧抱在怀中,“这样的学生真是难得,我教他教定了。”于是,把李耳安排到一个坐位上,又拍了拍他的头,“这孩子,恐怕将来我都教不了他!”
就这样,李耳在这位老先生的指导下读书了。
李耳在这位老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很用功,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他不但自己读书,还把学到的东西,教给村里的其他小伙伴。每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把村子里穷人家的孩子招到他家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