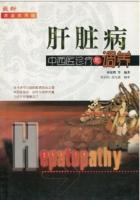这点,柳珞微相信,因为当时司徒骅也是这么跟自已说的。
“两个人慢慢地长大后,一个长得帅,一个长得俏,一天到晚厮守在一起,哪能不产生感情?等太太发现他俩在相爱的时候已经晚了,生米也煮成熟饭了。太太当然坚决反对,大少爷在得知真相后痛苦的要死,那段时间,我天天看他在喝酒,喝得人事不知。可有一点,我还得说大少爷的好话,那就是,他为了让那个司徒芷漪的心里不至于太难受,他始终不让家人告诉她真相,不管司徒芷漪怎样恨他骂他,他都把责任一肩挑了……唉,这才是真正有血性的男人啊……”
哑嫂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她在极力挽救在她看来是好姻缘的婚姻,而柳珞微,却已经不知道哑嫂在说什么了,她的脑海里混乱极了,乱极了。
她得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却说柳夏辉到了司徒家的别墅,推开门,却见司徒雷成斜倚在太阳底下,晃悠悠的摇椅发出咯支咯支的伴奏,五只毛绒绒肥嘟嘟的小拉拉们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追逐嬉戏。厨房门口,肥硕的靳妈坐在矮木凳上择菜,那个小保姆秀芳,在清扫树丛花枝间的枯枝落叶……眼前的一切,呈现出一派慵懒与闲散的气息。这,这跟司徒雷成在电话里所流露出来的焦灼与不安有着天壤之别。
“老爷子……”柳夏辉大步地走了进去。
司徒雷成懒洋洋地坐直了身子,太阳光并不强,只有几分苍白,苍白的好似失血病人的脸颊。可是,司徒雷成仍嫌光线太强,他将手掌覆在额头上,细眯着眼,看清楚了才弱弱地应了一声:“哎……是夏辉来了?”
柳夏辉走近,俯下身子看了看,疑惑地说:“老爷子,你怎么啦,病了吗?我才一天没来,你的脸怎么跟缩了水的黄瓜似的,皱巴巴的?”
柳夏辉这个人,平时说话直来直去的,在熟人面前更无所顾忌。跟司徒雷成,因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再加上司徒雷成刻意地讨好着柳夏辉,所以柳夏辉就把司徒雷成当成了知心的忘年交,言行举止间多少有些“没大没小”。
司徒雷成也不计较,不知他是喜欢这种调调呢,还是另有所图,别人就不知情了。反正,在别人看来,这对老少朋友的关系,处得可真叫人眼热。
“是吗?”司徒雷成顺势摸了一把自已的脸,自嘲道:“何止是缩了水的?我看像秋后的黄瓜,只剩皮襄了。”
柳夏辉嘻嘻一笑,把怀里的小黑背掏出来放在地上,拍了一下小狗崽的屁股,说:“找它们玩去。”
“老爷子,电话里那么着急,有事?”柳夏辉拖过小板凳,坐在一侧,问。
当然有事,而且是急事。
司徒雷成从刘嫂的手里接过保温杯,皱了皱眉说:“也不给小舅舅倒杯茶?这事也要我吩咐?”
刘嫂站在旁边不屑地翻着白眼,嘴里叽咕着,当然是很小声的:“他现在……现在又不是舅爷了……”
刘嫂可是个会记仇的人,不管谁的仇,她都记。以前林湘如活着的时候,总嫌她笨,嫌她懒,为了拉拉意外怀孕的事情还打过她。为此,刘嫂记恨在心,由此也被人利用了。这是后话。
而柳珞微也得罪过她,刘嫂当然也不会忘。所以,柳珞微的弟弟来了,她就当是柳珞微来了,自然不愿以待客之道来接待了。
何况,柳珞微已与大少爷离了婚,不再是大少奶奶了,柳夏辉自然没了以前的那个有光环的身份:小舅爷。综上所述,刘嫂觉得,此刻不往上踩上一脚更待何时?
司徒雷成拿阴郁的大眼一瞪,重喝了一声:“你说什么?”
刘嫂自诩在外头有了撑腰的了,她虽然赶紧张往屋里走,嘴里却不依不饶的:“我是说……说他现在又不是这个家的亲戚,他姐姐都被大少爷休了,他算什么呀?来就来呗,要喝茶,自己倒去……我不侍候……”
刘嫂说得极小声,纯粹是在嘀咕给自已听的。可司徒雷成不高兴了,虽然他没听清刘嫂在说什么,可刘嫂叽叽嘀嘀的声音让他很不爽。司徒雷成觉得,自从林湘如死后,这个家的人全他妈的变了。一开始是儿子儿媳没来由的,在一夜之间离了婚,其次,那个该死的贱丫头司徒芷漪上窜下跳地要争夺公司。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下人们也开始造反了,先是那个哑嫂提出辞工,辞就辞吧,反正要克的人已经死了,留着个会克人的哑巴也没啥用处。随后,司徒雷成发现,那个傻乎乎的刘嫂也不如以前那样听话和顺从了,不仅比以前更会偷懒,成天端着双手晒太阳,别说靳妈叫不动她了,连司徒雷成的吩咐她也敢拨嘴不动了。
妈的,她们是不是看自己一时不发威了想趁势爬到头上拉屎拉尿啊?假如真存有那样心思的话,哼,司徒雷成心里冷笑道,是不是一个个都想和林湘如去做伴?
“靳妈,你把那个该死的傻货给我揪过来,我倒要当面听听,她在发表什么高见!”在柳夏辉面前,司徒雷成更是不能容忍下人在主子面前放肆了。
柳夏辉忙劝止:“算了算了,老爷子,我也不口喝……老爷子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司徒雷成嘶哈着嘴,牙痛,让他更是怒上加怒:“事情等会再说,我要先收拾收拾那个目中无人的傻货,这样下去还不反了天了?”
这几天心火上来,司徒雷成保养的很好的牙齿也开始轮番和主人作战,弄得司徒雷成是,无法安睡,更无法好生吃喝,气得他是,恨不得掰下满口的牙齿。
“嘿嘿,老爷子,你不是叫刘嫂傻货吗?既然是傻货,那我们这些聪明人自然不跟她一样,老爷子要是跟她计较的话,不是跟她一样成了傻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