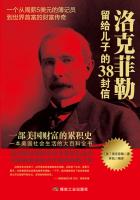雨已经下了有一会儿了,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滴雨是由怎样的一个姿态脱离天空、奔赴大地,只有那前赴后继的敲击声将我从窗边唤起,那股骤雨初来的幽冷直击眼眸,暗风吹入衣领提醒我这个春天仍还是冷。
雨珠不知是何原因离开了天空,欢快地撞击着大地,大地不嫌弃它们的鲁莽,就像师父不嫌弃我的愚钝一样。雨在窗前的模样使得它看起来像散了线的珠子,它顺着第一滴雨珠来时的轨迹速度惊人地拍上大地,轻微的一声便摔得稀碎,而更多轻微的声音覆盖着这一声响,那些碎成一片的雨水混成一块沿着低洼处溜走。此时远处的景象模糊不清,湿气一度闯进屋子扑打在我脸上,试图将我同外面的世界拉近点距离,雨水继续落在青黑的瓦上、缀绿的树上、嫩黄的草上、泛光的路上、灰白的墙上,它们都老实地接受雨水的洗礼,伏在窗台的我胸中似乎也落满了雨水,乃至鼻腔里也有湿冷的空气流动,庭院里那个大香炉还在吐着烟,烟飘散在风中,那笼罩着水雾的外面世界显得寂静而遥远。
湿漉漉的路上有人打伞走过,大红的伞布格外亮丽。
我所处屋子此时染上了一层深色,昏暗的光线使得此刻如同傍晚,桌椅变得古旧,书卷变得冷酷,其他的东西渐渐消隐,静得很,唯有雨声不曾消退。起初沙沙声像是书本被风翻乱了,书本随之被翻的越来越很快,像是指甲划过布料一般,又像是傍晚给寺门上闩的声音,这声音时而轻快、时而沉闷,然后是密密麻麻爆裂声,如炒豆子般繁密、激烈。突然一道亮光照进屋子,明亮耀眼的光劈开了这昏沉的景象,我看到远处的乌云夹着风雷压着屋檐朝我滚滚而来,雨珠一一破碎在窗前,它们拍打着水面,荡漾起一圈圈的波纹,看不清倒影。亮光转瞬即逝,那声音又变成了隆隆的车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仿佛看到赶车人马鞭在空气中飞舞,马蹄在平地践踏出一股尘土,车轮飞速转动,最后一声暴雷驱散了其余的声音,车轮随之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雨声落在瓦上是清脆的,顺着屋檐下来是急促的,滴在石阶上是的清亮,那瓦上似乎有人在行路,又似乎有人在弹琴,又似乎有人在敲木鱼,又似乎有人在念经,如果雨有灵,那么它的灵魂应该趁着这雨声又回到了天上去了。
这样的雨天我哪也不去,哪也去不了,我闭着眼只听着雨的歌声渐行渐远,不知这窗台已被打湿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