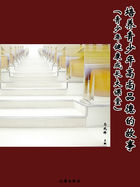以雷蒙·威廉斯为先驱的英国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兴起,宣告了阿诺德(为利维斯所深化和发展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终结,这就是,为阿诺德所排斥的“大众”在威廉斯这里开始成为“文化”的题中之意。按照威廉斯的重新界定,“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既包括了传统所谓的“知识的”和“精神的”,也包括了“物质的”(material)人类活动。“物质的”一语与“大众”相通,将人类的物质性活动纳入“文化”范畴,在威廉斯因而就是将普通人的指意实践即“大众文化”合法化;文化不能只是精英的,威廉斯要求,“文化是普通的”。在英国文化研究史上,这种以物质性和普通性定义“文化”的一个实际后果是,“将电视、报纸、舞蹈、足球以及其他日常制品和实践开放给批判而又同情的分析”。“大众文化”终于进入了“文化”研究的神圣殿堂。
自然,威廉斯的本意并不是要以“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如上面他那个综合性的定义所表示,又如他在提出“文化是普通的”时所申明——“我们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指一种全部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意义;指艺术和学问——发现和创造性努力的特殊过程。有些作者用该词表示这些意义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而我要坚持的是两者,是两者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但是,“大众文化”之挤入“文化”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后果是,传统的“文化”版图被实质性地改写了;而如果说以前“文化”一直主要地就是“艺术”文化,那么“文化”版图之被改写的一个美学后果则是美学将不能再是仅仅关于“艺术”的学问;换言之,威廉斯以后,美学的任务将是如何对待“大众文化”这种“非艺术”现象,一方面它无法为传统的“艺术”概念所涵括,但另一方面又不是完全与“艺术”无涉,而是有着大量的挪用和重构。由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性质,因而也就是“反美学”的性质,因为“美学”即隶属于一个精英的传统,其于20世纪西方美学史的意义迄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与英国文化研究差不多同步,法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发现并理论了与消费文化共生的社会审美文化现象。罗兰·巴特对时装的研究,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解剖,居伊·德博尔(Guy Debord)对“景观社会”的界说,一直到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之“仿真与拟像”的指认,等等,显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态度不同,其中几乎是完全的批判而少有同情性的分析,但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新的“审美”特性还是被客观地呈现了出来。根据他们的理论图绘,第一,我们已经由马克思时代的“生产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社会”;第二,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将物变成了符号即“物符”(objet-signe)的社会;第三,物作为一个能指,不再代表其实际的使用价值,而是指向一个被虚构和想象的价值,或者说,在“物体系”中能指与所指的自然联系被重新组织,例如“一条小小的发带透出漂亮雅致”被转换为“一条发带是漂亮雅致的符号”;第四,如果我们能够承认黑格尔的经典公式“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之关键点是“显现”,那么以符号这种感性形式去显现被生产出来的诗意欲望,当会造成一个美学的世界,符号的增殖就是美学的增殖。由于电子媒介的迅猛扩张,尤其是其无穷的图像生产能力,如果说印刷以复制文字符号为主的话,符号的美学在电子媒介时代就主要地表现为图像的美学,巴特所一般而论的“符号”被波德里亚突显为图像符号和由此而来的“日常生活的普遍的审美化”。或许有些危言耸听,波德里亚断言,整个社会的审美泛化将招致“艺术”的终结,因为“当一切都成为美学的,那就没有什么是美的或丑的,艺术自身亦将不复存在。”具体说,“为着图像的单纯传播,艺术消失于一个平庸的泛美学之中。”原因在图像,是图像毫无意义的增殖终结了“艺术”的存在。而如果“艺术”真的终结了,那么以“艺术”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也必将走向终结。
对于“艺术”和“美学”的前景,其实,波德里亚并非如我们想象得或他本人常常表达得那样悲观,他所谓的“艺术”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它是“真正的天才”、是“冒险”、是“幻想的力量”,是“对现实的否定和与现实相对立的另一场景”,是“一种超越性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艺术消失了。”我们知道,这是康德和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艺术”概念,是“审美现代派”的“艺术”理想。因而波德里亚所宣称的“艺术的终结”就不是一个泛泛之论,而是被他赋予了一种具体的历史意味,即“艺术的终结”在他意味着一个现代性“艺术”观念的终结,由此“艺术”将步入一个后现代的“泛美学”(transesthétique)的新时代。
面对艺术的转型,美学应当如何因应之而不致自身被历史所抛弃,是20世纪许多美学家思考的一个主题,除上面提到的英法作者外,还有如美国的杰姆逊,他将艺术置放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考察已成经典;又如阿瑟·丹托,其“艺术界”理论表现了对艺术史传统所拒斥的种种实验艺术的认定和接纳;再有更是尽人皆知的德国本雅明的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的“灵晕”的消失,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文化工业”的以艺术为其救赎的批判。无论其是否正确,都应视为对在审美对象即“艺术”发生变化之后的美学前途的积极求索。评价其求索之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此笔者只是提出,将审美对象的变化即“艺术”的“文化”化、“大众”化或日常生活化作为理解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一个有益的透视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