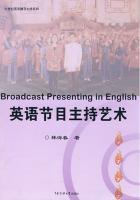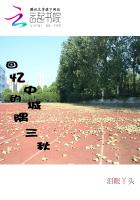河南古风淳朴,人性憨厚。一路上不时有捧着饭碗蹲在墙角的农民站起来跟我们招呼:“进屋吃一点?”学勤说这是自古沿袭的客套话,不能当真的。见到兰考老乡,学勤介绍我是从上海来的(他们不知道江苏,知道上海),姓尤。老乡们都笑了,用河南的拖腔像唱歌似的说:“城里人福气好,姓都比我们好。蔡,朱,又来了尤。”学勤见我不明白,解释说:“集体户有人姓蔡姓朱,你姓尤,老乡说的是谐音——菜、猪、油。”我恍然大悟,感觉有趣,也感到心酸。他们太缺乏因而也太向往“菜、猪、油”了!学勤悄悄说,这里老乡真穷,除了买盐几乎没有其他消费。唐寨老支书阎协崇是党的“九大”代表,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人民日报》以“革命先锋”为标题发过长篇通讯。但阎本人很朴实,见人说不出话。学勤说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坐的椅子一下子弹起来,他以为把椅子弄坏了,不知所措。还有一个人口相传的故事,说老乡进城看到飞速向前的火车,惊讶至极,逢人便说:火车爬着都那么快,若站起来还不知多快!
这里的老乡后来与火车结下不解之缘——到春荒就“扒”火车到远方去要饭。因周边都一样穷,要不到。“扒”火车是指不花钱买票;搭货车,在这里是默许的。老乡将客车叫“票车”,知道那是需要买票的。焦裕禄曾领县委常委深夜到火车站看望逃荒的农民,这一细节是真实的。学勤也领我“扒”了一次货车,当然不是要饭,而是游览了郑州、开封。我们虽已下乡成了农民,与真正的农民还是有天壤之别。
以前从学勤信中知道他的集体户很上进,也很激进,现在又添切身感受。队里为他们建了四间大瓦房不住,每人认一个五保老人当干娘干爹,与他们一起住,让孤老体验子女的温情。学勤说小陈惹了一头虱子。他们春节不回家,利用冬闲帮队里测量土地,做水利规划。不容易啊,曾几何时还是埋头读书的重点中学高才生,还是娇气的上海姑娘!
学勤陪我走访大佛堂(另一个大队)集体户,上海知青在异地他乡聚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一起做饭,那是一顿特殊的晚餐,兰考特色为主:熬一大锅黄澄澄的小米粥,在稀饭水平线之上贴一圈不掺红薯面的玉米饼,这已是他们极尽所能、很有档次的待客之礼。当地老乡一年只有除夕夜吃一顿白面饺子,平时从不吃纯白面、纯玉米面,都是要掺红薯面。各人拿出自己的储藏,使晚餐穿插了上海特色:有午餐肉、豆瓣辣酱,有我带去的咸猪肉。不伦不类,却绝对丰盛——在河南平原这个冬夜,一群上海知青就这样聚在一起像过节一样。我以杜甫诗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表达感谢惜别之情。
他们平时生活很简单,比江苏农村要差得多,整个冬天就是大白菜。那几天我与学勤、小陈围着炉子(他们烧煤,这让我很羡慕,我们没有煤,柴草严重短缺),边取暖,边做饭。锅子冒着热气,将咸肉用小刀削成片放进清水中,再放入白菜,肉的香味随热气沁人肺腑,谈天说地,慷慨激昂。
离开兰考前到县城瞻仰焦裕禄墓园,与学勤、小陈留影。
在候车室,我们一遍遍地唱“航标兵之歌”、“等待出航”,唱我刚学会的“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还有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这几首歌旋律相似,委婉、忧郁、压抑、感伤,融入了全部的离别之情。“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任何语言都已经多余。
突然,一直埋着头的学勤,抬起头,说我也回上海!我与小陈慌了手脚,像哄孩子一般,好一阵才算稳住情绪。小陈泪流满面,我也眼角发酸。还是引用学勤的描述:
——离开河南时已近年关,火车挤得一塌糊涂。我在他背后用肩膀硬顶,才把他送进车厢,车门关闭前一刹那,扔给他一袋在县城买的“金银卷”作干粮。所谓“金银卷”,即玉米、面粉分层合卷的馒头,玉米为“金”,面粉为“银”,这在当地已经是上等吃食。他到上海,不敢与我家里说兰考真实情况,他妹妹要把那袋没有吃完的“金银卷”扔弃,被他奶奶高声喝止:“这是学勤在河南过年才能吃的好东西,你们就这么扔了?作孽啊!”我妈妈和我奶奶在隔壁听见,一下子明白我在兰考的真实处境,不禁垂泪,家中春节黯然失色。
写此文时我找到了从邳县到兰考的火车票:1972年1月21日,320公里,5.4元。
扒火车
结束兰考之行回上海之前,按计划是向西旅行,目标去洛阳或西安。学勤、小陈与我早早进了火车站,“扒”西行火车。所谓“扒”,有扒拉开列车车门的意思,有七手八脚往车上爬的意思。这里主要是不买车票,免费搭载的意思。学勤走在前面,看他那种天经地义的模样,让从南方过来的我匪夷所思,但又十分兴奋,既有省钱的愉悦,又有冒险的刺激,还时不时映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画面。其实当地不买票搭乘货车很普遍,也很正常,既不英雄,也不无赖,车站上看见也不管的。因此就有焦裕禄领着常委雪夜到火车站看望外出讨饭农民的事迹。这个细节暗寓兰考贫困到极点,本地已讨不到饭;也不经意间透露出不花钱搭货车是天经地义的这一信息。从人们的不同叫法中也可分辨出,兰考人管客车叫“票车”,搭车是需买票的;货车不是“票车”,当然是无需买票的。
我们“扒”的第一列货车装的是白条猪肉,冰冻得硬邦邦的,一片片,横七竖八,人是不能与之为伍的。换一列,是个油罐车,圆溜溜的油罐外围有一圈铁杆,可扶手,倒也干净。不过静止尚可,一旦疾驰起来,是什么状态?我不敢想象。学勤说不要紧,说着率先爬了上去。我心怵,迟疑着不肯迈步。学勤下来,再等一列。这次不错,一只只麻袋装的是田菁(一种绿肥)种子,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对,就搭它。三人上了车,边拖动麻袋,让身体躺卧得更舒服一些——宛如刚住进招待所整理床铺一样,边互相打趣说:“都赶上票车的卧铺了!这么个好地方,可惜没有人知道。”话音未落,车厢的一角发出声音:“谁说没人?我打徐州就上来了。”惊吓之后,就是喜悦:遇到同行了!
近午,火车停靠郑州东站,很长时间也没有动静。经商量决定出站,先午餐,到郑州市区转一下,再“扒”车继续西行。郑州给我的印象,到处是红砖砌的正正方方的三四层高的楼群,顽强地给自己贴着新兴城市的标签。“二七”纪念塔刚建成,七层,双塔状,含意“二七”,在市内属较高建筑,式样新颖,又是绿色琉璃瓦,在周围的中低层红色砖楼中显得独树一帜。
对郑州我们并不在意,我们还是要向西。晚上,出了郊外,在月色指引下,辗转来到郑州火车站发车场。
郑州站是全国铁路运输枢纽,它的货场很大,分编组场和发车场。南来北往的货车都要先汇集到编组场,按去向重新组合,再到发车场等待出发。这些常识,都是学勤边走边给我的启蒙,也是他的经验总结。他说,有一次在编组场扒上火车,坐在车厢里被火车头牵引着来来去去,折腾了好久。所以“扒火车”须直接到发车场。郑州发车场与兰考之类小站不同,看管很严,我们三人未到入口就被拦下,值班老师傅恪尽职守,板着脸教育我们:发车场等于国家仓库,怎能随便进出?经不住我们死磨硬缠,加上三人的惨相,特别见陈又是女孩,终于同意放行;并指引路径,特意嘱咐遇到巡逻的不要乱跑,他们是有枪的。这个善良的老师傅应该是见不得我们小小年纪年根岁底、深更半夜、天寒地冻在外闯荡,诸多因素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但过关之后,我们边走边议论,坚持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老师傅家里肯定也有子女在外插队。因我们骗老师傅是搭货车回家过年,胡诌插队劳动一年所得不够买口粮,遑论回家路费?
发车场有十几股轨道,长龙般的列车时停时发,没有规律。有的像沉睡了,很长时间动也不动;有的则异常活跃,一会儿进,一会儿退,不知忙叨什么。我们为去向又讨论了一会,后来决定可向西去洛阳、西安,可向南去武汉三镇;不向北,大串联去过北京;不向东,那是回家的路。辨识列车去向是看车门边插的卡片。须绕过车尾的守车向前跑一截,才能在车门边看到标明方向的卡片,有油罐车不插卡片,还有漏插的,那就要跑更长的路。看了,去向不符,再折返,寻下一列,费时费劲又懊丧。折返多了,就厌烦,也顾不上安全,索性在火车底下贴着铁轨钻进钻出。身上穿着棉大衣,背着包(包里都是事先准备齐全的“扒火车”的必需品,如干粮、辣椒酱、水壶、电筒、小刀等),太厚了,钻不过去;只得脱下棉衣,把包放下,用手牵着,拖着过去,就这样也得紧贴铁轨才行。起初还害怕列车突然启动,几次一钻,就侥幸麻痹,就忘记害怕。跑多了就找到了窍门,原来轨道正前方有交通标志灯,凭颜色可判断行止(红停绿行黄准备),凭方向(上下左右)可判断去向。这一发现免除了来回折返之累和钻火车之险,只需远远地看标志灯即可了然于胸,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但很快又失望了:那晚不知咋地,西行、南行的车很少,仅有的几列都没有启动的音信。
直到子夜时分,遇见一位下班的铁路工人,他是搭便车回家去开封。他好心劝我们不要再等,说直到天明都不发西行、南行的车,让我们与他一起去开封,可随他一起坐在火车头里。开封是我们计划中返程路上的点,但事已如此,必须调整,而且火车头对我们也有很大的诱惑,于是决定同去开封。可是到火车启动时,火车司机坚持不准我们上火车头。这次死磨硬缠加惨相都不顶用,事后我们按自己的逻辑,认为司机家里肯定没有子女在外插队。下班的工人帮着说好话也没用,他很内疚,表示他也不上火车头,陪我们坐敞口车厢。
也只能如此了,由此也给了我们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严寒三九,天寒地冻,高速行进的列车,敞口车厢,拂晓前最冷最累的时段(下半夜两三点钟)。中原大地覆盖着皑皑白雪,露出两股铁轨伸向远方;铁道旁的大树完全被冰凌包裹,晶晶亮,刷刷地向后退去,我这个南方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自然景观。车厢里装的是机床,用草包、草绳包裹着,冰冷冰冷。我们将手上戴的一单一棉两副手套全部取下,四只重叠,垫在机床上,再坐在上面;不久屁股下一阵刺骨透心的凉气,寒冷将手套与机床冻在一起。只得再站起来,在车厢里不停跺脚,活动身子,抵御严寒;身边车外是一排排闪闪发亮呼啸而过的玻璃树;大脑里全部意识就是一个字——冷。那个不眠之夜,那个寒冷的凌晨,成为我兰考之行最深的印记。后来许多次的讲述,讲得最精彩,人们最爱听的也是这一段。其实它是我兰考之旅最艰苦的一段。
拂晓前抵达开封站。天还没大亮,城市还在沉睡,到候车室等待天明。候车室里很多人,有等车的,更多的是无家可归借此过夜的穷人。屋子里生着火炉,上面的水壶嘟嘟冒着热气,这在南方是很少有的设备,此时是我的最爱。坐在火炉边上的位置,将已冻硬了的手套放在火炉上烤;拿出杯子,从水壶里倒上热水,那股温暖、舒服,是无可比拟的。由此后,我坚定地认为,幸福是相对的,是上帝公允地施于每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其感觉好坏很多时候与其外在条件并无关联。寒意去了,倦意袭来;可能是打了个盹,然而感觉分明是睡了一个过瘾的好觉,醒来只见满屋暖和依旧,东倚西倒打盹的人群依旧,只是在水壶上烤着的手套发出一股焦味,慌忙取下,小心拍拍,冻结的冰水倒是干了,但两只手套各出现了一个焦印,一搓就是个洞。
天明了,一轮太阳光照人间,我们又精神抖擞了,迎着太阳走出候车室,世界好像都是我们的。与同栖火车站的人相比,我们跟他们有太多的相同之处,然而也有着最大的不同。
在古城开封游览了铁塔、龙亭、杨潘家湖、大相国寺等地,晚餐在河南饭店。由于在郑州遇挫,加上折腾一夜,西行计划变得索然无味,晚上搭闷罐货车离开开封返回兰考。
(作者系老三届上海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