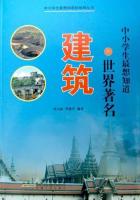一、“饥饿”、“饥荒”
在所有渗透到西方媒体的非洲印象中,灾荒和饥饿的印象是最始终如一和持久的。几乎任何一天阅读网上各种西方媒体发布的新闻,都可以找到关于灾荒如何肆虐非洲的新闻。这些新闻文本通常配着一些贫穷、憔悴和营养不良的妇女和儿童照片,他们令人遗憾地进入了相机的镜头(或读者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徒劳无助,似乎在祈求怜悯。这些报道和图片或者来自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津巴布韦和苏丹等,或者来自西部非洲的干旱地区,它们都在讲述一个同样的故事:非洲在遭受饥饿、饥荒。通常西方记者和编辑用概括和绝对的词汇,以很显著的标题报道有关非洲的饥饿和饥荒。
在描绘了非洲无助的形象后,很“自然”地得出西方必须帮助非洲走出困境的结论。这种帮助从呼吁西方国家的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到西方媒体公然呼吁把非洲的重新殖民化作为解决的唯一方法。在一篇标题为“为迷失的非洲哭泣”(Weep for the Lost Continent)的社论中,英国《独立报》宣称:“非洲是如此的无助,以致要相信它自己能帮助自己是很困难的。如果西方国家有这个意愿,它们可以重新对非洲这个它们匆忙遗留下的大陆进行殖民。用英国人作为它们的专业合伙殖民者,作为它们的行政官员,日本人和德国人能够管理非洲。”因此,西方媒体,尤其是曾经的非洲国家宗主国的媒体,塑造非洲的饥荒、贫困和绝望的形象的一个潜在目的,是为自己干预非洲,甚至重新殖民化非洲国家制造口实。
二、“黑暗”、“野蛮”
自从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开始,非洲在西方的印象就是“黑非洲”(“Dark Continent”)。《英语语言词典》2000年第4版(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Fourth Edition,2000)是这样解释“黑非洲”的:非洲先前的名字,如此使用是因为直到19世纪之前它的腹地基本不为人知,对欧洲人显得神秘无比。亨利·斯坦利或许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1878年他在《穿越非洲》的叙述中用了这个词。西方媒体使用这个词一方面是指非洲缺乏历史,这一点被西方的贸易者、传教士、冒险者、探险家和西方的媒体永久化;另一方面也指非洲黑人的肤色是黑色的。来自非洲的新闻报道这些“未开化人”的图景,他们在落后的传统行为、迷信,神秘过时、令人恶心的仪式,如女性的“割礼”中繁衍。2002年,在西方的印刷媒体和互联网上大量炒作非洲“启蒙”少女拒绝“割礼”的故事。
与此相关,2002年,BBC非洲部有一篇关于艾滋病在南非全国流行的报道说,有三分之一的南非人相信一种古老而奇异的“治疗”艾滋病的方式——与处女发生性关系。那里碰巧发生了一个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男人声称强奸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这个故事成为来自非洲的头条。西方媒体也充斥着来自非洲的野蛮审判的新闻,如一名尼日利亚妇女因被控告通奸而被执行石刑的报道。2002年11月,尼日利亚更是受到在西方媒体不公正形象的冲击,当年尼日利亚试图筹办“世界小姐”选美活动,但因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徒的抗议活动而被取消。根据BBC记者丹(Dan Isaacs)的报道,美女们在阿布贾得到“大量人群喧嚣和混乱鼓乐”的欢迎。当然,真正的大混乱在穆斯林抗议者发动暴乱时才开始,这个暴乱因当地报纸《这一日》一篇报道宣称说“如果先知穆罕默德在世,他都会爱上并娶其中的美人为妻”亵渎伊斯兰先知而引发。这个事件很快就借助西方媒体传到了西方。给西方人的印象是: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不能主办“任何的活动”,因为其人民持有非理性的信仰和文化。事实上,是媒体而不是信仰和文化导致世界小姐选举活动在尼日利亚流产。西方媒体负面的宣传,尤其是在暴乱之前耸人听闻地煽动性报道伊斯兰宗教法庭宣判那个被控告通奸的妇女石刑,给尼日利亚形象带来巨大的损失,不正确的报道和主观性的视角并没有把穆斯林反对这场选美活动放在适当宗教背景下。尼日利亚记者非理性的、激动而不负责任的评论只不过是折断了最后一根稻草,把穆斯林教徒带上了街头。
三、“冲突”、“战乱”和“政变”
非洲的许多地区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从部落冲突、武装冲突、内战到种族屠杀,在过去十多年里,3/4的非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战乱,其中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有安哥拉内战、莫桑比克冲突、索马里军阀混战、前扎伊尔内战、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仇杀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等。这些战乱有的已经结束,有的还找不到平息的迹象。非洲国家连续不断的战乱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非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冲突和内战在西方媒体中都得到相当的重视,它们自动获得媒体的中心位置或至少重要新闻的位置。
由于暴乱和内战,非洲被描述成一个普遍政治不稳定的大陆。没有战争,就有腐败的独裁者控制,或一个接一个政变作为改变政体的唯一方式。这种话语背后的假设是,非洲人不可能接受治理的民主原则,他们只能在独裁体制、腐败无能的暴君或军事统治下生活。据统计,非洲在1952~1985年间的军事政变共有73次,1989~1993年发生军事政变35次。频繁的政变满足了西方新闻媒体填充报纸杂志版面、电台电视台栏目的需要,西方人很轻易地把非洲与“政变”联系起来自然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英国《独立报》星期天版曾经有一个记者帕奇克(Patrick Marnham)发出疑问:“非洲是否能够被治理?”然后他继续宣称,“在非洲,没有人知道政府系统在运作”。BBC一篇题为“非洲的政变循环”(the African coup cycle)的文章中是这样报道的:“30多年来,从1960年到1990年代开始,政变是非洲实现政府变更的现实而又可行的唯一手段。”这样的媒体报道并没有告诉受众,在一些非洲国家发生政变和独裁时,还有许多国家从来没有感染过“剧毒的军事政变病毒”,它们在常规的基础上进行选举。
四、“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
自从1981年6月5日美国医生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已经从少数几个热点地区蔓延到了几乎是世界的每个角落。尽管首例艾滋病患者在美国发现,但非洲几乎成为艾滋病的代名词。国际新闻社(IPS)2006年12月14日文章《非洲:一个充满孤儿的大陆》开篇就写道:战争、艾滋病、疟疾、霍乱和饥荒渐渐地把非洲变成一个充溢孤儿和少年的大陆。可以说,西方媒体成功地给了艾滋病一张非洲面孔。通过高度轰动化的标题和感染者人群的照片,西方媒体似乎在告诉受众,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西方媒体把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在非洲迅速扩散归结为无知、不愿意改变性行为方式和落后的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使讨论性和艾滋病成为禁忌。
贫穷问题在疾病传播中起的作用也被提及。然而,与贫穷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些穷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接受医疗,而与他们一样的人在富裕的西方却能接受医疗,但是这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宣传。事实上,只要富裕的西方与贫穷的非洲国家之间的鸿沟继续扩大,艾滋病、伊博拉病毒、疟疾和其他的多血症疾病就会戴上非洲的面孔。就西方第四权力阶层来说,“非洲面临一个可怕的未来”,或者更准确地说,“非洲面临灭绝”,除非西方政府和人道主义机构给予救助。
五、“部落”或“部落主义”
西方媒体经常用“tribe/clan”或“triblism/clannism”来描述非洲人们共同体,把非洲发生的种族屠杀、内部冲突归入“部落”或“部落主义”新闻框架。《纽约时报》2007年1月22日文章《索马里新政府面临旧问题:部落》认为部落政治拖垮索马里。非洲固然有不少族裔社会发展还处于部落、部族或部落联盟阶段,但“部落”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有时“部落”几乎是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媒体强加在非洲国家民族头上的带有歧视和轻蔑的称呼。在殖民统治时期,各欧洲殖民宗主国为了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加强了对殖民地民族的研究。西方学者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对所属殖民地各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对所有的非洲人们共同体均冠以“部落”称号。“部落”一词可说到了滥用的地步,它有时用来表示文化单位,有时用来表示政治单位,更多的则是在“表示一个生物学上特殊的群体”。
美国非洲史专家保罗·博安南和菲利普·柯廷早在1964年就指出,制造“野蛮非洲人的神话”的表现之一是“部落”和“部族主义”在新闻媒体上的使用,“他们用‘部落主义’这一词来分析非洲事务,但对世界的其他地区却不采用这一词语。”“部落”这一概念不明、含义不清的术语,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中已失去描述人类社会组织的原有含义,而被赋予生物学上落后、低级和原始的含义。1968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写的“非洲史学”的词条中,非洲著名历史学家戴克和阿贾伊也谴责了一些殖民主义御用文人对非洲历史的歪曲,其中即提到他们对非洲社会组织的歪曲。戴克和阿贾伊指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描述非洲部落的离奇古怪,这是为了推进殖民统治的建立并使其合法化。”尽管“部落”曾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普遍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但大部分非洲学者对这一词持否定态度。非洲人类学家奥克特·比特克对这一词也深恶痛绝,认为“部落”所含的贬义源于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家对这一术语的滥用。
六、“原始”和“热带动植物”
西方媒体通常根据所谓的兴趣或人情味选择描述非洲“原始、热带丛林”中的动植物。当一场干旱威胁到几百万非洲人的生命成为新闻时,它是否适合放在《纽约时报》的头版?答案是:当非洲动物死亡成为新闻可以。1992年,《纽约时报》在报道干旱和饥荒蹂躏部分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时,在8天里面刊登了5篇重要的新闻。其中三个故事得到显著表现,它们是关于大象、犀牛和其他濒临灭绝的生物,而另外两个更为简短的故事则湮没在内页中,它们是关于非洲人自己的新闻。
指责这样一个事实是毫无价值的,即在这种现象中,美国新闻界更为关注非洲热带丛林中的动物,而不是非洲人,这或许可叫做“非洲的动物化”(“Animalization of Africa”)。美国电视频道(像Animal Planet、Discovery Channel)播放了一系列关注原始非洲和“狩猎旅行者”的纪录片,而不关注非洲当地人。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中的“狩猎旅行船”展现的是非洲原始热带丛林的经历。因此不用奇怪,在许多美国人的脑海中,一提到非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Animal Planet和Discovery Channel提供的印象。在不少西方人看来,这就是与非洲有关的全部。詹姆斯(James Michira)第一次到美国的飞行途中,在从纽约飞往双城的航班上,一位年长的女士坐在他的身边,她询问他,在非洲他们是否和狮子做朋友。这似乎是她从媒体上获知的有关非洲的全部。因此有必要重复的是,在西方,非洲有比野生动物更为值得关注的东西。
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到,非洲形象被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概念化和简单化非洲的过程。尽管非洲有53个国家,种族繁多、文化多元,但它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国家。在某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经常被描述成非洲的整体形势。显然,当西方媒体频频用以上词汇来描述和界定非洲时,西方受众眼中的非洲也就是西方媒体描述的非洲,他们能够想到与非洲有关的词汇是灾荒、战乱、疾病、原始、黑暗等也就不足为奇。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查雷妮(Charlayne Hunter-Gault)所说:“如果你年复一年所听到的都是饥荒、干旱、死亡和冲突,人们就会得出非洲问题很棘手,非洲从来没有变化的结论。”根据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2001年民意调查,英国人认为以下是导致第三世界贫穷的主要原因:战争/冲突(69%);无能的政府(66%);腐败(44%);债务(36%)等,而对非洲被殖民侵略的历史、被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盘剥的现实很少提到。事实说明,与殖民时代西方的人类学者和探险者一样,西方媒体也“被赋予这个权力运用西方的规范通过罗列非洲的不足来描绘非洲的形象”。莫里斯认为,英美媒体通过仅仅集中报道负面事件,把非洲国家政府和政治家描述成无能的、腐败的,非洲政府国家领导人被描述成充满权力欲望的、独裁的;而把西方国家描述成高级伙伴,肩负着帮助无助、野蛮、自我毁灭、像孩子般的非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