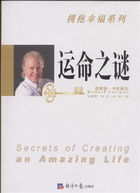正是随着知识分子对商业态度的转变,明清时期的一些文人开始涉足商业领域和广告领域。如清代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罢官之后,在扬州卖字画为生。他曾写一则“卖画文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广告字画价码醒目,语言简洁明快。当时,人们争相购买他的作品。知识分子的加入,对中国传统广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广告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是以文人为创作主体的对联广告在明清时期得到推崇。明清时期,士大夫几乎都有作对联的雅好,他们把中国古代对联的技巧推到了最高峰。明太祖朱元璋为粉饰太平,命令百姓在大年夜贴春联,相传他曾经为一个目不识丁的阉猪匠写过一幅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对联广告。自此,士大夫对对联广告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商业对联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说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唐伯虎曾为一绸布庄写有“生意如春意,财源似水流”的对联,“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曾为西湖一酒馆写有“东不管,西不管,我管,酒管;兴也罢,衰也罢,请罢,喝罢”的对联,以致求联者络绎不绝。相传清朝才子纪晓岚也曾为一理发店写过“虽是毫发生意,却是顶上功夫”的广告。清人朱彝尊《日下早闻》卷三十八记载当时的情景:“正阳门东西街招牌,有高三丈余者,泥金杀粉,或以斑竹镶之,又或镂刻金牛、白羊、黑驴诸形象,以为标识。
酒肆则横扁连楹,其余或悬木罂,或悬锡盏,缀以流苏”。随着文人的参与,带有浓厚文化意味的对联广告成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广告形式。《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对联,以图润笔”。“尤其是通文墨的儒商更是利用这种极其实用的文学形式,创作出许多以商业宣传作为目的的楹联,为商业与广告文化增色不少”。二是书刊广告得到发展。我国的书刊广告始于唐代,成于宋代,兴于明代。唐中叶我国有了刻板印刷,也便有了书刊广告的雏形。宋代,活字印刷技术出现,出版业获得快速发展,书坊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增加书籍的销售量,除了提高书籍的刊印质量,适应读者阅读兴趣外,还在书籍上刊登各类广告。与唐代书刊广告相比,“宋代书刊广告的广告意识更加自觉、广告内容更加丰富、广告形式更加完备,广告意识与版权保护意识相互结合,互为表里”。明代,商品交换较以前朝代更为频繁,市井通俗文学兴起,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书市生意兴隆,刻书业更加发达,经营书籍的商人多起来,彼此之间也发生了竞争,书商的商业经营意识也更强。
因此,书商们不仅要在印刷、装帧等方面提高技艺,而且需运用广告扩大影响,建立信誉。明弘治年间刊本《奇妙全相西厢记》的底页就刊有出版商金台岳家书铺的广告:“……本坊谨依经书重写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后来,明清小说成为继唐诗、宋词之后的主要文学样式,书商在书刊广告的基础上,用书籍的插画做广告,演变出了插画广告。三是商业招牌彰显文化理念。宋以前,商店的招牌只不过是商店的标志,并没有什么别的含义。而明清时期的招牌则突破了以往人名、地名的限制,赋予了一种深层的文化理念,在作为店铺标志的同时,还宣扬自己的商业道德。如全聚德、同仁堂、润善堂、春永堂、东来顺、月盛斋等,无不体现了以德立信的儒商理念。此外,诗词、征稿广告得以兴盛。明清时期文人所写的广告诗很多,如郑板桥的“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广告诗含蓄幽默,耐人玩味。而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致使书坊竞争日益激烈。书坊为获得优质而适销的书稿,便广发征稿广告。李渔所著《资治新书》系列书籍,初集卷首即有“征文小启”,其中收录的当时上千篇的文告、条议和判语等,若没有大量的应征稿件为基础,实为枉然。李渔编印的《尺牍》系列图书,书首也有“征尺牍启”。明清征稿广告直接成为后世征文广告的先声。晚清诗人李静山为蜚声海内外的“王麻子剪刀店”写过一首《王麻子诗》:“刀店传名本姓王,两边更有万同‘汪’,诸公拭目分明认,头上三横看莫慌。”近乎打油诗的句子,既诙谐又形象地渲染了王麻子剪刀的货真价实。
鸦片战争以后,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广告传入我国,“由于广告业发展过程中对于民用广告的需求和消费大大超过了官方布告,于是出现了文人以其丰富学识造就广告的现象”,《沪江商业市景词·报社》这样写道:“是非曲直报中分,一纸风行四海闻。振聩发聋权利大,万般提创(倡)总由君。”这些报刊多数为文人所掌控,商业化倾向严重,普遍重视广告。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指出:“报馆于售报之外,其宗收入,本以广告为首”。薛雨孙在《新闻纸与广告之关系》中,也认为报纸经营好坏的关键在于广告。对报社的这一行为,梁启超早在1907年便提出:“办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维持”。辛亥革命前后,梁又在《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进一步论述道:“吾侪从事报业者,此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上不易独立。报馆恃广告弗以维持其声明,此为天下通义”。《申报》是我国近现代影响最大的商办报纸,创办人美查办报的目的就是赚钱。该报在1872年4月30日创刊号头版头条载《本馆告白》后即接载《本馆条例》,专谈该报发行、广告事宜。《申报》1875年10月11日头版《论本馆作报本意》公然宣布“以行业营生为计”。《大公报》创办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天津,但“早期《大公报》的广告始终保持在版面的二分之一左右”。创办于北京的《晨报》自创刊之日起,广告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后的10年中,《晨报》的广告比重不断增加,广告的种类不断增多,广告的手法技术也在不断提高。据戈公振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广告所占比重达到最高——在总面积2880英寸的版面中,广告内容就占了1258英寸,新闻版面仅占949英寸。
我国现代著名的记者、编辑、出版家和政论家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风行大江南北,他除了重视新闻业务外,也非常注意广告经营,对广告经营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28年,《生活》周刊销量已达4万份以上,“来登广告的也与日俱增,大有拥挤不堪的现象”。针对朋友“好了!可以赚钱了!”的感叹,邹韬奋明确表示:“就是赚了钱,也是还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生活》周刊第6卷28期和30期刊登了上海女子私立中学的招生广告,事后发现该校未经立案批准,便在31期刊出《本刊重要声明》,宣布该广告作废,并向读者表示歉意。这一做法很好地处理了广告“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广告思想:以广告“事业性”促“商业性”,广告的“商业性”必须服从“事业性”,以“事业性”带动广告的“商业性”。他说:“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社的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本报对于所刊登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而且,他也注意广告的版面设计,认为应把广告和美化版面结合起来,什么广告放在什么位置都要从活泼版面考虑,不能让广告割裂新闻。“新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刊物,如20年代的《小说月报》、《语丝》、《新月》,30年代的《现代》、《文学》、《七月》,四十年代的《文艺复兴》、《文艺阵地》等刊物都刊载了大量的新文学广告”。其中,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现代》杂志共出6卷34期,“共有约530则广告,平均每期杂志约有15则广告,相对现在的刊物来说,这当然是个不小的数字”。
随着近代报刊广告的兴盛,近现代文人的广告活动也日趋活跃。创刊于1898年的《湘报》从第28号起刊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长兴学记》的招股广告,后又连载了《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的招股广告。1902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原配夫人去世,在友人的劝说下,拟再婚,在《顺天报》刊出征婚广告,广告中要求:“一、女士湖北人;二、大家闺秀,性格开朗;三、通文墨,精诗赋;四,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五、夫死可嫁,亦可离婚”。1916年,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后,曾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后又到北京创办《京报》,重视刊登广告,现存的1919年5月4日《京报》样刊上即有诸如“北京华孚商业银行广告”、“中国银行广告”、“新中国杂志广告”、“大喜香烟广告”等商业广告。1918年,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也非常注意发挥广告的作用,刊登进步书刊和国货广告,进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宣传,在报头下方刊有“广告价目表”,向社会各界招揽广告。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报头下即刊登了广告价目,广告有封面、中缝之分,短登、长登之别,价格也有区别。毛泽东本人也写过广告。1915年秋天,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为了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道,用蜡板油印了一份两三百字、落款是“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征友启事》文笔流利,字体刚劲有力,大意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朋友做朋友,并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还引用了《诗经》上“嘤嘤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诗,表示自己求友心切。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毛泽东把广告张贴在长沙街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刊出后,一些思想守旧的人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
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姓马的老校长,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于是他找到第一师范的校长,打听“二十八画生”究竟是什么人。当他了解到“二十八画生”原来是毛泽东,这是个品学兼优、受到师生称赞的好学生,征友只是为了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这才消除疑虑。启事发出以后,毛泽东陆续收到了几个人表示愿意联系的来信。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这件事:“我从这个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毛泽东接触广告,最早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当时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涯,决定重返学校,进一所好一些的“学堂”,他后来回忆说:“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然而,“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师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之后,毛泽东又选择了省立第一中学,“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但还是“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