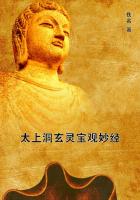新闻采访时,记者也要尽量采用常用的词语提问题,减少与采访对象沟通的障碍。例如,有记者去采访一个农村养猪分会的会长时问道:您这个养猪分会辐射了多少个农户?这个农民一愣:对不起,记者同志,什么叫“辐射”呀?记者被反问住了,只好向其解释什么叫“辐射”,要不然就没法再交谈下去了。在这里,“辐射”这个词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采访对象而言是个低频词,不容易理解其含义,这就给双方带来了交流的障碍。如果记者能够平视采访对象,事先就考虑到采访对象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用“带动”或者“影响”这类高频词代替“辐射”这类低频词,则会使采访对象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当然,从根本上说,新闻记者在采访或写作中是否具有采用高频词的意识,与记者自身是否有人文精神及其业务水平的高低和采访深入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牛新权)
延伸阅读:
1975年至1976年,在国家出版局、中国科学院、新华社领导下,由北京新华印刷厂,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以及北京市1500名中学生协同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查拼统计”。从政治理论、新闻通讯、科技和文艺四类书籍86本、期刊104本、文章7000余篇共2100余万字中进行“查频”,结果是印刷现代书刊一共只用了6265个字。这6000多个字中分五类,最常用的即560个,常用字807个,次常用字1033个,共计2400个,这些字占了书籍刊物汉字出现次数的99%。即是说,一个中国人只要认识2400个字,一般的白话文都可以看得懂。此外,不常用的汉字有1700个,偶出字2165个。
在560个最常用字中,最多的反复出现几十万次,如“的”字,在2000多万字中就出现了83万次。最常用字出现频率最多的有42个字,占了报刊用字的四分之一[江凯波:《书报刊上最常用的汉字》,《出版史料》2002年第4期。]。
11.从众效应(conformity effect)
又称“阿希效应”。指个体在群体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群体的影响与压力,因而在知觉、判断与行为上趋向于跟多数人相一致的现象。引起从众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在情境方面,有事情的性质、团体的荣誉、群体人员的成分、群体的凝聚性和一致性、群体的情绪气氛、群体间的网络结构关系等。在人格方面,有智力的高低、情绪的稳定性、自我概念、人际关系的概念、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等。从众现象在群体生活中到处可见,诸如入境随俗、随行就市、赶时髦、随大流等等都是。[陈会昌主编:《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心理发展卷》,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在传播活动中,从众是指个体(或群体)不知不觉地受到一个真实或臆想的群体的压力,而在态度或行为上发生的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变化。从众可以表现为思想上从众,大家怎么想我也怎么想;也可以表现为行为上从众,大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从众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主要看从众的目的和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体一旦进入群体之中,其个性便被湮没了,变得情绪化并且失去自己的判断,群体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追随群体的行为表现。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极左思潮控制下的宣传报道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一个明显的唯心主义口号,竟然被我们众多记者用自己的报道来“证实”,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亩产多少万斤的“卫星田”也被新闻界连篇累牍地报道[周象贤、李湘刚:《从众:新闻中的病理思维》,《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4页。]。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记者受到整体报道趋势的影响,放弃了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的原则,“从”了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之“众”,现在很多人回想起来,对于当年的狂热觉得不可思议。
在网络传播活动中,从众效应更为突出。像2005年2月24日,白烨在新浪博客上贴出原发于《长城》杂志2005年第6期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该文评价韩寒的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并对“80后”提出了批评:“‘80后’作家以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不可能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3月2日,韩寒做出回应,在新浪博客上贴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认为“以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由此,“韩白之争”拉开序幕。两位主角一个是“80后”的代表韩寒;另一个则是代表着“父辈权威”的白烨。
红火开战的不光是此二人,他们各自的支持者,更是紧跟其后,态度也更加激烈。特别是支持韩寒的一批“80后”,他们的语言多为犀利坚硬的秽语。在他们的偶像的带动下,向父辈权威专家发起了猛攻。韩寒的系列短文迅速扩大为一场风格粗鄙的“战争”,并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葛红兵、宋红岭:《分化与缝合——2006年文学理论批评热点问题述评》,《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这是典型的集群跟风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与网络的匿名性功能直接相关。在公开场合“论战”者的身份是公开的,众多“80后”即使倾向于韩寒的观点,也还是会顾忌自己的言论。因为当个体出面时,目标明确,谁也不愿意成为公众的靶子。
但是在网络上就不同了,匿名会掩盖个体的态度。平时许多“80后”虽然积累了对学校对老师对家长的不满,加上自身的叛逆性格,很想发泄自己的情绪,但苦于一个人或少数人,不敢表现出来,欲望常常被压抑。但当大家都怀着对权威、对传统的不满,加入了“韩白之争”时,便找到了共同的抗争对象,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力量,也就产生了从众效应。参与者会认为即使被骂也是整个“80后”这一代,不可能是点名道姓,匿名状态和暂时形成的群体会给个体带来心理上的保护,并增强了自己宣泄、对骂的胆量。正如有学者所言:“这是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的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中译者序第5页。]。
在历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不少作品都是记者克服从众的消极影响结出的硕果。比如在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对“非典”产生的原因有多个版本:禽流感或鼠疫引起、遭到生化武器袭击等等。然而,《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获第14届中国新闻奖消息一等奖作品)的记者,在衣原体是不是典型肺炎病原的争论中,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同中求异,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以独特的视角,勇敢地站在广东专家一边(没有认同北京专家的意见),在全国众多媒体中,独家如实报道了广东专家的观点。报道见报后,因为与众不同而受到广泛关注,引起强烈反响。并对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宣布“非典”的病原是变种冠状病毒提供了依据[刘保全:《从获奖新闻作品看记者的创新思维品质》,《新闻爱好者》2005年第4期,第20~21页。]。(赵自然、范璟)
相关实验:
阿希的“三垂线实验”证实了团体影响对人们从众行为的作用。阿希用卡片为材料,一张卡片上画有一条线X,另一张卡片划有A、B、C三条线,其中B与X线等长。阿希找来五个人一组做被试,其中只有一个不知情者,其他都是实验助手。他让每一个人判断ABC哪条线与X等长,并大声讲出答案。先由事先串通好了的人逐一报告说“C”与“X”等长。最后由不知情者判断,重复这个实验的结果发现,即使在“C”与“X”具有肉眼可见的差异时,仍有35%的人顺从了团体的看法,选择了“C”。[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487页。]
12.错误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 effect)
错误信息效应又称为误导信息效应。指在传播活动中,误导性信息使亲历事件的人产生了错误记忆的心理效应。[戴维·迈尔斯著:《心理学》,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错误信息效应是对过去经验和事件的记忆与事实偏离的心理现象。它产生的深层心理机制是,人的记忆是一种信息编码,这种编码把人获得的信息进行归类,然后命名;最后在脑子里存储的就只是一个归类后的命名,而不是信息本身。编码和解码过程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信息在转换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记忆的错误。另外,情绪、因果关系和内隐记忆也是造成错误信息效应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容易产生错误效应的人是富有想象力和容易接受暗示的。
错误信息效应在人际传播中十分常见。特别是在司法审判中,容易产生消极的后果。目击证人在目击一个事件后,会受到很多信息的影响而产生错误记忆,做出错误证词。如2001年6月1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报道了包括11名死囚犯在内的110名犯人,根据新的DNA证据被无罪释放。被释放的这些人中有一半,当初是由于目击证人的错误记忆导致的错误证词才判处有罪的[Deborah K.Eakin,Thomas A.Schreiber,and Susan Sergent-Marshal1.Misinformation Effects in Eyewitness Memory: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Memory Impairment as a Function of Warning and Mis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2003,29(5):813~825.]。
又如2007年7月6日,我国陕西林业厅作出了“镇坪有华南虎”的结论。其中《华南虎调查报告》得出华南虎存在的主要证据有:脚印、目击记录、虎啸。报告中“目击者”王根华声称自己“曾在山上看见过碗口大小的动物足迹,脚印直径17厘米左右。”而另一名目击者朱秀芬则声称:在5月18日早晨,她从山沟里挑水回来,在距离家门口20多米的小桥处,看见一头“半条牛”大小的动物蹦跳着往山下跑,“它身上有黑的和白的横杠杠”。然而,当调查“华南虎事件”的记者辗转赶往渔坪村2组时,在报告里被指“目击老虎约为1分钟的”王根华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他们其实根本没有看见老虎,只是看见过大型动物的足迹。而朱秀芬则说她也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动物。当时“镇坪有华南虎”的消息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经过人们口耳相传,在当地人心中深深地扎根。当镇坪县及曾家镇林业部门的官员以及当地电视台记者找到两位目击者询问的时候[《警方介入华南虎事件——华南虎目击者承认做假》,《成都商报》2007年11月21日。],王根华和朱秀芬自然地将自己曾经目睹的大型动物和“半条牛”大小的动物与华南虎联系在了一起,继而产生了错误信息效应。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错误信息效应的产生有时是由于媒体报道对新闻事件的生动描述,植入到受众的脑海中并形成错误记忆。也就是说,当受众在媒介因素的影响下,错误地认为一个事件他以前见过,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见过的时候,错误记忆就发生了。由于错误信息效应常常是无声无息,令人难以察觉,以至于过后单凭记忆的话,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些是真实事件,哪些是暗示事件(Schooler&others,1986)[戴维·迈尔斯著:《心理学》,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错误信息效应的影响是强大而且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人的大脑往往会帮助人们重构对于事件的记忆。所以在传播活动中,减少误导性信息是消除错误信息效应产生的重要前提。(石慧敏、赵自然)
相关实验:
错误信息效应的深层心理机制在于记忆构建。伊丽莎白·洛夫斯特(1978)和助手们为记忆构建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明。他们给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们呈现了30张幻灯片,放映的是机动车和行人相撞的全过程。其中一张关键的幻灯片显示,一辆红色的达特桑车(Datsun)在“停止”路标或“避让”路标前停住。然后他们问一半的学生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当红色达特桑车停在“停止”交通牌前时,另一辆汽车有没有超过它?他们问另一半学生同样的问题,但把“停止”换成了“避让”的路标。后来所有的学生都去看幻灯片,然后回忆哪一张是他们先前看过的。问题中提到的与实际情况一致的条件下,有75%的同学回答正确,而先前被问到误导问题的学生,正确率只有41%,并且他们不仅否定了实际看到的,而且记住了那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照片[〔美〕戴维·迈尔斯著:《社会心理学》,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