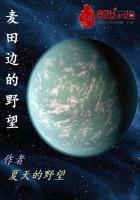尽管由于历史和视野的原因,“华语电影”还不是一个自明的、完备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极具政治性的非政治性概念,一个需要从各种不同的批评视角进行严格审查的意识形态建构。但“华语电影”概念必将而且已经给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生态带来巨大影响。不管是支持、反对,还是客观地研究,围绕“华语电影”概念所展开的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那就是对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电影给予整体性的正式命名的渴望,以及维护“中国电影”完整性、同一性、独立性的焦虑。细心的研究者一眼就能看出对两岸三地电影进行统一命名的愿望及其所处的困境: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都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传统。但是由于英国殖民、国共内战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两岸三地尤其是海峡两岸隔绝了半个多世纪,三地电影也因为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传统的“中国电影”概念,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个海内外华人电影研究者都接受的关于三地电影的共同命名还没有出现;无论是“中文电影”还是“华语电影”,都是一个从语言、文化出发的理念,它们有意识地规避三地社会的政治歧见,重新划定中国电影的文化疆界,对中国电影的主体性建构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电影应该以同一种语言和身份与世界对话。
在笔者看来,“华语电影”概念的重要价值,并非仅仅只是为两岸三地、以及其它华人社会拍摄的华文电影找到一个方便的命名那么简单。“华语电影”与文学研究中的“新国学”概念,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相同的学术立场与文化抱负。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电影类型,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尽管内涵方法论的元素),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电影”的学术观念。它是在“中国电影”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电影”为了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环境而做出的自我调整和全新定义。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要在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建立一种健全的发展格局和秩序,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统都“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即每一个思想、文化、学术派别都得到应有的评价,既不肆意夸大,也不着意贬抑,在一个整体中实现并获得自己的价值。简言之,“华语电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含有内在的现实批判性的概念,它与“中国电影大历史”的书写密切相关。[3]
对于中国电影“大历史”的书写,我们不仅可以从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宏观角度切入,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追溯中国电影的“起源、传统及其变迁”等具体方式着手。因为:包含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电影,都可溯源于一个多世纪前的上海电影;正是上海电影(有形的人材队伍和无形的文化传统)的分化与变迁,才造就如今大陆、香港、台湾三足鼎立的格局;分化后的上海电影(另一种意义上的两岸三地电影),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独立发展,已经形成新的品质与风格,但仍可清晰感受到其中老上海电影传统的影子。
“1945-1949,电影工作者四散,或南下,或北上,或东渡,一股力量分做三股;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三股力量几乎不约而同地异军突起,在世界影坛上奏出一曲中国电影的壮丽交响曲,三地电影的合流也在这时开始。”但是,“与此相应的,是三地各自所写的电影史,也可以说是偏颇不全或以偏概全,缺乏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学观念。虽然近几十年来,三地也各自出版过一些包括三地电影发展内容的电影史著作,但就其客观性和完整性来考量,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的史著。中国电影史研究这种长期隔绝、停滞不前的状况,不仅与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而且严重影响了三地电影研究的学术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三地电影业的进一步交流、相融与整合。”[4]从外部来看,西方人编撰的世界电影著作,往往将两岸三地电影置于一种并列、甚至割裂格局中。例如,在杰拉尔德.马斯特主编的《世界电影简史》里,“中国电影”和“港台电影”分别作为两个小节,与“日本电影”并列放在所谓的“东方电影”的条目下[5];在最新出版的《牛津世界电影史》中,有四个章节提到中国电影,标题分别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革命后的中国电影”、“香港通俗电影”和“台湾新电影”。“1949年之前的中国电影”(China before 1949)被单独放在第二部分的“民族电影”(National Cinemas)条目之下;而后三者(China After the Revolution,Popular Cinema in Hong Kong,Taiwanese New Cinema)则再次被并列置于“世界电影”(Cinemas of The World)框架之下。[6]这种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电影史,对中国电影的重视程度历来就不够,更遑论以“中国电影”的统一视角来论述三地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内部关系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安排。这种状况对三地电影的交流、融合与进步是不利的,也与三地电影同出一源、血脉相通,政治、经济、文化逐渐重新走向一体的历史现实不相符合。针对这种局面,一味地指责西方电影史家的“愚昧”和“偏见”是徒劳的,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撰写一部融会三地电影发展情况的中国电影通史,欧美电影史家对于中国电影整体格局的“误识”才会逐渐得到改正,“盲点”才会消失。李行说得好,“两岸和平统一,那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在国家统一之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如果能将原本同出一源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融汇起来,三流归源,那么《定军山》、《偷烧鸭》、《谁之过》则可同为第一,《难夫难妻》、《庄子试妻》亦可“同日而语”,相映成趣。于内于外,功莫大焉。
在“统一”中国电影史这个问题上,“华语电影”和“中国电影”的立场与使命是不谋而合的。因此,完全可以暂时搁置概念内涵方面的细微分歧,以“大中国”甚至“大中华”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电影”的历史和现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在历史研究中,这种具体的工作往往被称为“独创性的工作”(original work),也就是一些基础性的、原初性的研究,旨在“发现或核实某些事实以及某些先前未能确认的事实”。同时,不能贬低从新史实出发的、带有明显个人思想特征的历史阐释。因为,历史并不是一件件孤立的事实,而是编织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之中。一方面,某种统治着特定社会中特定时代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事件发生;另一方面,社会制度还会影响到生逢其时的历史学家们的见解和观念。电影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媒介现象,它所呈现的文化内容,无时不刻不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决定了电影的下层结构,决定电影依此发展的基础,以及可能繁衍出的潜力;而政治则决定了电影的整体结构。电影一方面反映出人类的通则经验,显示其社会政治的一面;另一面,也联系了个人经验,显示出心理政治的一面。”[7]甚至同一种电影传统,遭遇到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将衍生出不同的美学风格与样貌。
对于“中国电影大历史”的书写而言,“溯本求源”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中国电影百年的大历史,叙述的分歧并不源于历史的起点,而是源于历史中期发生的分化与断裂。中国电影曾经因“上海电影”而独树一帜,是否有所谓的“上海传统”存在?独树一帜的“上海电影”分化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足鼎立的格局,上海电影传统又产生了怎样的分化、断裂与新变?1949年前后,老上海电影人或南下香港,或东渡台湾,或留居上海,或“分配”和“调用”到全国各地,一股力量分成了三股甚至多股,他们的生活与创作覆盖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社会空间,跨越中华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两个时代。面对殖民资本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电影人的个体命运和上海电影传统的整体变迁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关系?上海电影文化与香港和台湾本土的电影文化之间具有哪些竞争与合作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上海电影”与“中国新电影”的诞生之间,具有哪些传承关系?[8]上海电影传统是否可以成为两岸三地电影再次合流的基础?这些都是“中国电影大历史”书写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最近,华语电影已经在国际上迅速起飞。以“华语电影”为题的研究也与日俱增,成为国际电影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很好地检讨华语电影概念,用力去写一部华语电影史。华语电影史既是华语电影研究的起点,也是华语电影研究的归宿。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注释:
[1]陈犀禾,刘宇清:《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趋势的几点思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第6-10页。
[3]关于“华语电影”概念的思考,笔者受到王富仁先生、钱理群先生的启发颇多。关于他们的思想,可以参见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钱理群:《我看“新国学”》,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4]程季华、李行、吴思远:《中国电影图史.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5]Gerald Mast,The Movies:a Short Story,A Simon&;Schuster Company,1996.
[6]Geoffrey Nowell-Smith Edited,The Oxford History of Word Cine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7]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16日,初版一刷,第23页。
[8]笔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约而同地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的三地新电影称为“中国新电影”,主要代表即大陆第五代电影、香港新浪潮和台湾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