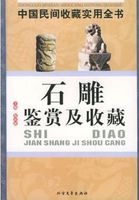这样,在富有诗美意味的意境创造中,高度的隐喻和非理性的意识流动为剧作染上了形而上的哲学印迹,在象征性、哲理性和多义性中呈现出饱满而唯美的艺术张力。气韵生动的诗美意蕴仿佛剧中的“一种奇特的阳光,一种具有异常强度的光,在它的照耀下,难以置信的、甚至绝对不可能的事物突然变成了正常环境”。在这种奇异阳光的照耀之下,善良与正义的人们逐渐成为一个个崇高的威武之师。而邪恶者,凶险的本性不断被暴露,人性恶不断膨胀。卓绝情境中的善与恶,以及尖锐冲突中的隐忍与凶暴、逃离与守护,使剧作具有了超常的蕴意。面对于大个子的淫威,马兆新疾恶如仇而又无力抵挡;为了守护内心圣洁的、美好的爱情,天甜视死如归;内心分裂的于大个子被过去生活的阴影撕扯着,在人性和兽性之间摇摆——独异而绝妙的人物和故事都非其他同类题材的剧作所能企及……在生与死胶着难分、几至白热化时,面对美好与邪恶的撕裂,人物灵魂的冲突与抉择显得炙手可热。在两难之中,悲剧形象李天甜自我人格的守卫与细草在忍耐中的自我淘洗显得尤其哀婉。
在这种情致的唯美追求中,尽管形象没有叱咤风云的壮烈,却也显示了她们炽热的内在情怀。它似乎在向世人昭示: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最能毁灭人也最能使人强悍的正是人内在的力量——人的精神:人类美好的感情和良知……正是在这种诗化情境中,剧作塑造的人物显示了奇绝的艺术魅力,剧作也超凡脱俗地从诸多剧作中脱颖而出,以悲情净化了人的魂灵,以善良感化着人的良知。这也是这部戏最为可贵之处。“一部戏剧作品是精彩动人还是平庸乏味,在于它所能在何等程度上从这种精神中激起适当的、高尚的反应。”
同时,正如斯特林堡说:“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其精神底层的力量与寿命。”正是深厚的精神蕴藉,使《荒原与人》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被阐释,不断获得再生。在剧作中,尽管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的北大荒这个非常的时空之中,但其意味同样是普遍而深远的。剧作家也只是将这一时空作为一个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李龙云曾经自述《荒原》的写作意图:“在这部戏里我好像写了知青。实际上,我不过借用了他们身上一些反映人类共同本质的东西。我力图接触一些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谈及戏剧冲突时,劳逊曾说:“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自觉意识被运用来实现某些特定的、可以理解的目标,它所具有的强度足以导致冲突达到危机的顶点。”在剧作中,剧作家的许多自觉意识和目标的达成是靠马兆新实现的。也许是因为承载着过多剧作家思想的负累,马兆新这个形象远没有于大个子等鲜活可爱,性格比较扁平,不够丰腴。而对于李龙云来说,马兆新的“自觉意识被运用来实现的特定的目标”,也就是在各种戏剧冲突中最大、最根本的冲突——人与自身的冲突。
对于人与自身矛盾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共同趣味。这源于人对自我的认同和肯定。而这正是80年代思想界和艺术界共同的精神取向。经过了一次次的思想争鸣与艺术讨论,有关人的话语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人对自我的认识与关注不可回避地成为了时代话语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人的觉醒”。而人的真正觉醒,不是意识到自身的伟大、崇高、无往而不胜,而是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无能、有限和永恒的苦难命运。李龙云是内省力很强的剧作家。“‘内省力’是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境地,是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思想,是认识自己,这可以启导他对别人的心灵也有深刻的认识……”从自我的历史和生活际遇出发,李龙云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上,以深刻的理性省思和无情的自我审视,剖析历史、感悟生命、昭示人心。
哲思与诗美是惶惑与焦灼后的豁然开朗,是内省力的审美升腾。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李龙云在北大荒生活了整整十年。十年艰苦卓绝的磨难,被文化和生活的巨大反差冲撞,人的内心很难抹去各种鲜活的记忆:“多少年过去了。尽管当时碰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但只要回忆起北大荒那段业余创作生涯,我就感到所有过去的一切都是值得怀念的。在我的记忆里,那里的荒原永远被夕阳的霞光笼罩着。它干净、深邃、美好,但又夹有一抹淡淡的惆怅。只要闭上眼睛,我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一幅画面:那缓缓流淌的别拉洪河,粉红色的高粱地中间那幽静潮湿的土路,那神奇的落马湖传说,那明亮的月光和流水……想到昨天,我就觉得仿佛重又置身于北大荒的怀抱里。古荒深处,长河落日如轮。一条清晰的爬犁辙蜿蜒曲折铺向远方。晚霞把荒原装点得那样高远、恬淡、苍茫。
坐在大爬犁上,身边演出队的伙伴们抱着手风琴睡着了。我倚靠着道具箱子,透过防蚊帽那井字形的花纹,望着沉下去的夕阳,在脑海里编织着文学天国之梦……”对青春岁月的追怀,对历史与现实的省思,生命中的哀与乐、苦闷和焦灼无不灌注在剧作的字里行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评论家林克欢说:“龙云的作品表现了他的困惑,一种焦灼。我之所以看重这部作品恰恰在于他这种困惑感。这是一种哲学的困惑,一种对理想失落的困惑。”但可贵的是,困惑和焦灼并没有吞没李龙云而是点燃了他内在的创作激情。对知青生活的创伤记忆在岁月中慢慢地沉淀下来,彼时强烈的激情与冲动此时在时间的磨砺下转化为一种持续性心境——情感能量在心灵中弥漫性地流动,在从容不迫的抒发中偶尔伴着难以抑制的迫切冲动……在弥漫性的心境下,创伤记忆被诗意地唤醒,并复活于剧中。
再次,《荒原与人》这部诗剧的成功,还得力于将诗的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进行戏剧演绎。具体来说就是将诗的审美效果引入了戏剧,营造了“意在言外”、“气韵生动”的诗美情景。其最直接的呈现在戏剧的对话上。剧作中作者的语言、情势的语言和人物性格的语言交相辉映,诗趣盎然。特别是大量的情势语言的运用,使李龙云完成了威廉·阿契尔所谓的剧作家的光荣任务:“让他剧中的人物揭示出自己灵魂深处的活动,而同时并不去说或者做他们在真实世界中所不会说的话或不会做的事。”以第九单元为例。李天甜爱恋着苏家琪,她是个历经苦难也不能磨灭心中诗情的女孩子,即使在批斗声中仍能幻化出与爱人诗意的交流。她不堪忍受屈辱,勇敢地选择了赴死;当死亡即将降临的时候,求生的欲望萌生,但为时已晚,疯狂的沼泽贪婪地吞没了这个几近圣洁的生命……在谈论泰戈尔的小说《摩柯摩那》故事的结局,摩柯摩那与情人最后的命运时,这对恋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李天甜:摩柯摩那走了。她走得那么坚决,那么不容易挽留……她为什么要走呢?
苏家琪:就因为她走了,她才更美。美总是残缺的,美只在人的想象中……
李天甜:作为一个女孩子,都会希望自己有内心的美,也有外在的美。当拉吉波看到她时,这种统一的美被破坏了,于是,她走了……
苏家琪:她希望用她的过去,留给拉吉波一片幸福的回忆,供他回味,而不惜忍受离开拉吉波的痛苦……
对话的隐喻意味很浓,与其说他们在谈论《摩柯摩那》,不如说他们在对自己的爱人和爱情自说自话。在泰戈尔那个浪漫凄美的爱情里,他们寄予了他们的爱情理想和信念,更预示着凄楚的结局……诗意的浪漫与含蓄使对话蕴藉悠远而深邃迷离。诗意让对话插上了翅膀,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劳逊认为,“对话离开了诗意便只具有一半的生命。一个不是诗人的剧作家,只是半个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