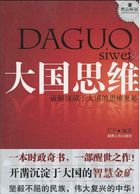直到遇到了安德鲁之后,埃达才彻底摆脱了性别束缚,获得了身心自由。尽管在生理性别上埃达和安德鲁是不同的,但是安德鲁并没有威胁到埃达自我的完整性,正如安德鲁的名字所示——“你也一样”(Andrew=And you do),实际上他们是一样的。两人拥有同样的爱好,都喜欢谈话,而在谈话时,两人是平等的,彼此既是听者又是说者,没有一个人会剥夺另一个人的话语权,所以他们的谈话能够称得上是有来有往的交流。与安德鲁的平等交往使埃达变得自信起来,埃达的自我不再缺失,她进退自如,“既能停留也能前行、既能进也能出。”在小说的结尾,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埃达和安德鲁的性别能够自由地相互交换,埃达可以变成安德鲁,安德鲁也能变成埃达,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能够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斯泰因这样说道:“渐渐地这事出现了。它是埃达和安德鲁。”所以这篇小说以一声满意的“是”结束了全文。
反对“父权制”:双性同体的目的所在
斯泰因在《埃达》这部小说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埃达和安德鲁的生活经历,表现了男性和女性消弭性别差异的可能性。其实,斯泰因对双性同体的认识是建立在她的生活经历基础之上的,因为她本人就是一个女同性恋者,不仅毫不避讳自己和同性伴侣艾利斯(Alice B.Toklas)的关系,公然与其生活在一起,还于1914年宣布了与艾丽斯的事实婚姻,而且在和艾利斯的关系中,她倾向于扮演男性的角色。例如,当她与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哲学家,艾略特(T.S.Eliot)、菲兹杰拉尔德(F.Scott Fitzgerald)等作家或塞尚(Paul Cézanne)、毕加索(Pablo Picasso)等艺术家探讨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问题时,艾丽斯是无缘聆听的,她只能和这些男性名人的妻子们聊聊女红、帽子、家具之类女人常聊的话题。所以美国文艺批评家盖尔文(Mary E.Galvin)在《五个现代主义女性作家》(Five Modernist Women Writers)一书中认为“斯泰因也许是除了萨福之外有记载的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女同性恋作家。”Mary E.Galvin,Five Modernist Women Writers.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2000,p.36.的确,在20世纪初,她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向常态性别模式发出了挑战。美国女同性恋理论批评家葛尔·罗宾认为:“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依据罗宾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斯泰因在现实生活中认同了女同性恋的性价值观,成功地转换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勇敢地逃离了不属于她的疆界,用属于她自己的独特方式取代了男性权威。不仅如此,她还在诸如《埃达》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融入了男性气质,追求男女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性别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合而为一,力求使她的创作达到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
然而,令评论家们奇怪的是,斯泰因虽然在小说《埃达》中设计了埃达和安德鲁合而为一的结局,但是她却并没有就双性同体的观念作出深入的理论阐释,倒是与她同时代的英国作家伍尔夫对此发表过精辟的见解。1928年,伍尔夫发表了“文学史上最长最迷人的情书”——并把这部风格独特的幻想体传记小说献给了自己爱恋多年的女同性恋作家兼诗人薇塔·萨克维尔-怀斯特(Vita Sackville-West)。1922年,弗吉尼亚与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同性恋作家兼诗人薇塔(Vita Sackville-West)相遇,并堕入情网。书中,伍尔夫以怀斯特为原形,塑造了奥兰多这位穿越时空、集两种性别于一身的形象,初步显示了伍尔夫对男女性别二分结构模式的挑战。次年,伍尔夫又发表重要论文《一个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在这篇文章中,她受到一对青年男女分别从左右两侧一起钻进出租车的情景的触发,提出“双性同体”的观点,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融合两性特征,即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伍尔夫这样说道: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一种是女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依靠的是这两种因素的和谐相处,融洽共存。柯勒律治曾经说过,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两种因素并存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有两种因素融为一体时,心灵才会才气横溢,充分发挥其所有才能。
与伍尔夫相比,斯泰因一再宣称她对女权运动不感兴趣,既不热衷于获得当时大部分妇女渴望得到的参选权,也很少发表文章直接论述性别问题,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意无意地歧视学无专长的女性。但是当“新女性们”义愤填膺地致力于“谋杀”19世纪帕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诗歌中描写的“家庭天使”、争取男女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平等时,斯泰因没有采取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她虽然没有像伍尔夫那样旗帜鲜明、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女权平等的观点,却在小说《埃达》的创作实践中运用“抽象、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技巧——把我们带到了熟悉的现实后面”。她取消了对埃达、安德鲁等人物的外貌、性格、举止和行为的具体描述,也淡化了人物具体可感的性格特征,甚至还有意识地模糊直至取消了人物的性别之分,从而用文学形式自觉地将文本创作和对以菲勒斯为中心的父权意识形态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语言和符号的深层层面探究取消父权制意识形态,建立女性符号、女性话语的可能性,使她的文学作品脱离了读者熟悉的语言形式和文类传统,使该小说摆脱了“教育小说”原本应该具备的社会性和现实性,从而用一种玄妙的方式揭示了双性同体的状态下整体不分的理想境界。
总之,在《埃达:一部小说》的创作中,斯泰因改变了写作手法和技巧,有意识地淡化了情节要素,去除了小说人物传统的文学体裁的整体性和封闭性特征,使用了一种非常直观的形式和风格,体现了她理想中的双性同体的境界,以此来抗衡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Bradbury,Malcolm and Robert Mc Farlane,Modernism.Harmonds worth:Penguin Books,1976.
Elliott,Emory ed.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Galvin,Mary E.Five Modernist Women Writers.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2000.
Gilbert,Sandra M and Susan Gubar,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 in English,Part Two.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85.
Stein,Gertrude Stein:Writings 1932~1946,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98.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伍尔夫著,瞿世镜译:《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伍尔夫著:《奥兰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