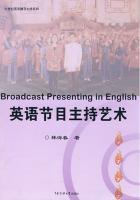其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政府的存在及其运行依靠的都是广大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来维持,因而“政府在公务活动中制作、获取及拥有的信息也是利用公共税金所生成的,属于‘公共产品’,即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人民基于纳税人的地位,当然有权分享这一公共财产。”总之,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必须将其制度化或法律化。如今,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条例。主要形式有:
(1)制定专门的信息公开法或信息自由法,总体地规范信息公开制度。北欧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方信息公开制度的地区。早在18世纪初,瑞典受英国“光荣革命”中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影响,制定了《新闻自由法》(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ct),在规定出版自由的同时,规定了普通市民和议员一样享有要求法院和政府公开有关正式官方文书的权利,开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先河。现代西方,则在1959年,芬兰制定了《官方文书公开法》。此后,美国、丹麦、挪威、法国、荷兰、加拿大、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日本等多国制定了相关法律。其中影响较大、内容较完备者,当属1965美国国会通过并于次年实施的《信息自由法》(FOLA),后屡经修改。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阳光下的政府法》,也被称为“阳光法案”,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信息公开法。
而我国也于2008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制定单项的或者特定事项的法律、法规,规定相应的信息公开事项。比如英国在还没有全面的信息公开法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制定了《数据保护法》、《地方自治体法》、《个人资料查询法》等,对信息公开和保护个人信息作了界定。
(3)在新闻法里对信息公开有所规定。如德国各州的新闻传播法都规定国家和政府一切从业人员都有义务向新闻记者等媒体代表提供有关信息。鉴于德国已在《基本法》中规定了人人都有采访公开信息的权利,所以新闻法的规定并非对于新闻媒介的特权规定。
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各国在信息公开的立法过程中,按照现代法治原则,普遍持以下几条原则:(1)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正如温克特·艾耶尔所言:“如果情报自由法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话,那么,不言而喻的是,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把公开作为原则而不是例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信息流通的自由度,促进社会的开放。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府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拒绝公民知悉、获取政府信息的要求。(2)任何公民都具有同等的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各国相关法律一般都没有对申请人在主体资格、申请动机上加以限制。因为全体公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而且,政府信息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一切公民本来对此就具有同等的权利。(3)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处理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关系。当具有公权利性质的知情权和属于私权利范畴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西方学者主张以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来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即使信息的公开可能会对立法造成相当的损害,但如果公开的利益超过其所造成的损害的话,信息仍然应当被公开”。(4)豁免公开的条款应该限定范围,界定清晰。首先必须明确,公开是原则,豁免公开是例外。但即便是豁免,也必须对豁免公开的范围进行限定并加以清晰的界定,意在避免政府利用含糊的法律用语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扩大豁免的范围,从而缩小公民知情权的范围。(5)政府拒绝公开信息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对公民的一项政治义务,而公民对政府信息所享有的权利属于强制性权利,当公民提出索取政府信息的要求时,不必说明其要求的正当性,相反,如果政府拒绝此类要求,则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说明理由。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知情权制度的一个要件。(6)法律救济原则。法学界有一句话:无救济,则无权利。当公民的要求遭到不当否决时,各国信息自由法一般都赋予公民法律救济的权利。途经有二: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从我国于2008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可看出,以上原则基本得到了体现,我国公民的知情权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后盾。
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公民知情权与国家保密权的关系问题。这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冲突问题。
“重视公民知情权(权利)的国家,无不将信息保密与信息公开的立法结合起来,限制国家的保密权(权力),在规定公民负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与责任之前,首先明确公民的知情权。”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本文点到为止。
三、知情权与媒介传播权利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对知情权的阐述中所说的,除政府外,新闻媒介也处于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同样被赋予了帮助民众获得所需信息的知情权义务。而在有关学者论述知情权的行使方式时,利用大众媒介知情的方式也列在第一位。他们举例说,如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获知相关信息。重大、敏感、热点的信息披露,大多是传媒的职责和魅力所在。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集中了各国一些代表性意见。报告认为,受众应有如下权利:一、通过传播获知信息的权利;二、使用传媒进行交流的权利;三、受众享有讨论的权利,四、受众在受到新闻侵害时有要求补偿的权利。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指作为新闻媒介受众的公民有权通过新闻媒介获知自己需要的信息,从而实现自身的知情权。也就是说,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来说,受众有权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和通过传播媒介了解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应获得的种种真实的消息情报,有权及时得知政府、行政机构等的有关公共信息和国内外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或有意义的事件。反之,凡是有意扣留这些信息,或者传播假的或歪曲失实的信息,就是侵犯了受众的知情权。
受众和媒介的这种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一般而言,公民委托具有获取信息的职业性质的新闻媒介代为行使知情权,而新闻媒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正是因为获得了公民的委托代理,从而被赋予了职业的新闻知情权。作为公民的知情权与作为媒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知情权,分别属于公民传播权利和媒介传播权利。雷润琴认为:“以主体身份为标准来看,(传播权利)可分为公民传播权利、媒体传播权利、国家传播权利。”媒介传播权利的合法性源头就是为了满足公民知情权,也就是说职业的新闻媒介受公民的委托,代为行使并满足其知情权,从而才能享有一定的媒介传播权利。正是在这种权利委托的意义上,媒介才被认为是社会公器。
媒介为满足公民知情权而享有的职业权利包括:(1)采访权。采访权是新闻媒介的公认标准。不具备采访权的媒介,很难说得上是新闻媒介。当2007年,中国著名的门户网站新浪获得奥运会采访证时,便有人欢呼新浪作为新闻媒介地位由此确立。同时,采访权是权利还是权力也值得讨论。雷润琴认为,采访行为是一种“合意”行为,记者并无强制被访对象服从采访的权力,记者采访权的滥用,应受到限制。因此,“采访权一般是指受法律保护的媒体人员在与其采访对象合意的情况下自由采访、了解、发掘信息的权利。即媒体及其人员在与被采访对象合意的情况下又不受干扰地收集、核实消息,并且安全有效地传送消息的权利。”(2)公开报道权。这是指受法律保护的媒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消息、新闻的权利。新闻媒介把收集到的具新闻价值的事实公之于众,满足公民知情权,是媒介应受法律保护的职业权利。出版权、播放权应该属于同样受保护的此类权利。(3)编辑权。这是依法受保护的媒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制定媒介传播方向、组织新闻报道、编排节目和稿件等业务权利。编辑权是否独立是所有新闻媒介面对的重大问题。一般来说,编辑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内容的独立性更强一些。所有权决定编辑权的,内容因为过多地受到商业经营的干涉,独立性就很难保证。(4)评论权。这是新闻媒介及人员通过媒介自由表达意见、观点的权利。作为新闻媒介的两大内容业务之一,评论向来被视为媒介的灵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新闻媒介的评论必须符合公正原则,同时这种权利必须限定在为公众所关注的和与公共利益攸关的范围内,不能扩张到任何人的私生活,除非其人的私生活严重影响公共利益,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女实习生之间发生的故事。(5)媒介优先权。这是指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采集时享有的优先待遇,分优先使用权和优先进入权。前者的对象主要是新闻传播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如电讯设备等;后者则指记者要求优先进入普通公民不可随意进入的限制性场合,如自然灾害区、事故发生地、战争地带以及法庭、监狱和国家机关会议地等场所。(6)消息来源保密权。这种权利保护记者不向任何人,包括国家司法部门泄露消息提供者的任何个人情况。总之,必须让所有消息提供者放心地为媒介提供消息。因此保护消息提供者,就是保证新闻媒介拥有永不枯竭的消息来源。因“水门事件”而被称为“深喉”的人,就是受这种权利的保护而至今还是一个谜。(7)舆论监督权。舆论,即为民意,是经过各种方式传播的民众的意见,狭义的舆论就是指大众媒介反映的民意或代替民众反映的意见。所谓舆论监督即指公众自己或通过大众媒介表达批评性意见形成舆论的行为与过程,其监督对象往往是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或利益团体。这种权利既是公民相关言论监督权利的延伸,具有公民权的性质,又是新闻媒介及新闻业者依法享有的新闻自由的延伸,是一种职业权利,具有社会权的性质。
在现代宪政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政府机关代理行使。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人民必须对其代理者行使权力的情况加以监督。舆论监督只是监督方法之一。新闻媒介在美国有所谓“第四权力”之说,这种权力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过公开报道评论形成的舆论监督。不过,新闻媒介也是代理民众行使监督权,当其自身代行此项权利过度,“媒介的权力”膨胀为“权力的媒介”时,它必然也要接受民众的监督。所以,舆论监督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过程。媒介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也要接受舆论监督,以免自身权力毫无节制。而舆论监督的限度,在法治社会,必然还是法律。
媒介为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依法获得上述传播权利(并非全部权利)。但从法律角度来看,权利和义务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对应词。媒介的传播权利亦如是,而所谓传播义务即是法律所设定的应该作为的与禁止作为的传播行为,主要体现在限制或约束上。本书对此不作深入探讨。
而媒介领域由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融合趋势。这种媒介融合趋势将使传统的模拟媒介发生数字化转型,从而一改过去单向度的大众传播模式,而呈现出去中心化的、交互性的融合传播模式。这一趋势将如何影响表达自由权的实现,则正是本书名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