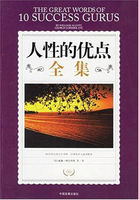6.3.7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救济安排与农户农业保险决策
(一)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与农户农业保险决策
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类似于“非正式保险制度”这样的风险处置机制。关于“非正式保险制度”,王凯(2006)认为“这是现代商业保险和国家强制实施的各种形式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蕴含通过群体合作对个体因风险发生造成的损进行分摊这一功能的社会经济制度。”例如家庭、教会、行会等,这些都是存在一定封闭性、紧密性、互惠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网络,将个体面临的风险加以分散和转移,体现“集众人之力,助一人之困”的互动救济精神。
在家族文化底蕴浓厚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家庭、家族组织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家国同构的社会体系的细胞。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的中心,家庭组织的稳固和健全是维持中国社会和文化不堕的最大因素。家庭、家族组织为其成员提供着养老、疾病、抚养等保障,具有保障、生产、教育、生育等多重功能,构成社会保障网络的重要基础。当某一家庭遭遇不幸事故时,其他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家庭服务以及避难所,使遭遇家庭能度过危机并最终恢复运行,这种互助除了基于亲缘上的情感因素外,还在于他们知道,他们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串,到那时对方也会提供援助。这种非正式保险安排又称为“相互给付”,其实也是一种社会配置风险的分配方式。这种非正式的保险制度有其优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但由于风险单位数量的有限性,风险的分散是不充分的。
家庭、家族组织等社会关系网络、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与农业保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中国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伦理为本的制度结构和独特的中华文化以及受此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沉淀,以及欠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共同决定了保险制度未能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上产生”。弗兰西斯·福山(F.Fukuyama,1995)指出,如果家庭被视为风险转移工具,保险潜在的经济价值就会被削弱,家庭提供保险安排,为其成员提供各种风险保障。家庭仍在很大程度上对家庭成员提供着保护以抵御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家庭仍然是一个相当有效的保险制度。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商业文化、外来文明对农村和农民家庭模式、结构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小农家庭的经济取向与选择空间,但在中国的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动摇人们对家庭等血缘、亲缘性社会网络组织的依赖,这种依赖在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日本以及经济转型中的东南亚国家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农户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地拥有从某种集体中寻求经济决策的习俗,而不愿意自己单独决策。原因似乎在于,单独决策的风险收益边界在中国现有的传统框架中一时无法清晰地界定。
在四川等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社会化、现代化、开放性程度比较低,村落内的家庭、宗族组织等社会关系网络比较紧密和广泛,当农民个体遭遇损失时,可利用这些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在村落社会关系网络中分散、转移,一定程度上替代农业保险等正式风险分散机制。而在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社会流动性大、开放性高,村落内人际间社会关系网络比较松散,人际联系纽带比较弱,利用这种人际社会关系网络分散风险的有效性大大降低。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互动加快,农民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外界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这种互惠性、人际性社会关系网络的侵蚀将越来越大,这种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的有效性和功能将受到削弱。此外,这种非正式风险分散机制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导致其范围很小,对风险的分散能力有限,尤其是应对具有“共变性”特征的农业灾害风险,这种机制的作用大打折扣。
(二)政府救济安排与农户农业保险决策
政府的赈灾救济制度中外自古有之,是一种很古老的风险分散机制。到了现代社会,政府救济仍然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应对和转移风险,保障他们生存安全的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政府救济是无偿的,因此,农户在受灾更多会寻求政府无偿的救济,而不会考虑要付费的农业保险制度,所以,政府救济安排会抑制农户寻求农业保险分散、处置风险的动机和意愿。政府救济对农业保险的替代,不仅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在经济非常发达的美国也是存在的。在美国60多年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发展中,由于政府救济安排的存在,抑制了农民的投保意愿,削弱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影响了农业保险投保率和覆盖面的提高。关于救济安排存废之争也是没有停止过。政府救济还具有政府安抚民心,获得民众尤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政治支持的政治功能。因此,政府救济安排现在会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可能会一直伴随农业保险的发展。
6.3.8意识形态与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
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嵌入”式的互动关系,农户的生活观念、生产行为、风险态度等受到其价值信念系统的支配和影响,农户的农业风险管理行为决策“嵌入”到农户特定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特定的价值信念系统和意识形态结构将型构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风险态度、消费偏好、群体交往模式,例如一些农户将遭遇天灾人祸归于“因果报应”、“上苍发怒”,就是特定的意识形态结构和价值信念系统所塑造的风险观、风险认知,这种风险观、风险认知对农户的生产生活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化传统对农户的风险观、风险认知和生产生活行为决策的影响上。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内省式的文化,是向内看的文化,追求天人合一。向内看的文化传统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尽量去适应自然环境,不过度开发、掠夺自然生产资源,不盲目崇拜、应用各种奇巧淫技,农业生产不追求外向的规模扩张,而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内卷化。这种文化传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农户追求稳定的保守型风险态度和保守的生产经营决策,导致农业生产技术变革非常缓慢,而没有产生西方“爆炸式”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质变,也导致了农业保险这种现代风险管理制度没有产生于中国,以及在广大农户中推广的缓慢。
意识形态对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下的风险保障观。中国农民传统意识形态的内核是家族文化、家族主义,君权思想、地缘、学缘意识文化都建构于基于血缘认同的家族文化之上。中国厚重的家族文化传统对农户农业保险决策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家族文化传统导致农户缺乏现代契约精神、信用观念,致使农户认同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不认同基于合同、契约的非人格化交易网络。农户信任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家人、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而不信任作为“陌生人”的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上门推销、宣传农业保险持怀疑、抵触态度,导致农户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其次,家族文化传统导致农户缺乏现代法律理念、信用观念,导致农户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认理、讲情而不讲法、不认法。在保险交易中,相当部分农户认为只要受灾,保险公司就应该赔,而不考虑受灾原因、损失是否属于合同规定的责任范围,由于农户和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合同的不同理解、看法,导致容易引发保险纠纷,而保险纠纷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很快扩散,引起更多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不理解甚至抵触,从而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开展;最后,家族文化传统形成了农户倾向于依靠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互助共济的风险保障观,导致农户在遇灾受损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家庭、家族成员、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而不是求助于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
因此,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及建构其上的传统意识形态对农户的风险态度、风险观、农业保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到农业保险在农村的开展、普及,影响到先进的农业风险保障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影响到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化进程。如果没有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有力支持,仅靠简单制度移植和政策号召,农业保险制度缺乏自我实施、自我发展、自我演化的动力,如果仅有工具理性,而缺乏“文化自觉”,任何制度移植、制度建构都很难获得成功。
第四节小结
本章以上海、江苏、湖南、四川四省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为例,管中窥豹,通过对四省市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创新、演化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深化对中国农业保险演化的机理、路径、过程和动力的认识。四个省市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的缩影,也是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代表,在演化的轨迹、路径、动力、过程等方面,四省市农业保险制度与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通过四省市农业保险制度演化的实践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和支撑前面对中国农业保险演化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能获得对中国农业保险制度演化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