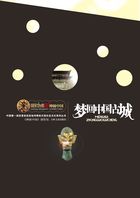《史记》在历史表述审美要求上的成就十分出色,至今仍能给人们以审美感受。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从史学发展上看,《史记》之前,先秦史家在史文表述上已形成一些看法,但在史书撰述的艺术水平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史记》整体的表述成就来看,后代史书确实很少能与之比肩,称得上是“绝唱”。司马迁对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及其高度的文字修养,对提高史家追求史文表述审美性的自觉性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史学批评家对《史记》写人物、记战争、绘场面所蕴含的艺术性加以阐述,推动了史学批评中审美意识的发展,并逐渐树立了史学领域注重史书表述审美要求的传统。白寿彝先生把历史文学作为史学史的重要内容提出来,他所说的“历史文学”就是指我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追求艺术性的优良传统。他说:“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学,是用第二个意思。”【2】而我们古代的史学家往往用“善叙事”来评价这种艺术性的文字表述。自汉代以来《史记》“善叙事”就为历代史学家所公认,他们在史书撰述过程中自然以《史记》为楷模,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尽量讲求审美性的文字表述,从中积累了很多历史文学撰述经验。此外,人们对《史记》艺术性的评论引发了很多相关问题的讨论,如史书叙事、史文关系等,从而使相关理论得到不断深入的阐发和总结。这些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撰述还很有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而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第一节 《史记》“善序事理”与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传统的形成
善叙事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鲜明特点,它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以至于很多人把这看成是整个中国史学的特点,产生了中国史学长于叙事而缺乏理论的印象。实际上,每一部史书的叙事成就都是在批判继承前代史书叙事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并且总是与相应的理论总结相伴随,这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良好传统。历代人对《史记》叙事的评价和继承就体现了这个传统。班固较早地评价了《史记》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性:“文章则司马迁、相如。”【3】据陈直考察,两汉人只称太史公有良史之才,称赞文章之美者,始见于此【4】。与此前扬雄等人“善序事理”的笼统评价相比,班固之评已经超越了史书文字的评价标准,而把《史记》文章的艺术性凸显出来。我们说,班固和司马迁并称“良史之才”,《汉书》文辞典雅,讲究叙事,这与班固对《史记》叙事之美的关注有很大关系,说明班固在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上已经有了自觉意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较早地从审美意识上对史文表述的要求进了行理论探讨,明确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5】。他说的“以叙事为先”,是关于“叙事”之审美的总的要求。从这个总的审美要求中,不难看出他同班固等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有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都表现了史家探讨史文表述要求的自觉意识。在后来的史学发展中,不同时期不同史学流派对于《史记》文字表述风格的不同态度,及其所表现的自觉意识,常常成为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传统形成和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观古代史家、学者和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和实践,有很多问题与《史记》有密切关系,是围绕《史记》而逐渐展开的。如史文篇幅的繁与简、文字风格上的文与质,以及表达效果上的显与隐等,都有理论上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史记》在史文表述方面的审美性得到了多方面的阐释,使人们对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理解得更加深刻。
史以叙事为美,因此,如何叙事是史书表述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从班氏父子称赞《史记》叙事之美,经张辅等人以繁简比较《史记》、《汉书》的表述风格,到唐刘知几提出以简要为主的叙事标准,史书繁简问题逐渐成为史书表述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实际上,史书繁简不仅是文字表述上的问题,还与史家的尊经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刘勰把《左传》和《史记》加以比较,一个“于文为约”,一个“详而易览”,这种文字表述上的差异,关键在于前者是附经而行,因而受到制约,使得氏族难明;而司马迁创立的写人的纪传体,表述因人而异,比较自由,因而受到后来史家的尊崇。通过这一比较,我们看到经、史、文的相互关系,以及史文表述审美要求所面临的制约。因此,后来学者关于经、史、文三者相互关系的认识和阐发,往往影响人们对史文表述的要求产生不同倾向,并成为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传统形成和发展程度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史通·叙事》一开篇,刘知几就提出了自己对经、史关系的认识:“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逮于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能露其锋颖。”他由此得出史不如经的认识。刘知几提倡史文俭省的理论依据也是缘经而立:“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史记》叙事“多谢《五经》”、“蓁芜”烦碎,而别赞“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的“微婉之才”【6】。可以看出,他对史文表述的要求明显受到经学思想的制约。在此制约下的叙事观念宗“春秋笔法”为史学叙事的典范。即《左传》中所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7】晋杜预的《左传正义序》对此加以解释:“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例,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8】钱钟书认为这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9】刘知几的史书叙事观念显然受到宗经思想的影响,虽然他的史文尚简的观念也有对史书撰述实践和理论的合理总结,并非完全在宗经思想下形成,但在很多问题上宗经观念仍制约了他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理解。
以宗经的眼光来看,《史记》叙事写人的文字相对于《春秋》经文,当然显得繁富。那么,后代人所推崇的《史记》之简妙又怎样理解呢?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汉大赋繁复华美的风格,以及赋作在汉代的兴盛,就知道司马迁《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多么简约质朴,也就可以领会司马迁对历史撰述表述风格的独特要求,他是在自觉追求一种属于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他的简约不再是寓褒贬于一字一句,而体现为在叙事、写人中蕴含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法则,让人们在读故事、感人生的审美感受中不知不觉地领悟历史真理。或者说,他在事与人的历史时空之外营造了另外一个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体味到历史、现实、社会和人生种种规律,而这个空间并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述出来,而是人们在阅读司马迁记叙描写的文字的同时体会到的,这就是史书文字表述的审美性。从《太史公自序》和他评价文章的一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推断,他所追求的文字表述风格并不是《春秋》笔法【10】。鲁迅称这种风格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11】,这是对《史记》文字表述艺术性的准确概括,并且揭示了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特征和价值:把心中所感、所想真实自然地表述出来,这样的文字就是美的;它冲破了那种受制于经义的文字运用,建立了一种新的史书表述要求,即从叙事写人中生动、真实地再现历史,让人们在审美感悟中更直观地观往察来。《史记》的出现,为后代史家撰述提供了史文表述审美要求的楷模,史学评论家开始关注史文表述的审美性,并逐渐建立起史书文字的审美标准,从而促进了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传统的形成。
中国史学自兴起之后,曾一度依附于经学,对史文表述的宗经要求,也是这种依附性在史家思想上的反映。正因为有这种关系,史文表述宗经的要求和审美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有一些相互涵融的范畴;在发展时段上这两种要求也不是绝然分离的,而是互有消长。随着经学思想影响力的减弱,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史学对史文表述审美要求也逐渐明显。魏晋时期,在史学评论活动中,人们多经史并称,表现了两者地位的渐趋平等,两晋时期始有文史合流的倾向【12】。萧统《文选》对史论之美的情有独钟,范晔《后汉书》对史论文采的自恃,以及沈约以文才之冠而参与修史,凡此种种,都表明了这种趋向。至明清两代,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和其他史书的言论更多,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已经明确区别于经学,有了独立的地位。明洪迈曾比较《尚书》和《左传》记言,得出经简传烦的结论【13】。章学诚也有“经旨简严,传文华美”【14】,“列传之体缛而文”【15】之说,与《春秋》的“比事属辞”相区别。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史学脱离经学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之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及其影响,以及后代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论对增强这种自觉的审美意识无疑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