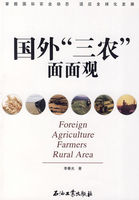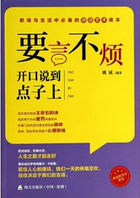当社会上只有一个教派或者两三个教派,并且教派的教师们都有一定的纪律服从关系时,那么宗教教师的利己情绪就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如果一个社会中有两三百甚至数千个小教派,那么其中任何一个教派的势力都不足以危害社会的秩序,教师的利己主义也不会有害于社会。这时候,各宗派教师身边的敌人多于朋友,于是教师们也必须十分关注自己品质的修养。那些品质都已经被大教派的教师所忽视了。大教派的教师之所会忽视那种品质,是因为政府支持大教派的教义,其获得了广大帝国几乎所有居民的尊敬,而教师们的身边全都是同门、信徒或崇拜者,没有任何敌对者。而小教派的教师之所以要关注这些品质的修养,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基本上是孤立无援的,因此也只好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师。在这种相互谦让中,他们彼此都能感到便利,从而他们大部分的教义也能摆脱所有荒谬、欺骗的东西,从而变成纯粹、真正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世界各个时代的人们最希望看到的。但是,成文法律从来没有使这样的宗教成立,也许将来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成立这样的宗教。这是因为,关于宗教的成文法律,总是会受到世俗的迷信和狂热的影响。那种独立教派的教会管理方案,其实可以说是无管理方案,可以使所有宗教教义实现最和平适中的精神。在英国内战结束时,曾经有人建议在英国成立这种宗教。在宾夕法尼亚,政府实施了这种教会管理方案。虽然那里的教友派占最多数,但法律对所有的教派都一视同仁。因此,听说那里就产生了上述最好状态下的精神。
虽然说仅仅平等对待各教派,并不能使一国的所有教派或大部分教派产生那种和平适中的精神,但如果教派数量繁多,并且教派势力小到不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的话,那么各教派对其教义的狂热不仅不会对社会有害,反而会对社会有利。要做到这一点,对政府来说,就必须果断地决定让所有宗教自由,并且教派之间不允许互相干涉,这样它们自然会迅速分裂成很多的教派。
在阶级区别完全确立的文明社会,常常并存着有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一种是严肃、刻板的,一种是自由、开放的。普通人民一般都会赞扬和尊敬第一种体系;而那些时下名流一般都会尊重第二种体系。我认为,这两种相反体系的区别是由人们对过度纵乐的谴责程度决定的。对于放肆甚至扰乱秩序的无节制的纵乐和破坏贞节等行为,只要不有伤风化,自由开放的体系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包容。然而,严肃的体系对这些过度的纵乐行为是极其厌恶的。人们常说,轻浮会导致普通人的毁灭。对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来说,即使胡作非为的放荡行为只持续了一周时间,也足以让他一直沉沦,陷入绝境而不得翻身,最后逼于无奈作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因此,那些聪明善良的人,都非常厌恶这些放纵的行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因为这些行为而陷入绝境,甚至不得翻身。然而,对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来说,这些行为并不会立即使他陷入绝境,反而他们还将一定程度的放纵当作他们财产利益或地位的一种象征。所以这一阶级的人,大都不会厌恶这些放纵的行为,最多也只是轻微责备而已。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教派都是在民间创立的。它们在普通人民中间吸收了最初的和最多的皈依者。因此,这些教派一般都采用严肃的道德体系,当然也有一些极少数例外。正是采用了这种严肃的道德体系,各教派提出改革旧教义的方案时才获得了大多数普通人民的支持。为了进一步获得这种支持,很多教派不断地改进这种严肃的道德体系,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然而与任何其他事情相比,这种过度的严格总是能获得更多普通人民的尊重和理解。
一般来说,那些有身份的富人大都是在社会上地位显赫的人。因此,社会时刻都在关注他的举动,他自己也就只好不断注意自己的所有举动。社会对他的尊敬程度,与他在社会上的权威和声望关系很大。于是,他们不敢做任何毁坏名誉的事情,并且要谨慎地遵循社会对他们这种人的一致道德要求,而不论这种要求是自由还是严肃的。相反,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人,并不是社会上的什么显赫人物。当他在农村时,说不定还有人会关注他的行为,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行为和声誉。当他进入上层社会时,他立即就沉没在卑微和忽视之中。没有人会关注他的行为,他也就任意妄为、自甘堕落地去做一些卑劣的事情。而一个卑微的人想要获得上层社会对他的关注,唯一的方法就是成为一个小教派的信徒。一旦成为某教派的信徒后,他就会立即受到几分尊重。因为为了教派的名誉,所有的教友都会关注他的举动;一旦他做出了什么廉耻的事情,违反了教友们相互要求的严肃道德纪律,他就会被驱逐出教派,这也是当时最严厉的惩罚了。当然,这种惩罚不是国家法律上的制裁。所以,相对于国教来说,小教派往往非常注重规矩和秩序,因此其严肃道德体系也要严肃得多。事实上,这些小教派的道德其实也严厉得有点过度了,似乎有点不通情达理。不过,国家对国内所有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情理之处,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不是使用暴力,而是采取了以下两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国家应当对国内中等及以上身份的有钱人施压,叫他们全都去从事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并且,国家不给予教师固定的薪水,避免他们变得怠惰;另外,国家可以对较难懂的科学采取考试检测的制度。无论什么人,他在从事某种自由职业或者被提名为某种名誉有酬的职务候选人之前,都必须经过这种考试检测。如果国家强迫这一阶级的人研究学问,他们自己就可以很快找到很好的老师,那么国家也就不需要替他们提供老师了。对于狂妄和迷信来说,科学就是一针消毒剂,把社会上流人士从狂妄和迷信的毒害中解救出来。这么一来,下层人民也同样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第二种方法是促进人民的娱乐。迷信和狂妄的产生,常常是因为内心忧郁或悲观。而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乃至所有的戏剧表演都可以很容易地消除大部分人民的这种情绪。国家应当对专门从事这些技艺的人给予奖励,或任由其自由发展。对于煽动人民群众的狂妄者来说,他们一般都对公众娱乐非常惧怕和厌恶。因为娱乐给人们带来的快感,违背了他们煽动的目的。并且,戏剧表演常常会揭穿他们的诡计,使他们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所以,他们尤其讨厌戏剧。
如果一国法律对国内所有宗教的教师都一视同仁的话,那么这些教师和君主或行政部门,就不需要保持任何特定或直接的从属关系,君主或行政部门也不需要去管理他们职务上的任免。这时,君主或行政部门对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防止他们相互迫害,就像对待其他人民一样。不过,如果一国存在国教或统治的宗教,那么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那时,如果君主对该宗教的大部分教师不能进行有力控制的话,那么他自己也将永无宁日。
所有的国教教士都建立了一个较大的法人团体。他们共同协作并坚持自己一直坚持的精神,并且在一个人的指导下按照计划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法人团体,他们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完全不同,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持人民对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们用以下设想来实现这种权威。一是设想他们教导的所有教义是确实且最重要的;二是设想这些教义是摆脱悲惨的绝对方法。如果君主敢嘲笑或质疑他们教义中最细微的部分,或者保护其他嘲笑教义者的话,这些教士就会宣布君主亵渎神明,同时采用所有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归顺于其他君主。如果君主反对他们的任何要求的话,也会有相同的结果。不管君主怎样声明他的信仰,或者表达他对教会认为君主应当遵循的教义是如何服从,只要君主反对教会,他就会被判逆反之罪,说不定还要加上一个伪道的罪名呢。因为,宗教的权威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权威,宗教发出的恐怖行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恐怖行为。当国教教会的教师宣传颠覆君权的教义时,君主就只能凭借暴力即常备军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权威了。有时,常备军也不能保障君主永久的安宁,因为士兵常常也会被那些教义所腐化。例如,在东罗马帝国存续期间,希腊教士就曾在君士坦丁引起了多次革命;后来几百年间,罗马教士也曾在欧洲各地引起多次动乱。上述实例充分证明了这么一点:
如果一国君主没有控制国教或统治宗教的教师的话,那么他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
人们认为,俗世的君主无法管辖有关宗教信仰和其他有关心灵的事件。即使君主能够很好地保护人民,但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很好地教导人民。在上述信仰和有关心灵的事件上,君主的权威与国教教士们团结起来的权威相比,一般没有那么大。另外,保障社会的治安和君主的安全,也常常依赖于教士们关于上述事件所宣扬的教义。既然君主不能以自己的权威对教士们的决定直接表示反对,那么君主就必须拥有影响他们决定的能力。而影响他们决定的办法,就是让大多数教士对有些东西有所害怕,但对有些东西又有所期望。例如,他们害怕降职或处罚,希望获得升迁。
在所有的基督教会,牧师的薪俸基本上就是他们可以终生享受的财产。只要他们行为端正,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剥夺。如果这种财产的保留不是那么稳固的话,他们就不能维持对人民的权威了。试想,如果他们稍微得罪君主或达官贵人,就要被剥夺财产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们是朝廷的爪牙,从而也就不再相信他们的教导了。如果君主滥用暴力,以他们宣传煽动的教义为由剥夺他们的财产,那么这种迫害只会使他们以及教义的声望增加十倍,从而君主自身地位的危险也将增加十倍。所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暴力手段都不是治国治民的好方法;对那些仅仅要求一点点独立自主权利的人,更不能采用暴力的手段。因为吓唬这些人,反而会刺激他们的反感,从而引起更顽强的反抗。相反地,如果对反抗者宽容一些的话,也许就可以缓和双方的矛盾,使反对者们放弃反抗。例如,法国政府常常使用暴力手段强迫议会或最高法院公布一些不孚众望的公告,但最后的结果总是很少达到其目的。不过,它采取的将所有顽强不服的人全部送进监禁的办法,却非常有效果。斯图亚特王室的各君主,有时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来控制英国议会的一些议员,然而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抗。于是,各君主也就只好改变策略了。但现在的英国议会,可以说正被人用另一种方式控制着。
大概十二年前,奇瓦塞尔公爵曾经对巴黎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个小实验。那个实验充分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法国所有的最高法院都采用英国目前的方法的话,那么法院将更容易被操纵。不过,这种实验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如果说强制和暴力是政府最坏的统治方法,那么分权和谏言应该说是最好的统治工具了。但由于人性本身的傲慢,所以当人们不能或不敢采用坏的统治方法时,才会勉强采用好的统治方法。法国政府一般能够并敢于使用暴力的统治方法,因此它对一般好的统治方法不屑一顾。
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国教教会的牧师采取强制和暴力所产生的危险,要大于对其他阶级采取强制和暴力所产生的结果。牧师有自己的权利、特权和个人自由,只要他们和本阶级的人关系良好,那么就算在最专制的政府下,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比同等身份的有钱人更受人尊敬。无论是在巴黎温和的专制政府下还是在君士坦丁强暴的专制政府下,或者这中间各种程度的政府统治下,情况都是这样。不过,虽然牧师阶级很难用暴力加以强制,但却和其他阶级一样容易操纵。君主的安全和社会的治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君主操纵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就是不断提升他们自己的权力。
以前,基督教的制度规定:由各主教辖区内的牧师和人民共同选举主教。
不过人民这种选举权没有持续多久。即使是在享有这种选举权的时候,他们也大多是听牧师们的。在这种有关心灵的事件上,牧师们总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指导者。后来,牧师们就开始厌倦这种操纵人民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来选举主教要方便得多。大部分修道院也是一样,其院长也是由院中的修道士来选举的。在教区内,主教决定着所有下级任职人员的任命。也就是说,主教掌握了教会里所有的升迁权力。虽然这时君主对他们的选举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如教会对于选举和选举的结果有时会征求君主的同意,但君主还是不能直接操纵他们。这样,每一个想要升迁的牧师,都会去阿谀奉承教会中掌握升迁决定权的人,而不是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