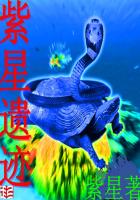自这个世界处于混沌之始,每个时代中都会伴随着一些神奇的事物被发现。自上个世纪以来,被发现的未知事件要比之前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多。在这个新的世纪里,越来越多的更为震撼人心的事物会被逐个揭示。一件新事物自诞生开始,人们从起初的不愿意相信,然后到开始希望能够做到,再到他们看到能做到--最终做到了,人们都奇怪为什么这在之前几个世纪就做不到呢。上个世纪,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思想--只是思想的本身--就和电池一样有威力--如同阳光一样美好,抑或是像毒瘤一样坏。允许一个伤感或者恶毒的念头进入你的大脑,就跟允许一个猩红热病菌潜入你的身体一样危险。假设它进入你之后你允许它存留下来,只要你还活着,你没准就永世无法痊愈。
但凡玛丽小姐的心中充斥了不顺心的想法、厌恶别人的酸溜溜的念头,下决心禁止任何东西取悦于她、吸引她的兴趣,她就是个面色发黄、病态的、疲倦的、不幸的孩子。但是,现实十分善待她,虽说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开始被推动着,受益无穷。当她的内心慢慢填满了知更鸟,牧尔上面挤满了孩子们的农舍,古怪易怒的老花匠本,可爱质朴的约克郡小女仆玛莎,春天和一天天慢慢活过来的秘密花园,一个在牧尔上长大的小男孩迪肯和他的“小动物们”,就再没有地方留给不顺心的想法了,那些想法改变着她的肝脏和其他的器官,令她面色发黄、身体疲倦。
但凡柯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只要一想着他的恐惧、虚弱以及对待他的人的憎恶,他就会想到肿包和早夭,他就是那个歇斯底里的、半疯癫的疑心病患者,也许他并不知道阳光与春天为何物,也根本不知道如果他努力尝试,他就可以好起来、自己站起来。但是当美丽的新念头把丑陋的旧念头代替,生命就又开始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了,他的血液健康地在血管里流淌,力量如同那奔涌的洪水在身体里流淌。他的科学实验是简单而又实用的,并没什么大惊小怪。更为令人惊讶的新变化会发生在身体上,如果当一个不顺心或泄气的念头来到他的心里,立刻就会有一个和谐、坚决的念头,来代替它。这两种念头根本势不两立。
当秘密花园复苏过来后,两个孩子也随之变得有了生气,而另外一个人在某个遥远而又美丽的地方游荡,在那挪威的大峡湾和深谷中、在那瑞士的崇山峻岭里,算起来,这个人把令人心碎的黑暗念头装满自己的内心已经整整十年了。他不曾勇敢过,从未尝试着用其他的想法去代替那黑暗的念头。就算他在蔚蓝色的湖泊中尽情地游荡,也始终想着它;就算他躺在四周盛开着犹如地毯般深蓝的龙胆花,花香弥漫的山谷中,他也始终想着它。当他曾经历幸福的时候,可怕的悲痛却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从此让他的内心塞满了黑暗,顽固地拒绝着哪怕一丝一毫的阳光穿透进来。他已经遗忘了他的家园,疏忽了他的责任。当他四处游荡时,黑暗笼罩着他的全身,看到他对于其他人来说就都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因为他一出现,就仿佛用阴郁毒化了他四周的空气。大多数未曾熟悉他的人以为他要么就是半疯,要么就是灵魂里隐藏着什么罪行。他是个高个子的男人,拥有着扭曲的面庞和驼着的背,每当到旅馆登记的时候,他填的名字都是:“阿奇博尔德·克兰文先生,米瑟韦斯特庄园,约克郡,英国。”自从他在书房见到玛丽小姐后,他旅行的地域便变得更加广大而遥远。
他曾到过欧洲最为美丽壮美的地方,但他在任何地方却都待不了几天。他喜欢选择最为宁静而偏远的景色。他曾到过层峦叠嶂之巅,峰顶入云;他曾俯瞰巍峨的群山,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群山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仿佛正在孕育整个世界。
然而这金色的光辉却仿佛从未染上他,直到有一天,他第一次察觉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他当时正在奥地利提柔省一个美丽幽静的山谷里,他独自一个人穿过那美到可以把任何人的心灵从阴影里净化出来的美景。但这美景却没有让他提起半点儿精神。走了很远后,他终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就跌坐在溪流边上的如茵苔藓上休息。那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涓涓溪流,穿过那芳香湿润的绿色,在狭窄的河道里快乐地奔流着。时而冒着泡越过石头、围绕石头,水声犹如低低的笑声。他看到鸟儿把头扎进溪水里轻轻地喝水,然后弹弹翅膀又轻轻地飞走了。溪流像有了生命一般,山谷本来就非常安静,但细小的响声让这里的宁静更加幽深。
阿奇博尔德·克兰文静静地凝视着清澈流淌的溪水,渐渐地觉得自己身心俱静,静如山谷。他想着自己是不是快睡着了,然而他却没有。他一边坐着一边凝视着阳光照耀的流水,眼睛开始看着东西的边缘在向外生长。一片精致的勿忘我长在离溪流不远的岸边,它的叶子被打湿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注视着这些花朵,他回忆起多年前他曾经也一样注视过这种东西。他温柔地想,这是多么可爱啊,这千万朵小小花朵组成的蓝色将是怎样的一幅奇景啊。他并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在一点一点慢慢注入他的心--注入、注入,直到有其他东西被轻柔地代替。仿佛甜美清新的春天就是从那一潭死水里开始的,升起、升起、升起,直到最终,完全代替了黑水。不过他自己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知道,当他静静地盯着那鲜艳娇嫩的蓝色,仿佛山谷越来越静。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坐了多久,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当他最后一动,醒了过来,他慢慢地起来,站在苔藓组成的地毯上,长长地、柔和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十分奇怪,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化解开来悄无声息地消散了。
“这是什么啊?”他近乎于耳语般地小声说道,手摸着前额头,“我觉得简直是--又重新活过来了。”
这个未知的感觉有多奇妙,我并不十分了解,也无法解释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别人也无从知晓。他自己根本不明白--但是,在事后的几个月里,他都清楚地记得这个奇怪的时刻,等他重新回到米瑟韦斯特庄园后,他偶然发现,就在那天,当柯林进入秘密花园时喊出:
“我要永永远远地活下去!”这异常的寂静在他身上保留了整整一夜,他这一觉睡得非常安宁,可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他并不知道这份平静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到了第二天晚上,他早已为他那些黑暗而奇怪的想法打开了大门,它们列着队冲了回来。他离开了幽静的山谷,继续着他的流浪之路。但是,让他奇怪的是,有几分钟的时间--偶尔能达到半小时--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内心黑暗的想法似乎又自己抬起头来,他知道自己不是个死人,而是个活人。慢慢地--慢慢地--由于某种他不知道的原因--他正在伴随着那个花园一起缓缓地“活过来了”。
当灿烂的夏天转变为深金色的秋天后,他去了寇眸湖。在那里他做了一个可爱而又有意思的梦。晴朗的蓝天下,他躺在水晶蓝的湖面上,或者在山坡上柔软浓密的青草翠林之中踱步,一直到走累了为止,就能睡着了。不过到这时,他的睡眠质量已经开始变得很好了,他知道,他对梦已经不再是一种恐惧了。
“也许,”他心想,“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强壮了。”
的确是变强壮了,但是--是因为有那些不常见的平静的时候,当他的想法开始转变的时候--他的灵魂也在慢慢变得强壮。他开始想到米瑟韦斯特庄园,思量着是不是该回家了。有些时候,他依稀地想着他的儿子,并问自己,当他再次站在四柱雕着精致花纹的床边俯看那张睡着了的轮廓清晰、面似冠玉的瓜子脸,黑睫毛紧紧镶在那双紧闭着的双眼周围,这时候他会有什么感受。他退缩了。
有一天,很反常地,他走出了很远,等他回来的时候,月儿圆圆地高挂天际,整个世界都是紫色的阴影和银色。湖水、湖畔和树林的宁静是如此的美好,他没有回到他居住的别墅。他走向水边的一个藤树荫翳的小露台,在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将所有夜晚里天堂般的香气通通吸入。他感到那股奇特的平静正悄悄地把他笼罩,越来越深,直到他渐渐沉入睡梦。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静静地睡着了,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梦来。他的梦真实得根本感觉不出来是在做梦。他后来回忆,那时候他认为自己非常清醒、非常警觉。他觉得自己坐在那儿,闻着那晚开的玫瑰的芬芳,听着脚边的湖水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这时一个呼唤的声音传来。声音甜美、清澈、快乐而又渺茫。听起来非常遥远,但是他听得却很清楚,仿佛就在他身旁一样。
“阿奇!阿奇!阿奇!”那声音若隐若现地喊道,如此的甜美清澈,“阿奇!阿奇!”
他记得自己差点儿跳了起来,那声音是如此真实,仿佛他自然就应该听到一样。
“莉莲!莉莲!”他回答道,“莉莲!你在哪里啊?”“我在花园里面,”声音传了回来,如同金笛一般,“我在花园里面!”之后这个梦结束了。但是他并没有醒来。他睡得沉沉的,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当他真的醒来的时候,晨光明朗,一个仆人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他是一个意大利籍仆人,如同别墅里面其他的仆人一样,习惯于接受外国主人指示的任何怪事,坚持不问主人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和回来,他会在哪儿睡觉,是否会在花园里四处游荡,或者整夜都躺在湖上的一艘船中。那人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有若干信件,他静静地等着克兰文先生拿起来。他走了之后,克兰文先生手里捧着信件坐着,边读边看着湖。奇怪的平静依旧笼罩着他,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轻松,而那些曾经发生的残酷的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似乎有什么改变了。他在回忆那个神奇的梦--真实的--真实的梦。
“肯定在花园里!”他惊疑不定地说道,“在花园呢!但是门锁着,钥匙被深深地埋在了地下。”
几分钟以后,他瞟了瞟手中的信件,看到最上面的一封是英语信件,是从约克郡寄过来的。收信人和地址都是用朴素的笔迹写的,但他并不认识这笔迹究竟是谁的。他打开信,几乎没来得及看写信的人是谁,第一行字就牢牢抓住了他的注意力。
亲爱的克兰文先生:我是苏珊·索尔比,上一次在牧尔上对您说过的那些冒犯的话,请您不要介意。
那次我说的是有关玛丽小姐的。今天我要再次冒昧开口请求您了,先生,如果我要是您的话,我一定会回家来。我想要是你能回来的话,我们都会很高兴的,而且--假如您能原谅我的话,先生--我想您夫人也会希望您能回来的,如果她还在的话。
您最忠诚的仆人苏珊·索尔比
克兰文先生将这封信反复读了两遍,才放回了信封里。他反复地想着那个梦。
“我要回米瑟韦斯特去,”他说道,“对,立刻就走。”
他穿过花园来到别墅,命令皮切尔为他做回英格兰的准备。几天之后,他终于重新回到了英格兰,在长长的火车旅途中,他惊觉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的儿子,过去整整十年中,他从未如此思念着他。在那些岁月里,他只希望能够马上忘记他。但现在,尽管他没有特意想念他,但是关于孩子的回忆却不断地涌进脑海。他清楚地记得那些黑暗的日子,他像个疯子一样四处狂奔,因为孩子还活着而母亲却死了。他曾经拒绝去看望他,等他终于过去看他了,才发现他是那么一个虚弱、可怜的小家伙,几乎所有人都断定他活不了几天。但是让照顾他的人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坚强地活了下来,然后每个人又都断定他肯定会长成一个跛脚、畸形的怪物。
他从来没有刻意想做一个坏的父亲,但是他从不认为自己像是个父亲。尽管他一直请来医生、护士照顾他,但是他把自己埋进了自己的不幸之中,连想起自己的孩子都感到畏缩。离开米瑟韦斯特庄园一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看到悲苦的小家伙倦怠、冷漠地抬起长满黑睫毛的一双灰色大眼睛,和他曾经爱慕过的那双明亮而又快乐的眼睛如此相似、又不那么相似,他没有勇气一直看着它们,他转过身离去,面如死灰。从那之后,他很少见到他,除非他在床上睡觉,他只知道他的确是个残疾人,脾气暴躁、歇斯底里、精神上几乎疯了。要让他更好地避免危险的狂怒,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每个细节上都要顺着他来。
这一切的回忆并非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是,随着他乘坐着火车蜿蜒地穿过山路和金色平原,这个正在“重获新生”的人开始用新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他思考得很清醒、很久、很深。
“也许我整整错了十年。”他对自己说道,“十年确实太长了。恐怕这一切都太迟了--实在是太迟了。这些年来我都是怎么想的啊!”
当然了,这完全是错误的魔法--一开始就说是“太迟了”。就算柯林都能把这些告诉他。不过他完全不懂得魔法--不论是白的还是黑的。这个他还要自己学习。他想知道,苏珊·索尔比鼓足勇气来给他写信究竟是不是只是因为这个母性的人意识到了男孩的病更加严重了--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他不是被那个神秘而又平静的咒语迷住、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现在说不定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呢。之后那股平静给他带来了一种勇气和希望。他没有屈从于悲观的念头,而是自己在努力尝试着相信更乐观的东西。
“会不会是她看出来我有可能能够对他产生好的影响了,就能控制他?”他心想,“在回到米瑟韦斯特的路上我得去看看她。”
在穿过牧尔的道路中,他把马车停靠在了农舍门前,七八个正到处玩耍打闹的孩子,聚拢到了一起,行了七八个友好礼貌的屈膝礼,并告诉他,妈妈一清早就去了牧尔的另外一头,帮助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女人。“我们家的迪肯,”他们主动介绍道,“到了庄园,在那里的其中一个花园干活,他每周都要去那里几天。”
克兰文先生看了看围在自己周围的这一群结实的小身子和他们圆圆的小红脸蛋儿,每一张都各有特点地咧着嘴冲他笑着,他惊讶地发觉他们都十分强壮、健康。他对着他们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金币,递给最大的“我们家的伊丽莎白·爱伦”。
“要是你把它分成八份,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半个银币。”他说道。然后在爽朗的笑容、咯咯的笑声以及轻快的屈膝礼的包围之中,他就坐车离开了,身后留下那些小孩子们的狂喜、轻推和高兴的蹦蹦跳跳。驾车经过美丽的牧尔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为什么这里会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呢?这种感觉他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有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万物复苏、百花齐放。心里面暖起来,他越来越靠近那座高耸巨大的老房子了,它庇护着同一血脉的人们已经六百年了。上一次他是怎么驾车离开的啊,一想起里面上百间屋子上锁、小男孩静静躺在垂着金银织锦缎的雕花四柱床上,他就不寒而栗。他会不会发现自己已经好转些了,自己能不能不再对他畏缩呢?那个梦是那么的真切啊--那个从远方传回来的声音是多么的美好而清澈啊。“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我要找钥匙去,”他说道,“我要把门打开。我一定要--虽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他抵达庄园后,仆人按照以前通常的仪式接待了他,他们注意到他看上去已经显得好些了,他并没有去他经常住的、一直由皮切尔照料的那个偏远的屋子。他去了书房以后,派人请来莫得劳克太太。她来到他这里以后,多少有些激动而又有些惊慌失措。
“柯林少爷现在怎么样,莫得劳克?”他询问道。“嗯,先生,”莫得劳克太太回答道,“他……他变了,可以这么说吧。”“恶化了吗?”他试探道。
想不到莫得劳克太太的脸居然红了。“嗯,你看啊,先生,”她试图解释道,“克兰文医生、护士,包括我都没办法弄明白他。”“怎么会这样呢?”
“实话说,先生,柯林少爷也许是好转了但也可能是恶化了。他的胃口,先生,简直是难以理解--他的性子嘛--”
“他……是不是变得更加--更加难以理解、更加古怪了?”她的主人眉头打着结,紧张地问道。
“事情正是如此,先生。如果你把他跟过去相比的话,确实性格是变得非常古怪了。他过去是什么东西都不吃的,可是突然之间他就开始变得特别能吃了--然后他又突然停止了,饭菜也像过去一样一口没动被送回来。先生,你也许不知道,他从来不准别人把他带到外面。要让他走到外面去,那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简直是能让人像一片树叶一样战栗。他会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克兰文医生都说连他都不愿意承担强加给他的责任。哦,先生,他事先毫无兆头地发了一场最厉害的脾气,之后没多久,他突然要求每天要被抬到屋外去,坐着他的轮椅,和玛丽小姐以及苏珊·索尔比的儿子迪肯散步。他迷上了玛丽小姐和迪肯两个人,迪肯带来了被他征服的动物,还有,先生,他现在每天都要在户外从早上活动到晚上。”
“他看起来怎么样?”这是下一个问题。“如果他饮食正常,先生,您肯定以为他在长肉--可是我看可能是一种浮肿。他和玛丽小姐单独待在一起,有时候会奇怪地大笑。他以前可是从来不笑的。要是您允许的话,一会儿克兰文医生马上过来。他这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
“柯林少爷现在在哪儿呢?”克兰文先生问道。“先生,他在花园里。他总是在花园里待着--不过他不准任何人靠近,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看着他。”克兰文先生差不多没听到她最后的话。
“在花园里,”他说,等他支走了莫得劳克太太,他站起来一遍遍重复着那句话,“在花园里呢!”
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让自己回过神来,回到清醒状态,等他觉得回到地球之后,转身走出了房间。他像玛丽一样走了出去,穿过灌木丛里深藏在月桂和喷泉花床之间的大门。喷泉正喷涌着泉水,四周环绕着鲜亮的秋季花卉。他穿过草地,走进爬满常春藤的墙边那条长长的走廊。他的速度不是很快,眼睛盯着路走得很慢。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好像正在被拉回他那久久寻觅的地方。随着他越走越近,他的脚步渐渐越走越慢。尽管常春藤厚厚地生长在墙上,可他还是知道门大概在哪儿--但是他不知道那把钥匙确切的埋藏地点。
于是他停下脚步站在原地不动,他环顾四周,几乎是在他停下来的那一瞬间,他蓦然一动,问自己是否是身在梦中。
常春藤密密地爬满门上,钥匙埋在灌木丛下的土壤中,十年寂寞,尽管花园里面有声音,但没有任何人曾经穿过那道门。同时,奔跑踢踏的脚步声正从里面传出来,仿佛有人在树下绕着圈追赶,还有奇怪的压抑低沉的人声--好像是捂着嘴高声咆哮呼喊着。听起来好像是年轻人的欢笑,是孩子们那种不可抑制的笑声,他们努力不让人听到,可是由于他们过度兴奋而累积起来,每隔上一会儿就会大笑爆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做的都是什么梦啊--看在天堂的分儿上他都听到了些什么啊?他是不是丧心病狂了,以为自己听到了其他人的耳朵听不到的声音?这是不是就是那个遥远但十分清晰的声音想说的?
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那是难以控制的时刻,当那些声音顾不上安静。脚步越跑越快--他们正在朝花园门口奔来--有一个急速、有力、年轻的呼吸声,一道恣意纵情的笑声无法自抑地大声爆发出来--墙上的门被重重地推开,一层常春藤来回摇晃,一个男孩全速穿过了常青藤冲了过来,却没看见那个外来者,几乎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
幸好克兰文先生及时伸出了双臂,使他不至于因瞎头瞎脑地撞上了他而跌倒,当他把他抱稳了,他却真正地停止了呼吸。
他是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男孩。他生气勃勃,经常的运动让他红光满面。他把浓密的头发从额头上甩上去,抬起一双美丽而独特的灰眼睛,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男孩气的欢笑,眼眶上镶着流苏般黑黑的睫毛。就是这双迷人的眼睛让克兰文先生屏住了呼吸。“谁--什么?谁?”他惶恐地问道。
这并不是柯林预计的--这更不是他原本计划好的。他从未想到过他们会这样相逢。但是,这样也许会更好。玛丽刚才在和他一起跑,也冲出了大门,看起来他把他自己弄得比任何时刻都要高大--起码高上好几英寸。
“爸爸,”他说道,“我是柯林。你没有办法相信吧。连我自己都几乎无法相信。我就是柯林。”
他同莫得劳克太太一样,不理解他爸爸是什么意思,此刻克兰文先生正在匆忙地说着:“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是的,”柯林急着说道,“这就是花园的神奇功效--还有玛丽、迪肯、小动物们--以及魔法。没有人知道。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你来再告诉你。我好了以后,我跑步能赛过玛丽。我想当一个运动员。”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像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他的脸涨得通红,由于心情急切,他的词句有些颠三倒四--克兰文先生的灵魂正由于难以置信的欢乐而颤抖了起来。
柯林把他的手伸出来放在了父亲的胳膊上。“你难道不高兴吗,我的爸爸?”他最后说道,“你难道不高兴吗?
我要永永远远地活下去!”克兰文先生把双手放到了男孩的肩上,攥着他不动。有一阵他甚至不敢试图说话。
“带我去花园看看吧,我的孩子,”他终于说道,“将一切都告诉我。”于是他们领他走进了花园。此刻,这个地方是秋色狂欢的海洋,金色、紫色、紫蓝以及火焰一样的红色,四处都盛开着一丛丛的花朵,百合簇拥在一起--白色的百合,以及白色和深红相间的。他清楚地记得第一丛花是何时种下的,在一年的这个季节里,它们迟到的光彩开始显现。玫瑰向上攀岩、垂挂,聚成一串串吊下来,阳光把树木晕染得更深,让人觉得仿佛是站在一个树藤荫翳的黄金庙堂之中。新来的人静默地站着,就如同孩子们初来时一样。他反复地环顾四周。
“我原本以为它们都已经死了。”他说道。“玛丽原本也这样以为,”柯林说道,“但是它又活了过来。”
之后他们全部坐到了他们的树下--除了柯林之外,他希望站着讲故事。
这是他所听到过的最为奇幻的事,阿奇博尔德·克兰文心里想。故事以男孩的行事风格、任性随意、滔滔不绝讲述出来:神秘的魔法,野生动物,春天到来,被侮辱了自尊的小少爷站起来,迎面反击本。神奇的伙伴儿,一起玩游戏,小心保护这个大秘密。听故事的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有时他不笑的时候眼泪也会涌上来。这位运动员、演讲家、探险者真是一个可笑、可爱、健康的年轻人。
“现在,”他在故事的末尾说道,“不必再保守这个保密了。我敢说他们再见到我,肯定会吓得昏倒--可我再也不会坐回到那个椅子上了。我要和你一起回去,我的爸爸--去房子里。”
本的职责令他鲜有机会离开花园,但是这次他编了一个借口,说要把蔬菜运到厨房去,因此被莫得劳克太太请过来到仆人大厅喝一杯啤酒,所以那时他正好在场--就如他渴望的那样--见证了米瑟韦斯特庄园在这一代人里经历过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有一扇对着院子的窗户打开了,露出了一抹草地。莫得劳克太太知道本是从花园里来的,猜测他没准儿瞅见了主人,甚至碰巧看到了柯林少爷。
“你看见他们了没有,本?”她问道。本拿开嘴边的啤酒杯,用手背抹了抹沾满啤酒的嘴唇。“哎,我见到他了。”他态度狡猾却又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他们两人你都看到了?”莫得劳克太太试探着问道。“是啊,两个我都看到了。”本回话,“多谢你啦,夫人,我能再满上一杯吗?”
“在一块儿呢?”莫得劳克太太赶忙兴奋地把他的啤酒杯子倒满。“在一起呢,夫人。”本一口灌下刚刚倒上的一杯啤酒。
“柯林少爷在哪儿呢?他现在看起来怎么样?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内容?”
“我没听见他们的对话,”本说道,“再说我只是站在梯子上从墙头上看。不过我可以跟你说,外头一直有情况在发生,只不过你们在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你想知道的,你很快就会知道。”
不到两分钟,他喝完了最后一滴啤酒,庄重地挥了挥杯子,指向露出一抹草地的那个窗户。
“看看那儿吧,”他说,“你如果好奇的话。看看是谁穿过草地走过来了。”
莫得劳克太太定睛一看,顿时把双手甩得高高的,尖叫一声,所有男仆和女仆都听到了她的叫喊,冲过了仆人大厅,站着往窗外看,他们的眼珠子全都快要掉出来了。
米瑟韦斯特庄园的主人穿过草地走了进来,他的模样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在他旁边,有一个头高高昂起,眼睛里充满欢笑,走得和约克郡的任何一个男孩一样有力气、一样稳当的男孩子,他就是--柯林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