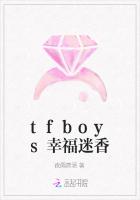地下室的那间公寓,查理不在的时候被关闭了。现在他重新回到这个属于他的小天地,从那个老旧的病房搬回了自己的私人治疗室,门前的那片草地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地方长期无人居住的样子。查理将每班轮岗之间的那点儿时间都用在呵护自家土地、将杂草变成花园的工作上了。他跟那些埋在土里的种子一同沐浴在骄阳之下,那些花朵需要他的照顾,在那些灌木花草之间,查理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说了算。
在沃伦医院,他偶尔会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门里或是在阳光照射的停车场上瞥见米歇尔的身影。每当查理看着她的头发飘动在风中,缓缓走向自己的车时,总是强忍住上前叫住她的冲动。无论是何种情况,米歇尔总是看不到他,或是假装没看到他。其实这无所谓,因为就算她确实看见他了,限制令还是会阻止他们一同出现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这一点,查理的新上司康妮·川普勒护士长也特意在他回来的时候叮嘱过。查理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下定决心做好自己。康妮一遍又一遍地向查理不停地叮嘱着那些新规矩,每一次他都用面无表情的方式搪塞过去。他知道自己把同米歇尔的关系搞砸了,缄默不言是他能给出的最好的结果了。反正,康妮将他调到了隔壁一个很不错的岗位当差,在遥测病房,那地方有着不为人知的好处。
遥测病房在整个病区的中部,有点类似于处在“地狱”般需要紧密观测的重症监护病房和“天堂”般酒店式管理的正规普通病房之间的“炼狱”。这些病房主要住的是心脏病较为严重但已经趋于好转的人,是为了防止状况稳定的病人突然发生急转直下的情况。这里的病人都是需要仔细照顾、用心观察的。
当然,在病人看来,“炼狱”的生活还是格外令人厌恶的。他们被各种各样的导线和输液袋困扰着,好像牵线木偶,不得自由。顺着那些各式各样的导线看去,连接的不是哔哔作响的机器就是闪烁着亮光的测量仪,有些时候是一抽一拉的呼吸系统,就是那种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玩意儿,显得特别夸张,充满了戏剧性。遥测病房的病人们没有几个需要用镇静剂的,所以往往这样的场景或多或少会让他们觉得有些紧张,紧张得稍微过头一些,血压就会飙升,而对应的仪器便会响得比之前还夸张。一般这种时候,就该查理登场了。他的主要技能就是教育病患,他对这种一对一的教学还是很津津乐道的。对于这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查理可以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全方位介绍,对这些各式各样的仪器,他有一套专业的说辞。他解释说:“是的,你们这些吓坏了的家伙,比如你们迷上了测谎方面的仪器,至少对其中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当你们认真去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后,测谎仪一点儿都不可怕。插在你们身上的这些玩意儿也一样,当你们知道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你们也就不这么害怕了。”话说回来,查理确实对测谎仪有很深的了解,其实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大多数警察还要了解。
心电图(EKG)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血液从心脏的顶部流入,再从底部流出,通过心房、心室推送。每一次挤压都会触发一次电脉冲,心电图就是将这些电脉冲翻译到图纸上,这一切都是由一根带墨水的针滑来滑去完成的。
通常情况下,查理都是一边给那些发皱干瘪、长着稀松的灰白毛发的乳头上夹电极,一边解释这些事儿。
在健康的心脏里,肌肉的运动会形成有规律的波浪,血液通过心脏就好像农民用手从奶牛的乳头里规则地挤出新鲜的牛奶一样。从心电图上看,一个正常的脉冲看起来像是山峰。所有有关心脏的信息就藏在这些山峰中。有些看起来格外尖,或是在峰顶很松散,抑或有缺口,有些看起来则跟地震后似的。看着这些图纸,护士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在皮肉的下面、肋骨的后面,心脏像一袋子被抓起来的老鼠,兴奋地颤动着。
查理这次准备离婚的过程已经为他在这个春天带来了两次测谎仪的检查。头一次是来自阿德里安娜的指控,她说查理是一个酒鬼,甚至在看孩子的时候都不忘喝酒。除此以外,还有她向警方申请的禁止令,是在她报警申诉家庭暴力之后发生的,这成了她争取孩子全部监护权的核心论证。用测谎仪是查理的主意。测试被安排在6月18日,正好是查理从灰石出院两个月以后。根据机器显示,他说的话都是实话,查理顺利地通过了测试。但这只是他在法庭上需要经历的所有奇怪的战争中最微小的一次胜利。就在12天之后,阿德里安娜最终成功地获得了针对自己丈夫的禁止令。
如果说沃伦县的家庭法院系统在这场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没有让查理占上风,那北汉普顿的常规法院也没偏向他。查理在那个法庭上被控跟踪、破门而入、侵犯和骚扰。这是个犯罪的指控,比他离婚的局面复杂多了,面对的还是个非常激进、令人生畏的检察官。查理本来打算像处理离婚事件那样继续为自己辩护,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了。
查理需要开具财务状况来证明自己只有能力请得起一位公共辩护律师。他将所有外部必需花销统统列出来,诸如每月1460美元的抚养费、心理咨询费用、信用卡最低还款额度。他好像忽略了每日最基本的个人花销,单子上没有房租和饭钱,对于他来说,这些滑稽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必须满足的。查理没有将它们列在单子上,就是觉得这不是必须存在的。他算是彻底破产了,在法院看来他的生活水平在净收入的支撑下维持得再健康不过了,所以公共辩护律师的申请被拒绝了。现在他不得不自己花钱找个代理律师来,这让他过得更加窘迫。他从黄页上翻找出一个律师,付了钱。但这段关系仅仅维持了三天,那律师就放弃了。他声称查尔斯·库伦的性格让他做这个案子太“艰难”了。由于无法在庭上发泄自己的怒火,查理将这一切怨愤转嫁到自己的这位前任律师头上。他给法庭写了一封情绪暴躁的长篇信件,将自己与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对比。“一个护士会中途放弃、离开自己的病人吗?!不,他不会。为什么不?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专业的!”这封发泄的投诉信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从目前的状况看来,除了代表自己出庭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查理对法庭几乎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8月10日那天,他放弃了,承认了自己骚扰和侵害的罪行。法庭给出的判决是罚款和缓刑,没有送他进监狱。他可以自由地回家去了。到家之后,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这次在药片和酒的作用下,他开车跑到了沃伦医院的急诊室。这种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再熟悉不过的无助戏码或多或少帮他缓解了一些压力,就好像打喷嚏或是其他的一些日常举动一样,虽然有效,不过持续的时间很短。第二天晚上医院就让查理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下自己驱车回家了。
即便才8月份,地下室公寓却出乎意料地冷,屋中唯一的声响就是壁炉上那个座钟指针走动时发出的沉闷的嘀嗒声。米歇尔有电话,他也知道她的家在哪儿,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他违反自己的禁止令。他试图让自己保持缄默,但终究还是需要开口说话的。他听着座钟的声音,牙齿伴随着时钟的节奏上下磕碰,哐哐哐……两只眼睛盯着前方桌子上的酒瓶轮流地睁了闭、闭了睁,看着它在自己面前左右变换着跳起了舞。就在他开始奋笔疾书给法官写一封长长的信件时,他的手肘在换行的过程中不停地敲击着厨房的塑料贴面。
“米歇尔·汤姆林森和我之间发生过性关系。”他如此写道。法官没有真正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起码没有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了解他。但是查理却将这些法官看得很透彻。他在信中继续写道,那些人曾经是自己的病人。就在圣巴拿巴烧伤病房中心,为了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些脆弱的人在他的面前被脱去了长袍,每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着氧气的获取。他一直写着,写到天空被清晨的朝阳浸染了一抹亮色。他刷着牙,往池子里吐了一口鲜红的口水。然后他去见乔治,那个法官任命的家庭服务顾问,那个决定着库伦和他的孩子们未来的人。
查理非常想留孩子们在身边,尤其是现在。这些小孩儿无疑会成为查理最真诚的粉丝。他们是需要照顾的,是有依赖性的,正如那些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护理的病人一般。他坚信自己有一天真的会成为孩子们期待的那种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富有同情心、能照顾他们的人。确实在某些人眼中他就是这样的。比如一些同为护士的同事,比如他的母亲,比如曾经的阿德里安娜以及米歇尔。也许,他思忖着,如果能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他是可以让他们爱上自己的,他们也会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查理得到了他们的关注,获取了满足感,他也许就不会做什么傻事而冒险失去他们了,也许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再给医院那些像纳托丽女士那种无辜的病患下药了。查理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一名好护士,一个乔治和家庭法院都乐于看见的好男人。乔治最后给出的建议将会是成就这种潜在未来的关键,所以每次在进行这些强制性访谈的时候,查理都会警告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精神状态良好。
当然了,对于查理一直在杀人这件事,乔治确实一无所知,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查理过于频繁地尝试自杀,或是经常用这种方式装腔作势地闹一场。乔治还从库伦的文件中注意到自杀的行为是“最严重、最终极的虐待、放弃手段,此等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可能会作用于其子女”。过了几天,阿德里安娜的律师就在家庭法庭上使用了这份报告,综合查理酗酒的其他证据,以及阿德里安娜在因家庭暴力报警时所做的笔录留下的证词—“如果将他和我们的女儿单独留在一起,很可能会对他本人及我们的孩子构成生命威胁”,查理没有一点儿还击的余地。唯一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庄严的舞台,只剩下医院一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