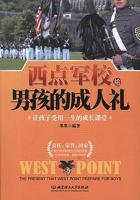两日后,我们已经上了纳木那尼峰的雪线。虽然我们商讨的结果是甩掉他们拴着我们鼻子的绳索,坚定我们的自由意志,以旅游探险的形式先征服纳木那尼峰,再去冈仁波齐峰伺机而动。为了突出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没有选择前人走过的路线,而是随便的找了一个冰川终碛就开始上行。
虽然这样我们表面上不用背负傀儡的骂名,但我知道,这确实是一个糟的不能再糟糕的决议。我们心里谁都清楚这还是换汤不换药,被人家引导着,同时还又背负了额外的一个自欺欺人的包袱。
我用匕首轻轻一挥,一朵冰蘑菇应声而落,溅的我满头满脸都是雪水。但好歹到了冈仁波齐峰,要不要不择手段,是由我们自己来执行的,不行就放弃,因为那几乎不是人力能做到的,不然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在心里这样开解着自己!
我又一个旋风腿踢落了一朵冰蘑菇,感觉非常的带劲。这是冰川的前沿,这样的冰蘑菇到处都是,不规则的分散在如巨大的堡垒般的终碛后方不远处的冰舌上,再往上就是继续融化着的冰。融化了的冰水汇聚成一条条溪流,从冰碛层上潺潺流动。我们踩着大小不一杂乱的岩块而行,并不是特别的难走,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一些不稳定的石块滑倒,而且上面未融化的冰雪并不见得纯白,上面铺了薄薄的一层灰土,使得雪层看上去很脏。
傍晚时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到冰天雪地的世界。厚厚的雪层间交叉着千沟万壑,这让我们的旅程变得开始艰难,看着天堑一样巨大沟壑,我们不得不改变了攀爬的路线,希望能从边缘绕过这一段冰川,等过了这一段,再返回到冰川继续前行。
然而要从边缘过这一段冰川,必须先攀上两边的峭壁,因为从冰川上我们能看到峭壁的上方就是一条山脊,沿着冰川源头延伸着。在山脊上宿营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赶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重新下到冰川上。时间上的紧迫让我们的攀登惊险万分,幸好我们攀岩的基本功还算扎实,但雪山攀岩不同于普通攀岩,峭壁上多的是冰凌和雪窝,非常的滑溜。经过千难万险,总算安全抵达山脊,然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大风说起就起,一开始还只是偶尔夹杂着一些山脊的粒雪,不一会儿狂风就开始漫卷雪花,吹的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们只能戴着风镜,伏低身体在山脊上迤逦而行,戴着风镜能见度就非常的低,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几乎是自杀行为。我们最后只得拿出冰抓,匍匐着爬行通过一段山脊后,下面的冰川看起来也并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刚才一样沟壑纵横。但是我们现在必须下去,即便是冰川表面没有任何的改观也势在必行,天已经快完全黒了。
我们利用一块突出的岩石,绑好登山绳,我和牛玲先下到下面的冰川,脚下的感觉还算结实,并没有裂隙,我们的心也就稍微安定了点。小个子解开绳索,将整条绳子对折平分,然后在岩石上绕了一圈,垂到我们面前,我和牛玲抓住一头,小个子沿着另一段绳索攀爬下来,落地后,一拉一端的绳头,整条绳子都滑落下来了。我们收好绳子,马上开始搭帐篷,这是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风实在是太大,光拉紧绳子就已经使我们累的脱力了,狂风还刮跑了我们一个帐篷。我们累的气喘吁吁,都瘫倒了。
这种天气下露天过夜,第二天看到的必定是三块冰坨子,我们又选的是人迹罕至的未开发路线,估计我们要永远的被冰葬在这纳木那尼峰上。我们在雪峰上的生存经验无限接近于零,躺在冰层上喘了半天也没点头绪,这种地方没个经验丰富的本地向导真是非常的要命。
牛铃郁闷道:“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实在不行,咱们就地挖个雪窝子,窝上一夜。好歹也能挡挡风。”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我和小个子也想不到别的办法,所以不管可不可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根救命稻草,于是说干就干,拿出工兵铲甩开膀子就开挖。表层的冰非常的硬,但是下面完全就是非常疏松的雪,我们费劲挖开一个缺口后,挖起来就容易很多,跟铲细沙就没什么区别了,不多一会儿我们就挖了一个深达二米五,三米见方的一个雪坑。底下铺上几层防潮布,把我们的装备包全部丢了下去,干完这些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草草的啃了几块压缩饼干,就钻进睡袋里,拿出两张熊皮,半垫半盖,别说这个办法效果居然非常好,风几乎吹不进来,雪坑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冷,反而感觉还挺暖和。我们实在累趴了,表扬牛玲的话说到一半就睡过去了。
不过在雪坑里睡觉仨爷们都是生平第一遭,也不知道他们睡的怎么样,反正我睡一点都不踏实,闭眼没多久就噩梦连连。就这样半梦半醒的睡,心想总比露宿要强的多。半夜里,我正做着乱七八糟的梦,突然就感觉自己的床往下一沉,一下子就把我惊醒了过来,一骨鲁就坐了起来,迷迷糊糊的四周望了望,却看到他们两个也坐了起来。我没头没脑的问道:“你们也梦见自己的床塌了?”
我们上方狂风大作,犹如许多厉鬼在齐声嘶吼,听着让人毛骨悚然,大团的雪花不断地滚落下来,我们的睡袋熊皮上都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
他们眼中写满了惊惧,牛铃似乎一下子变得很清醒。
“哪有三个人都一起梦到一样的结果的,****的不会是雪崩了吧,安静。”他说完,紧张的做了个禁声的手势,“屏住呼吸,仔细听!”
我们都大气不喘的听了一阵,最初除了厉鬼一样的风吼声,什么也听不到。这时我也已经完全清醒了,憋的我呼吸都有点不畅了,就长出一口气道:“你小子,正是吓死人不偿命,也许只是旁边的雪层裂开震动了一下。”
“震动哪有这么大动静,这他娘的跟翻船了似得。”牛铃显然觉得我们解释太过牵强,“不行,我得上去听听,蹲下,搭个人梯。”
我骂道:“你小子跟小牛犊似得,被你一踩,我半条命就去了,要上也是我上!”说完我一把把他摁低身子,一脚就踩到他肩上。我脑袋刚探出洞口,那鬼叫声马上就没有了,就感到大块大块的冰碴子没头没脸的砸过来,同时听到一种雷霆万钧般气势的隆隆声由远及近,一下子仿佛就已经到了我面前。我大叫一声:“****!”顾不得通知牛铃低下身子放下我。一下子就跳到坑底,面如土色结结巴巴的说:“可……能真的雪……崩了,这……下埋进咱……们自己挖好的棺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