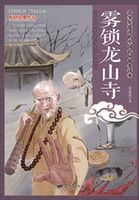第二部4
“这样我们便了解到这个病例的真正病因了,”弗朗茨说,“多姆勒告诉沃伦说,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病人,条件是他必须同意无限期避免与女儿见面,时间至少是五年。沃伦的精神首次垮下来后,他似乎主要担心这件事会不会泄露出去,传回美国。”
“我们为她规划了一个日常治疗方案,希望等着观看效果。预期的治疗效果不佳——这你是知道的,在这个年纪上,治愈率很低,即使是所谓的社会治愈率,也很低。”
“开始的时候,那些信看上去很糟糕。”迪克表示同意。
“很糟糕——非常典型。我很犹豫过一番,才准许最初那些信从诊所发出去。后来,我认为,让迪克了解我们这儿搞的工作是有益处的。你真好心,对那样的信还作了答复。”
迪克叹了口气。“她表现得那么好——在信里写进那么多责骂自己的话。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只能说:‘做个好姑娘,要听大夫们的话。’”
“那就足够了——因为她因此能想着外面的某个人。有一阵子,她什么亲友关系都没有——只有一个与她并不亲密的姐姐。此外,我们在这儿读她的信也能从中了解她——那些信是了解她状况的一扇窗口。”
“听到这些我很高兴。”
“你现在一切都知道了?她觉得自己是个同谋犯——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案件中,不过我们想要重新估价她的最高稳定程度和个性的最大力量。最初出现的是这样一个震动。那时,她去上一个寄宿学校,听到女孩子们谈论——纯粹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她产生了自己并不是同谋犯的念头——从那一点上,就很容易滑进一个幻想世界,在那个幻想世界中,越是受到喜爱和信赖的男人,就越邪恶……”
“她直接进入那种恐怖状态了吗?”
“没有。其实,到了十月份她开始显得正常时,我们却觉得陷入困境了。假如她是个三十岁的人,我们就会让她自行调整,但是她还那么年轻,我们担心她的内心扭曲状态会就此定型。所以多姆勒先生便对她坦白地说:‘你现在的职责是为了自己。这绝对不是说你已经走到了尽头——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等等。她的脑子的确好极了,所以,他就让她看一点儿弗罗伊德的书,并不给她看很多。她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们把她变成个这里的宠儿了。不过,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他补充说。接着,他用迟疑的口气问道:“她最近写给你的信是她直接从苏黎世寄出的,我们一直想知道,她在信中写的内容是不是能揭示她的心理状态,她是不是已经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
迪克考虑着。
“也是,也不是——你想要的话,我就拿出这些信让你看。她似乎充满了希望,并且一般来说,渴望生活——甚至有些浪漫。有时候,她谈起‘往日’的口吻,就像出狱囚犯的口吻一样。但是你却分辨不出她指的是罪行,还是监禁,还是所有这些经历。毕竟,我在她的生活中不过是个稻草人而已。”
“当然啦,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我再次向你表示我们的感激。所以我才希望在你见到她之前,先与你会会面。”
迪克笑了。
“你以为她与我的个人关系会来个飞跃?”
“不,不是为那个。但是我想要求你非常温和地处理这事。你对女人十分有吸引力,迪克。”
“那么,上帝帮助我吧!好的,我要态度温柔,并且避免吸引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打算见她,我就嚼上一头大蒜,还要留上一口短髭。我要把她吓得掩起面孔来。”
“不许吃大蒜!”弗朗茨把他的话当真了。“你不会以自己的职业作赌注的,不过,你是在拿它开玩笑。”
“……而且我还可以一瘸一拐地走。再说啦,我住的地方的确没有真正的洗澡盆。”
“你这完全是开玩笑,”弗朗茨松弛下来,至少是装出松弛的姿势。“现在对我讲讲你自己和你的计划吧。”
“弗朗茨,我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做个称职的心理学家——也许要做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弗朗茨笑得很开心,不过,他发现迪克这一次并不是在开玩笑。
“这太好了——而且非常富有美国风格,”他说道,“对我们来说,要这么做更困难些。”他站起身,走向落地窗。“我站在这儿看到的是苏黎世——那儿是大教堂的尖塔。在教堂的墓地中,埋葬着我祖父的遗骸。与教堂隔河相望的地方,埋葬着我的祖先拉瓦特,他没有埋在教堂墓地里。附近是另一位祖先的塑像——海因里希?佩斯塔罗茨,还有一个是阿尔弗雷德?埃斯彻大夫。最重要的是最常见到的兹温格利——这些天神般的英雄对我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我懂了,”迪克站起身来,“我刚才那不过是说大话。一切其实仅仅是个开端。在法国的大多数美国人想回国都想疯了,可我不想。我只要到大学去听课,就能整年从军队里领取津贴。一个伟大的政府为了培养未来的伟人,这样做不是很好吗?然后,我要回家去过上一个月,看看我的父亲。再以后,我就回到这里来——有人给了我一个工作。”
“在哪儿?”
“你的对手——在因特拉肯(瑞士中部阿勒河畔最古老的城市,现为旅游胜地,夏季游客甚多。——译注。)的吉斯勒诊所。”
“别沾它的边,”弗朗茨告诫他说,“一年之中已经有十几个年轻人到他们那儿去试过了。吉斯勒本人就是个狂郁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经营那个诊所——当然,你明白,这是个秘密。”
“你那套美国的老计划怎么样了?”迪克用轻描淡写的口气问道,“我们到纽约去,面向亿万富翁建立一个时髦的机构。”
“你这是稚童的想法。”
迪克应邀到院子边缘的一个小屋里与弗朗茨和他的新婚夫人一起用餐,跟他们一起进餐的,还有一只小狗,狗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就像烧焦的橡皮。他感到一种朦胧的压抑,并不是由于这里稍有些寒伧的气息,也不是由于弗劳?格雷戈罗休斯的举止出人意料,而是由于弗朗茨突然从似乎颇有见地的领域畏缩了。在他看来,禁欲主义有着不同的界定方法——他可以将它看作走向终结的途径,甚至可以当做获得荣耀的过程,但是想到故意将生活范围缩减到几套世代相传的衣裳,未免太苛刻了。弗朗茨和他妻子的举止在这个狭小的空间显得缺乏优雅,也缺乏豪放。迪克战后在法国居住的几个月时光,以及在美国的荣耀福荫庇佑下,进行的奢侈清算,都对迪克产生了影响。另外,人们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之所以来到这块巨大的瑞士手表的核心,也许是出于他的直觉,也就是说那种影响对一个严肃的人来说并不是好事。
他的恭维让凯瑟?格雷戈罗休斯感到自己具有魅力,但与此同时,他却对弥漫在屋子里的菜花气味感到越来越难受,他也讨厌自己,因为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不快的感觉。
“上帝啊,难道我跟这些人完全一个样吗?”他在不眠之夜中就是这样胡思乱想的,“难道我跟其他人完全一样吗?”
这样的素质对于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相当糟糕,不过对于那些专门做世界上最罕有工作的人来说,却是十分优良的品质。说实话,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分析年轻时的一个分野时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决定了自己是否愿意为不再相信的主义而献身。在苏黎世寂静的不眠之夜中,他的目光划过明亮的街灯,盯着一个陌生人家的厨房,他那时常常想,自己要做个善良的好人,要做个勇敢聪明的人,可是这一切要想实现却很困难。假如环境允许的话,他还希望得到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