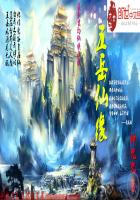当日金枪手徐宁正在家中纳闷,早饭时分,只听得有人扣门。当直的出去问了名姓,人去报道:“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特来拜望哥哥。”徐宁听罢,教请汤隆进客位里相见。汤隆见了徐宁,纳头拜下,说道:“哥哥一向安乐!”徐宁答道:“闻知舅舅归天去了,一者官身羁绊,二乃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吊问。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处?
今次自何而来?”汤隆道:“言之不尽。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时乖运蹇,一向流落江湖。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徐宁道:“兄弟少坐。”
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重二十两,送与徐宁,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叫寄与哥哥做遗念。为因无心腹之人,不曾捎来,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徐宁道:“感承舅舅如此挂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之心,怎地报答?”汤隆道:“哥哥休恁地说。先父在日之时,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恨山遥水远,不能够相见一面,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徐宁谢了汤隆,交收过了,且安排酒来管待。
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见徐宁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汤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徐宁叹口气道:“兄弟不知,一言难尽。夜来家间被盗!”汤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
徐宁道:“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又唤做赛唐猊。昨夜失了这件东西,以此心下不乐。”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徐宁道:“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拴缚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汤隆问道:“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徐宁道:“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假意失惊道:“红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徐宁道:“兄弟,你那里见来?”汤隆道:“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我见了,心中也自暗忖道:‘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作何用?’那汉子应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乱放些衣服。’必是这个人了!我见那厮却是闪肭了腿的,一步步捱着了走。何不我们追赶他去?”
徐宁道:“若是赶得着时,却不是天赐其便!”汤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搁,便赶去罢。”
徐宁听了,急急换上麻鞋,带了腰刀,提条朴刀,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拽开脚步迤逦赶来。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汤隆道:“我们且吃碗酒了赶,就这里问一声。”汤隆入得门坐下,便问道:“主人家,借问一问: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攧走。”汤隆道:“哥哥你听,却如何?”徐宁听了,做声不得。有诗为证:
汤隆诡计赚徐宁,便把黄金表至情。
诱引同归忠义寨,共施威武破雄兵。
且说两个人连忙还了酒钱,出门便走。前面又见一个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汤隆立住了脚,说道:“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宁道:“我却是官身,倘或点名不到,官司必然见责,如之奈何?”汤隆道:“这个不用兄长忧心,嫂嫂必自推个事故。”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小日中:将近中午,方才去了。口里只问山东路程。”汤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明日起个四更,定是赶着。拿住那厮,便有下落。”当夜两个歇了。
次日起个四更,离了客店,两个又迤喂赶来。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处处皆说得一般。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
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见前面一所古庙,庙前树下,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汤隆看见叫道:“好了!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宁见了,抢向前来,一把揪住时迁,喝道:“你这厮好大胆,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时迁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宁喝道:“畜生无礼,倒问我要怎的!”时迁道:“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里面却是空的。徐宁道:“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时迁道:“你听我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不肯货卖,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许俺们一万贯。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闪肭了腿,因此走不动,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时,我到官司,只是拼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别人来;若还肯饶我官司时,我和你去讨这副甲来还你。不知尊意如何?”徐宁踌躇了半晌,决断不下。汤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飞了去!只和他去讨甲;若无甲时,须有本处官司告理。”徐宁道:“兄弟也说的是。”三个厮赶着,又投客店里来歇了。徐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
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只做闪肭了腿。徐宁见他又走不动,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个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再行。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不知毕竟有甲也无。有诗为证:
宝铠悬梁夜已偷,谩将空匣作缘由。
徐宁不解牢笼计,相趁相随到水头。
三人正走之间,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背后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汤隆问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郑州做了买卖,要回泰安州去。”汤隆道:“最好。我三个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说三个搭车,再多些也不计较。”汤隆大喜,叫与徐宁相见。徐宁问道:“此人是谁?”汤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得这个兄弟,姓李名荣,是个有义气的人。”徐宁道:“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都上车子坐地。只叫车客驾车子行。”
四个人坐在车子上,徐宁问时迁道:“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
时迁吃逼不过,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乱说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宁却问李荣道:“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李荣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专好结识官宦来往,门下养着多少闲人。”徐宁听罢,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碍事。”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唱几个曲儿,不觉的又过了一日。
话休絮繁。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买些肉来,就车子上吃三杯。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徐宁一饮而尽。李荣再叫倾酒,车客假做手脱,把这一葫芦酒都倾翻在地下。李荣喝骂车客:“再去沽些!”只见徐宁口角流涎,扑地倒在车子上了。李荣是谁?却是铁叫子乐和。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赶着车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都到金沙滩上岸。宋江已有人报知,和众头领下山接着。
徐宁此时麻药已醒,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开眼见了众人,吃了一惊,便问汤隆道:“兄弟,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汤隆道:“哥哥,听我说。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伙。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阵,无计可破。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只除是哥哥会使。因此定这条计,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却叫小弟赚哥哥上路,后使乐和假做李荣,过山时下了蒙汗药,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徐宁道:“却是兄弟送了我也!”
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小弟亦到此间多说兄长清德,休要推却。”徐宁道:“汤隆兄弟,你却赚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这个不妨,观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有诗为证:
钩镰枪法古今稀,惯破连环铁马蹄。
不是徐宁施妙手,梁山怎得解重围?
晁盖、吴用、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安排筵席作庆。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学使钩镰枪法,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
话休絮繁。旬日之间,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王巳老小,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更过数日,戴宗、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徐宁见了妻子到来,吃了一惊,问:“是如何便到得这里?”妻子答道:“自你转背,官司点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银首饰,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来叫唤。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说道:‘甲便夺得来了,哥哥只是于路染病,将次死在客店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把我赚上车子。我又不知路径,迤喂来到这里。”徐宁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汤隆笑道:“好教哥哥欢喜:打发嫂嫂上车之后,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诱了这两个丫鬟,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做一担儿挑在这里。”徐宁道:“恁地时,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汤隆道:“我又叫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此,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
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宋江、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徐宁道:“小弟今当尽情剖露,训练众军头目,拣选身材长壮之士。”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说那个钩镰枪法。
不争山寨之人学了这件武艺,有分教:三千甲马,斗时脑裂蹄崩;一个英雄,见后魂飞魄丧。正是:撺掇天罡来聚会,招摇地煞共相逢。
毕竟金枪徐宁怎地敷演钩镰枪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