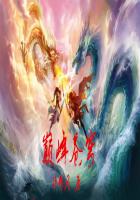那袭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后间,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说:“好端端的,这是怎么说?有什么委屈,起来说。”袭人道:“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这会子因为没有法儿了。”王夫人道:“你慢慢说。”袭人道:“宝玉的亲事,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宝姑娘了,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宝玉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两个因从小儿在一处,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袭人道:“不是好些。”便将宝玉素与黛玉这些光景一一的说了。还说:“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独是夏天的话我从没敢和别人说。”王夫人拉着袭人道:“我看外面儿已瞧出几分来了,你今儿一说,更加是了。但是刚才老爷说的话想必都听见了,你看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袭人道:“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说话,他就笑;没人和他说话,他就睡。所以头里的话却倒都没听见。”王夫人道:“倒是这件事叫人怎么样呢?”袭人道:“奴才说是说了,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王夫人便道:“既这么着,你去干你的。这时候满屋子的人,暂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儿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说着,仍到贾母跟前。
贾母正在那里和凤姐儿商议,见王夫人进来,便问道:“袭人丫头说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问,便将宝玉的心事细细回明贾母。贾母听了,半日没言语。王夫人和凤姐也都不再说了。只见贾母叹道:“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有什么,若宝玉真是这样,这可叫人作了难了!”只见凤姐想了一想,因说道:“难倒不难,只是我想了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说给老太太听,大家娘儿们商量着办罢了。”凤姐道:“依我想,这件事只有一个掉包儿的法子。”贾母道:“怎么掉包儿?”凤姐道:“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来,说是老爷做主,将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要是他全不管,这个包儿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欢,你怎么样办法呢?”
凤姐走到王夫人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王夫人点了几点头儿,笑了一笑,说道:“也罢了。”贾母便问道:“你娘儿两个捣鬼,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呀?”凤姐恐贾母不懂,露泄机关,便也向耳边轻轻的告诉了一遍。贾母果真一时不懂,凤姐笑着又说了几句。贾母笑道:“这么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宝丫头了。倘或吵嚷出来,林丫头又怎么样呢?”凤姐道:“这个话原只说给宝玉听,外头一概不许提起,有谁知道呢?”
正说间,丫头传进话来,说:“琏二爷回来了。”王夫人恐贾母问及,使个眼色与凤姐。凤姐便出来,迎着贾琏努了个嘴儿,同到王夫人屋里等着去了。一回儿,王夫人进来,已见凤姐哭的两眼通红。贾琏请了安,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的丧事的话说了一遍,便说:“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谥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员照料。昨日起身,连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有多少话不能说。’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若是路上遇见了,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王夫人听毕,其悲痛自不必言。凤姐劝慰了一番,“请太太略歇一歇,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罢。”说毕,同了贾琏回到自己房中,告诉了贾琏,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题。
一日,黛玉早饭后带着紫鹃到贾母这边来,一则请安,二则也为自己散散闷。出了潇湘馆,走了几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绢子来。因叫紫鹃回去取来,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忽听一个人呜呜咽咽在那里哭。黛玉煞住脚听时,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什么话。心里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黛玉未见他时,还只疑府里这些大丫头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所以来这里发泄发泄;及至见了这个丫头,却又好笑,因想到:“这种蠢货有什么情种?自然是那屋里作粗活的丫头受了大女孩子的气了。”细瞧了一瞧,却不认得。那丫头见黛玉来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来拭眼泪。黛玉问道:“你好好的,为什么在这里伤心?”那丫头听了这话,又流泪道:“林姑娘,你评评这个理。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我就说错了一句话,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听了,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因笑问道:“你姐姐是那一个?”那丫头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听了,才知道是贾母屋里的,因又问:“你叫什么?”那丫头道:“我叫傻大姐儿。”黛玉笑了一笑,又问:“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说错了什么话了?”那丫头道:“为什么呢,就是为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黛玉听了这句话,如同一个疾雷,心头乱跳。略定了定神,便叫了这丫头:“你跟了我这里来。”那丫头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儿上葬桃花的去处,那里背静。黛玉因问道:“宝二爷娶宝姑娘,他为什么打你呢?”傻大姐道:“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说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宝姑娘娶过来罢。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第二宗——”说到这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才说道:“赶着办了,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家呢。”黛玉已经听呆了。这丫头只管说道:“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宝姑娘听见害臊。我白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咱们明儿更热闹了,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呢?’林姑娘,你说我这话害着珍珠姐姐什么了吗?他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混说,不遵上头的话,要撵出我去。我知道上头为什么不叫言语呢?你们又没告诉我,就打我。”说着,又哭起来。
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停了一会儿,颤巍巍的说道:“你别混说了,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你去罢。”说着,自己移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原来脚下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的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离的远,也看不出是那一个来。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
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心里微觉明晰,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便站住了问道:“你作什么来的?”紫鹃陪笑道:“我找了绢子来了。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我赶着过去问姑娘,姑娘没理会。”黛玉笑道:“我打量你来瞧宝二爷来了呢,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紫鹃见他心里迷惑,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了,惟有点头微笑而已;只是心里怕他见了宝玉,那一个已经是疯疯傻傻,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时如何是好?心里虽如此想,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搀他进去。
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丫头们也有脱滑顽去的,也有打盹儿的,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黛玉,便让道:“姑娘屋里坐罢。”黛玉笑着道:“宝二爷在家么?”袭人不知底里,刚要答言,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他努嘴儿,指着黛玉,又摇摇手儿。袭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语。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袭人看见这番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是没法儿。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
“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袭人见了这样,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不减于宝玉,因悄和紫鹃说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纹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罢。”因回头向秋纹道:“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去罢,你可别混说话。”秋纹笑着,也不言语,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
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瞅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
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紫鹃、秋纹后面赶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贾母院门,只管一直走去。紫鹃连忙搀住,叫道:“姑娘往这么来。”黛玉仍是笑着随了往潇湘馆来。离门口不远,紫鹃道:“阿弥陀佛,可到了家了!”只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