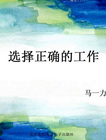西方文明的思想宗师(希腊公元前428~公元前360年)
成长环境
公元前428年柏拉图生在雅典一个显赫而富有的家庭。父亲阿里斯同的先祖是雅典古老的王室,母亲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梭伦,这种光荣通过显赫的政绩与有效的联姻得以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短暂而混乱的三十僭主时期威震一时的克力锡亚斯和查米迪斯就是柏拉图的舅父。柏拉图幼年丧父,母亲再嫁皮里兰佩斯——权倾一时的执政官,伯里克利的知己和政治同僚。由于有好学的兄长阿得曼托斯与格拉康的关爱,柏拉图的成长并未受很大影响,而生父在他的心目中幻为一尊至善的偶像。姐姐波顿妮生有一子斯彪西波,后来是柏拉图名副其实的衣钵传人,在他死后主持阿卡德米学园的工作。另一个兄弟安蒂丰在这个修养甚好的家庭里显得特殊些,放弃了哲学而去玩马。
一个平庸的时代往往以伟大为疯狂,指个性为叛逆,而称赞盲从是明智,逃避是洒脱,怯懦是务实,卑鄙是机敏,这样的时代外强中干,浮华热闹,但产生不了骄人的功绩,只有阴沟里暗自流淌的罪恶。智慧在地下运行,时代的精神寂寞地游荡在唯一自由的风中。人类历史总是一个又一个平庸时代接踵而至,而柏拉图有幸生在屈指可数的伟大时代之一,那是一个人可以因其智慧获得幸福的时代,并因他的存在,使这伟大成为不朽。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创造了空前的统一,也领略了混战的苦涩。分别有两次重大的战争标志着希腊政治地图的戏剧性变化,先是公元前490年至前479年的希波战争,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城邦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成功击退了入侵的波斯帝国,挫败了波斯人使希腊成为亚洲帝国殖民地的企图。
这次战争使零落的希腊统一,更为雅典赢得了财富与光荣,它一跃成为海上霸主,提洛同盟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支配者,它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帝国,不仅拥有整个爱琴海,而且要控制科林斯湾和维奥蒂亚,雅典的战士们仅一年之中就同时征战塞浦路斯、埃及、腓尼基、伯罗奔尼撒、爱琴海和麦加拉。比雷埃夫斯港是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中心,白帆巨樯,熙来攘往,阿提卡的橄榄,米洛斯的大理石,皮帕瑞图斯的葡萄酒,精美的陶器,炫目的珍宝都在这里成交,输出的是货物,收获的是繁荣与强盛。
冷峻的斯巴达人则退居内陆,继续实践自己俭朴刻板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念。但这些勇猛而缺乏安全感的战士始终警惕着阿提卡半岛上兴高采烈的雅典人。权重生嫉,新仇旧恨一旦发作,所有的人都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遂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纠集了各自的盟国,雅典和斯巴达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场内讧,以冒险为天职的雅典水手难敌不知花花世界为何物的拉哥尼亚武夫。
在外患内乱的情况下,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因染时疫撒手归西。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政坛被巧言令色的投机分子占据,雅典政治地位急剧逆转。胶着数十年后,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在政治上再也没有出现伯里克利时代的霸主气象。
与政治上的辉煌相伴、并且比政治实力的起伏更引人注目的,是雅典对人类文明无与伦比的贡献。在两个世纪中,雅典孕育了梭伦、庇西斯特拉图、底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伯里克利等政治家,他们创立了法律,完善民主制度,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希腊帝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一名卓越的指挥官福尔米翁。这些雅典人还是修养很高的艺术鉴赏家,以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为首的戏剧家创造了精妙绝伦的大众娱乐,神灵被赞颂,人性被揭露,讽刺剧则以一切外表庄严的事物为靶子,以模仿与调侃的方式在笑声中扯下其伪装,让他们赤裸裸地站在哄堂大笑的人民面前。自由与勇气同样注入了雅典卫城的建筑师姆奈西克里和伊克蒂诺以及雕塑家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的作品中,显得和谐而完美。而修普底德,在他记录雅典和希腊的光荣历程时,成为了历史学家中最优秀的一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代表着雅典哲学的巨大转折和发展。
成长于此时此地,柏拉图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是一个伟岸强壮的青年,优秀的军人,出色的运动员,由于他敏感的心灵和语言的天赋,他还是一个诗人与剧作家。除了资质出众以外,他与雅典其它世家子弟并无二致,雄心勃勃地等待着在政坛大展身手的那一天。
直到20岁的柏拉图开始追随苏格拉底,一个全新的世界便在这个少年面前徐徐展开,他乐于看到苏格拉底以排山倒海的雄辩术揭露那些简单常识的武断和臆想,并投身其间,在苏格拉底的指导下,从为论辩而论辩进而至于条分缕析的讨论。所以,后来柏拉图常说:“感谢上帝,我生为希腊人而非野蛮人,生为自由人而非奴隶,生为男子而非女人,尤其是,我生逢苏格拉底时代。”
追随名师
在苏格拉底以前,古希腊自然哲学已有骄人的成就,苏格拉底本人也曾对物理世界进行研究,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宣称从树木和石头那里学不到什么,与其玄而又玄地讨论世界的构成,不如研究人类自己。人生各个方面,如战争、婚姻、友谊、爱情、家政、艺术、伦理、道德,都成为他探寻的课题。因此,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另外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这个矮胖、秃顶、突眼睛、朝天鼻的哲学家在粗陋的外表之下有某种和蔼可亲的东西使他成为雅典城最优秀的青年衷心爱戴的导师,这些青年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有不同的思想信念与政治抱负,但他们都被苏格拉底了无牵挂、自由自在的世界所吸引,无数后人争论不休的一些题目也曾激动过这些热爱论道的思想者。
雅典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块石头都异常熟悉苏格拉底健行不倦的身影。他见多识广,让人很难相信他70年的岁月几乎全部消磨在雅典城的街头巷尾与路人谈天上。他是节制的典范,他所教导的美德最好的实践者。他薄有资产,战时能够负担重甲步兵的装备,但从不工作,不考虑明天的事情,永远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却随时随地会陷入沉思冥想,物我两忘,很少念及对妻儿的责任。妻子桑西普不得不独自抚养三个儿子,不免时时作河东狮吼,故而与苏格拉底流芳百世相比翼,做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悍妇。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清谈是苏格拉底唯一的授课方式,思维与论辩的乐趣是他最乐意的报酬。德尔斐神庙的先知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总是谦逊地宣称自己一无所知,对人所公认的知识持普遍的怀疑态度,而且宣称只有知道自己无知者,才是人类中最聪明的人。和号称教人以所谓“有用”知识的智者们不同,苏格拉底四处请教关于人的知识,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正义,等等。在德谟克利特万物流变的思想和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影响深远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如果不能用全面完整而绝对的方式给某一件事物下定义,你就并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他的谈话总是在和和气气地请教中开场,对一个习以为常的东西,请你下一个明晰的定义和绝对的判断吧。但任何人想当然的定义都会被苏格拉底以事实分析步步进逼,在排山倒海般地追问下这个可怜人的脑袋和舌头都麻木了,而且发现自己走到了最初立场的反面。此时,苏格拉底仍然谦虚地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已。这种近乎自大的自谦令德高望重的希腊人如坐针毡,气得发疯,却受到天生叛逆的青年们打心眼里的赞许。
对传统的有力否定、对民主政治的敌视、对他所属的中下层平民阶层的鄙视、对大多数雅典人智力和知识的多次嘲弄和对自己才智毫不脸红的高度评价,使苏格拉底在公元前423年就成为喜剧插科打诨的对象。天性快乐的雅典人从不放过任何笑料,而苏格拉底本人也乐于看到自己被表现为一个温和而机敏怪诞的老头子,取笑别人也被别人所取笑。但他令人不安的言谈在各个阶层的雅典人中都引起了不满,日积月累,终于成为一种敌意。
尤其是他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反民主的倾向越来越浓,他们将雅典的失败归咎于吵闹不休的民主制度,而把斯巴达粗鄙的武夫和强悍的寡头统治当作疗疾的良药。人们称他们是“拉哥尼亚迷”,“留着长发,半饥饿,不洗澡,学苏格拉底。手中拿着羊皮纸裹的棍棒”,在公元前411年的四百僭主专政和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专政时期肆虐雅典。这些青年与1933年柏林街头狂热的法西斯冲锋队其实非常相似,梦想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暴政,给予公民以尽可能少的权利与自由,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阻止他们的人,在克勤克俭的表象下却往往掩盖独裁者的荒淫无耻。亚西比德是苏格拉底亲密的弟子与友伴,像颗流星一样划过雅典的民主政治,他在政治挫折中投向了雅典的死敌斯巴达,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柏拉图的舅父克力锡亚斯与查密迪斯,是三十僭主专政时期呼风唤雨的人物,在短短八个月的独裁期内,屠杀了1500个希腊人,甚至超过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十年杀人的总和。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谈论和宣讲美德,他的弟子的行径严重损害了老师的声望。他说美德就是知识,最有德性的人就是那个最知道的人。可是聪明而多才多艺的亚西比德是民主政体时期最荒淫、最骄横和最强暴的人,阿提卡散文大师克里锡亚斯文风纯正优雅,许多个世纪以后还是罗马皇帝奥勒留学习希腊文的宗师,同时却是寡头专政时期最贪婪、最阴险的一个恶棍。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属于那少数的最知道的人,却毫无美德可言。
雅典民主政体很快复苏。民主派的政策相对很温和,颁布了大赦令,宽容了许多政治犯。但是,与雅典民主政治相比较,雅典的社会思想是守旧落后的,民主派对雅典人思想中的混乱忧心仲忡。苏格拉底这个七旬老翁仍然喋喋不休地与又一代雅典青年谈笑风生,虽然他是作为公民的忠诚是有名的,但他对民主制度的批评更为显著。在雅典惨败,寡头制肆虐的痛苦经验之下,民主派对他的玩笑已经笑不出来了,他们显然认为,打倒苏格拉底远比改正他所指出的罪恶要容易得多。尽管有大赦令,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元前399年,以渎神罪的名义,雅典民主派开始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对思想家的第一次有名的审判,罪名却并不陌生,不久之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击败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本人的好朋友、出色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被驱逐出雅典时,罪名就是他居然胆敢公开宣称,太阳是一块燃烧着的大石头,因而冒犯神灵,罪不可恕。
但是,这审判远非后世的许多次迫害那样卑鄙无耻,他们给予苏格拉底申诉的权利。是苏格拉底自己选择了死亡。作为曾经存在过的人们中最高贵的一个,他不属于任何逃避或者言行不一。他既不肯让哭哭啼啼的妻儿来到法庭引起审判者的怜悯,也不肯降低自己的尊严去迎合某种口味,他不愿意终生享受雅典法律的保护却在此刻逃避它的惩罚。他自由自在地活过了,也气势如虹地走向死亡。
这时,在28岁的柏拉图心中,有些东西永远地破碎了。
世代官宦的环境本来使柏拉图有早慧的政治敏感性和比大多数人优越得多的起点,而且柏拉图确实一直有从政的念头。可是三十僭主时期的暴政和民主政体处死苏格拉底相继打消了他对雅典政坛曾经有过的幻想。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为他注入了一种我们今天或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意识的观念,其持有者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也使他们永远站在一个客观冷静的理性立场,批判性地分析现实社会,因此苏格拉底会敌视民主体制。对两万多雅典男性公民而言,那是一种彻底的直接民主制度,但与20多万的奴隶、贵族和平民妇女根本无干,所以在运行中它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一个制度中,诡辩者以其富有煽动性和欺骗性的演说就可以左右政治决策,政治家需要口才来增强他的说服力,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传授修辞术的职业教师生意的兴隆。而出于时代的局限,苏格拉底并未想过民主的扩大,斯巴达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他所向往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相当于20世纪纳粹德国所试图建立的那种体制。二战后逃出法西斯炼狱的欧洲人发自内心地说,民主政体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可也绝对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但苏格拉底和其他雅典人生而处于最彻底的直接民主体制之下,他们所看到的是它的缺点带给雅典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合理,智者们纷纭的意见已经置疑了雅典传统信仰,他自然而然地充当了社会的良心,超越地思考着什么样的国家是好的。
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在斯巴达人的庇护下,三十个雅典贵族接手统治这个城市。他们中有柏拉图母亲的堂表兄弟克里底亚斯以及母亲的弟弟查密德斯:“凑巧的是,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我的亲戚,而且很熟。他们马上要求我参加国家的管理,这正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