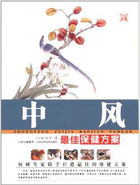我大乐,因为从没见过那么大的乌龟,不顾小丙的强烈反抗又把它捉到大乌龟的旁边进行比较。春晓接着又拿出了很多好东西,有做工精细的弹弓、黑亮粗大的蟋蟀,还有许多奇怪的前朝古币。我完全被聚宝盆一样的春晓吸引了,每天上午的四个时辰都在和她玩闹,斗蟋蟀或者玩我在池塘边捉来的青蛙,看着它们在水盆中蛙泳。其他的人都成为了我们的攻击目标,春晓的弹弓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弹无虚发的感觉,莫一凡的后脑勺上一度全是被我打出来的包。先生们都对春晓十分宽容,任凭后面蛐蛐、蟋蟀叫成一片也毫不理睬。我狐假虎威也得以免除了先生们的责罚,只有上算数课才稍稍收敛一些。
很快我就知道了先生们之所以对春晓那么宽容,不仅在于她的出身,更因为她天资聪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让先生们在她面前觉得压力很大。一次先生命我们当堂作诗,结果春晓交上去的七言古诗句句用典,先生一时词穷,竟无法点评,晚上回去翻倒箱箧查了大半夜才勉强理出思路。渐渐其他人也无法对春晓视而不见了,连莫一凡都试图与春晓说话,一时间,春晓成了南长学堂最引人瞩目的学生。
但我始终是春晓最亲密的玩伴,我甚至知道她每月何时会闷闷不乐、烦躁不安几天。我觉得自己大概明白春晓为什么要到学堂来了,或许她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同龄玩伴。而春晓对我的最大意义在于,从此再也不会有什么鸡兔同笼问题把我难住了,只需叫她看一眼,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春晓善于模仿笔迹,于是先生留下的文章也通常是由她代我完成。这样的时光过得飞快,日子就像被穿堂风吹得哗哗作响的书页一样翻得飞快,一晃眼间,两年时光流转不见。
直到有一天,春晓跟我说她要去上汴京大学堂。当时我正在出神地看着窗外的橡树,两年间它长高不少,现在已经无法从室内看到它比较高的枝头了。
我们的桌子上早已不见什么乌龟和弹弓,那些玩意几乎在春晓转来后便迅速迎来了在少年们身边的绝唱,从此便被弃之一边。春晓开始没完没了地作词,这些作品被高价买走,然后在街头巷尾被人们传唱不休。有人说是昔日有名的词人柳三变把它们买走的,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商人,专门收购别人四溢的才华。
“你打算上哪个大学堂?”春晓忽然撂下笔,问我。
我有些惊讶,发现自己并没想过这个问题,便摇摇头说:“不知道。”
春晓“哦”了一声后又拿起了笔,静默片刻,待我的注意力又转向橡树上正在相亲相爱的两只麻雀后,她小声低语:“我打算上汴京大学堂。”
在那个瞬间,我想起了与自己从未谋面的爷爷和把汴京大学堂贬得一文不值的令狐太乙。
那天下午,我在校场上训练时一直恍恍惚惚,被林教头骂得狗血淋头。训练结束适逢学堂放学,我向学堂大门口瞟去,无意间看到春晓正和贾贻贝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这让我想到似乎贾贻贝这段时间来一直喜欢找春晓说话,有一次还给她送了一支林墨轩的狼毫。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怒火中烧,哪怕是儿时杜唐在我的耳朵上咬了一口时,我也没有这般愤怒过。我必须要做些什么。
因此,在第二天中午,当我把贾贻贝的脑袋按进马桶,看着浑浊的气泡冒个不停时,我心里也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
“从此以后不许你再和春晓说话。听见了吗?”我告诉贾贻贝。
半天他都没有回答。我心想这小子有点脾气,正打算再给他几脚,忽然想起他还被自己按在马桶里呢,赶紧拎着头发将他拉起来。
随着淅沥沥的水声,贾贻贝破口大骂:“你这厮好大胆子!等本少爷查出你是谁……”
于是我一把又将他按回了马桶,钟馗面具下的脸露出了微笑:“你查不查随你便,但是你如果再和春晓说话,我就让你再也说不了话。”
这样的拙劣的威胁与对骂持续了半个小时,最终贾贻贝还是认输了,也许这跟我扬言要把他脱光裤子扔出去有关吧。
在我看着贾贻贝吐出的浑浊气泡的那刻,我明白自己可能要失去春晓了,因为我是不可能考上汴京大学堂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混蛋,本来我是不想上什么大学堂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我却发疯般想进入这个水木大学堂的死对头,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我尝试着让春晓教我功课,把之前耽误的那些东西统统弥补回来。在家我则硬着头皮向父亲请教两年前教的更相减损法,父亲很激动,一边扇着我的耳光一边给我讲。然而这样的恶补效果却不佳,都说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可惜我是在羊差不多死绝了才开始补,变成了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春晓有时会变得很伤感,写一些离愁别绪的诗词交给先生。这使得学堂的气氛也变得伤感起来,因为先生往往回家查了很长时间书后终于看懂了这些诗词,便放声大哭,丝毫不顾文人的矜持,第二天来上课时,也依然红着眼圈,讲几句话便会哽咽住。南长学堂弥漫起一片凄风苦雨。
虽然大家都很哀愁,但是我明白,这些缱绻的诗句其实只与我有关,我也因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更加悲伤。
在距离大考还有半年时,汴梁城下起了大雪。我在夹袄外披上了蓑衣,抱着从父亲的木箱里偷出来的藤球,迎着风雪向北走去。在我家的北面是陈桥,陈桥的北面是惠明寺,惠明寺的北面是淇水,过了淇水就可以看见一座石塔,那里就是汴京大学堂了。
我在石塔旁的校场见到了汴京大学堂蹴鞠队的洪教头,那里的校场远比我们南长学堂的要大,说实话以前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校场。
“我会踢球,我想上汴大。”我愣头愣脑地说。
洪教头大笑:“很多人会踢球,也有很多人想上汴大。你如果想上,就必须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相信你比那些人都强。”
我把藤球拿了出来,抖掉蓑衣,一言不发地开始颠球。刚开始是用右脚,然后是左脚,接着左右开弓,随后头、膝、胸、肩、颈全都招呼上了。在鹅毛大雪中,我一边颠球一边想不知道明年是不是可以和春晓一起站在那石塔上看着雪片纷纷落下,看着汴梁城在风雪中逐渐变得隐隐约约。
这样的美好想象也许持续了几个时辰,反正我不间断地颠了多长时间球就想象了多长时间。等我回过神来,洪教头已经在校场上席地而坐,周身落满雪花,鼻涕垂在笔尖,冻成了钟乳石的样子。
“洪教头?”我喊道。
他微阖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了,摇动身子抖掉雪花,用手敲掉挂在鼻子下的钟乳石,挣扎着站了起来。
“欢迎来到汴京大学堂。”他握住了我的手。
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汴京大学堂,我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去他的水木大学堂。”
洪教头的手握得更紧了。
恰巧汴京大学堂校刊《汴大纪要》的主笔就在附近,他把我和洪教头请到了旁边的亭子里,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在听洪教头谈完关于贯彻朝廷开展蹴鞠运动精神、培育汴大文武全才特色的宏篇大论后,主笔把目光转向了我。
“作为今年第一个进入汴大的学生,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声情并茂地说。
“你是要真情实感吗?”我问。
他拿着毛笔正要记录,听了我的反问有点惊讶,说:“当然,真情实感。”
“春晓。”我一字一顿地说。
据说第二天的《汴大纪要》头条是这样的:汴大贯彻朝廷精神,不拘一格录取人才;蹴鞠高手文武双全,录取之时高吟孟诗。
《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