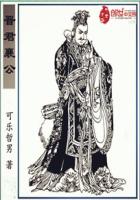温州知府范思敬收到刘录勋参劾和琳的公文,以及要求联名的信,看后就随手扔到了故纸堆中,根本就没把石太生用生命换下的最后一策当回事。范思敬认为,此案已经基本结束了,窦光鼐三战皆败,必定会被调回京中。范思敬还存了一点私心,他已经看出和珅已呈蒸蒸日上之势,未来必权势之熏灼不可限量,早晚要盖过阿桂,成为把握朝纲第一人。因此有心投靠和珅,巴结和琳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敢得罪他?只是孟卫礼一案来得蹊跷,让他有些心慌。
和琳带走孟卫礼,据说是这小子私吞陈辉祖案中漏出来的宝贝。虽说没自己什么事,但孟卫礼如果急了乱咬人,头一个可能就是黄梅,第二个就是他。范思敬思来想去,总是放心不下,于是派了自己的亲信家人陈喜带了银子去杭州打听。
陈喜去了杭州,打听到孟卫礼被押在杭州臬司大狱里,拿着范思敬的书信找到熟人,依例上下打点一番才进得狱中。臬司衙门的大狱条件要稍好于别处,特别是孟卫礼住的这边更受到额外照顾。中间一溜宽走道,两边虽仍是铁栅小窗,孟卫礼的牢房相对宽敞些,还架了一张床。饶是这样,那孟卫礼整天卧在床上一阵阵地呻吟,一声声叹息,像得了大病似的。
牢头开了牢门,将陈喜放进去,又咔啦一声下了锁,惊得陈喜心一跳,像是自己也被关进去似的。孟卫礼听得有人来,抬了头,认得陈喜,急忙从床上下来道:“老陈啊,你可来了。是不是范大人要想办法救我?”
“嘘—可不敢在此说这种话。”陈喜轻声道,“我家老爷让我给你捎几件换洗的衣服,再问一问你,这案子审得如何了,你都说了些什么?”
“刚来杭州时,在臬司衙门大堂上审过一次。还是问独玉玉山子和唐寅《麻姑图》的事,我据实而答后,阿桂等人并未说什么便退堂了。后来便将我放到这牢里,再没音了。这些天吃喝倒是不错,只是我这心里着实放不下来。那黄梅真是没良心,他也在杭州,十多天了却没派一个人来看我。我本指望他来救我呢,看来是没戏了。”
“范大人叫你不要乱说话。你不过是私藏官物的罪,而且事先并不知情,属无心而犯。这是轻罪,至多是个回籍禁锢,说不定仅仅罢官为民就完了。若是胡说些别的东西,当心你项上人头也保不住。”
“这个我明白。陈二爷,劳烦您转告范大人,我对范大人忠心耿耿,望范大人多多替孟某人担待。最好,弄个削官为民,我还能回老家去侍奉老母。”说着说着便掉下泪来。
陈喜见孟卫礼答应不乱攀咬,心下大定,塞给孟卫礼一个包袱,安慰道:“这里是一百两银子,你家老仆王升不日也将到杭州。孟大人不要愁了,此案定无大事的,在狱中将身子养得好好的,出了狱也好赶路回家。”
孟卫礼看着陈喜走远了,心神倒安定了一些,觉得有知府替自己说话周旋,这案子也不会判得重了。若是削职为民,早离了这是非之地,也不算是一件坏事。转念想到那日飞来的横祸,又暗暗为自己叫屈,再想起十多天前,大堂上审案、问话的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当朝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领班大臣阿桂。阿桂根本不相信他说的什么一个叫庞茂琨的老头,为报十多年前的救命之恩,特意送的两个宝物这些话。阿桂问道:“庞茂琨家住何处,平时与什么人交往,又做何生理?”孟卫礼那天光顾了高兴,竟一句也没问,耷着脑袋回答不出来,只是说冤枉。巡抚伊龄阿与按察使福岜也说,当年陈辉祖之案发案之前,浙江古玩珍宝交易极盛,大多都是王亶望家中流出来的东西,孟卫礼能得到这两样东西亦不奇怪,此案并非大案,当堂即可审结。当时孟卫礼急得差点晕了过去,幸好窦光鼐说了一句公道话,但凡审案,必有人证物证口供,如今只有两样东西,旁证皆无,怎能随便定案,还须细细查访,才能断得公正。阿桂说道:“就依学政,命福岜加以详查后再作定论。”
孟卫礼正在胡思乱想,听远处监门一响,又有一个人走进来。
这一回进来的是个五品官,五十多岁年纪,头戴白水晶顶子,穿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八蟒五爪袍,套着白鹇补服,走路佝偻着腰,晃着手臂。孟卫礼不认识这人,见他径直向自己走过来,便隔着栅栏问道:“请问,您是哪处府上的长官?”
“我是浙江学政副使李大鼎,是窦大人派我来的。”说罢,回头对跟在身后的牢头道,“打开门,出去守着,任何闲杂人等不许进来。”牢头答应一声,将牢门打开,出去了。
李大鼎呵呵笑道:“这回窦大人是派我来救你的。”
孟卫礼又惊又喜道:“现在就能放我出狱吗?多谢李大人,多谢窦大人。”
李大鼎拍拍孟卫礼的肩道:“我又不是来劫狱的,哪能有这么快?窦大人叫我传话于你,他会力保你。你这件案子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大了说是私藏御用之物,说不定要杖流三千里;小了说,不过是一时糊涂贪便宜,买了涉案之官物,弄好了官降三品,还能留用。”
孟卫礼想了想道:“李大人,我不过是个八品同知,再降三品,我还得倒欠两品呢。那是个什么官?”
李大鼎咳嗽两声道:“不是官降三品,是官降三阶。你是八品,降一阶是从八品,降三阶是从九品。带从九品按原任出差,只要干得好,用不了两年,又是官复原职。”
孟卫礼听得眉头舒展开来,连忙道:“那就请窦大人多费心了。下官若有起复之日,一定忘不了窦大人和李大人的恩情,随时愿效犬马之劳。”
“好,你这句话说得恳切,我必会向窦大人转告。不过,眼下窦大人就用得着你,你可愿意帮忙?”
“窦大人的事皆是在下分内之事,岂能说是帮忙。李大人请讲,只要我孟某能办得到的,必全力去办。”
“孟大人是个爽快人,很合我的性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窦大人卖你这么大的人情,这个忙你若不帮还真不行!我问你两件事,头一件,海成在平阳县所问过的人证名单你可记得?第二件,你跟了黄梅这么多年,他所做的不法之事,你可敢具结上告,并做人证?”
孟卫礼道:“李大人,咱明人不说暗话。人证名单海成那里就有,窦大人若要取,他不敢不给,何必问我要?还有,我要是卖了黄梅,岂不是连自己也卖了,恐怕旧罪未去,又添新罪,到时更难出这大狱了。”
“海成在平阳县的时候,就将名单毁去了,他若有,我还用问你要吗?你若再啰唆耍赖,我可是救不了你啦,你就在这大狱里待着吧。你还指望黄梅救你吗?黄梅还怕沾腥呢,早就回了平阳了。到时候,判下来杖流充军,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这……”孟卫礼怕窦光鼐急了在这案子上给他下手脚,眼珠转了几转道,“李大人,你可得保证,我做了这两件事,可都是为了窦大人,今后可别扯到我身上。”
“你放心,窦大人与我相交数十年,他老人家的脾气我知道,是说到做到的实在人,只要你将名单写出,将黄梅之事具结写明白,窦大人保你平安无事地走出这臬司大狱。”说话间,已将笔墨递到孟卫礼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