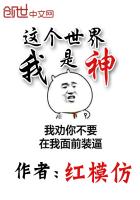一
伊尼斯-玛格拉斯的瘦女人拥有无限愤怒的能力。她可不是那种能力有限的人,发怒就像刮风,狂风过后,立刻风平浪静,重现笑容。她可以把愤怒储存在那些永恒之洞穴中,那些洞穴通往每一个灵魂,里面塞满了愤怒与暴躁,直到她往里面注入智慧与爱意,只因在生命之初,万事万物以爱开端,以爱结束。起初,爱就像一个笑盈盈的孩子那样,精心地滋润着心灵的岩石与沙漠,打开通向心灵深处的大门,孩子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爱悄无声息地溜走,成为过眼云烟。这时恨如疾风般尾随而至,就像断瓦残垣中的巨人和侏儒那样,开采岩石,铲平通往心灵深处的路;不过,待这工程完工之后,爱又会飘然归来,永久地扎根于心灵,这就是永恒。
瘦女人必须当着太阳与风的面,拥抱戈特的拉布列康矮精灵,以此来执行“敌人的宽恕”,通过自我牺牲来接受心灵的洗涤,才能减轻丈夫的罪孽,为其赎罪。
只有在宽恕了那些承受“原罪”煎熬的人们后,她才能自由地与“惩罚”作对。完事之后,她准备烤三个蛋糕,前去拜访安格斯·奥格。
她在烤蛋糕的时候,休玛斯和布丽吉德·贝格这两个孩子溜进树林聊天,为这桩奇事惊叹不已。
起先,因为不确定警察是真的离开了,还是蛰伏在黑暗中等着突袭并抓他们去坐牢,于是孩子们轻声细语,不敢闹出太大动静。“谋杀”这一字眼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他们更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杀人。这是个可怕的词,因为无法想象他们的父亲牵连其中,这个词显得更可怕了。他干了什么?他的一举一动和生活习惯在孩子们眼里是再寻常不过了,也许他是卷入了一个阴谋,这个令人恐惧又难以理解的想法在孩子们的脑中一现。他们知道这件事和壁炉下面埋着的另一个爸爸和妈妈的尸体脱不了干系,但他们知道哲人是清白的,因此他们认为这实在是一件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悬案。
树林里面没有人追着他们,过了一小会,他们就大胆地迈开了步子。走到松林的尽头。犹豫了一阵子,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下又忍不住走得更远了些。美丽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驱散了他们心头的阴霾,没多久他们就追逐打闹了起来。他们就这样随心所欲地嬉戏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米豪·麦克穆拉楚的农庄,他们气喘吁吁地坐在一棵小树下休息。附近有一片灌木丛,他们趁着休息的功夫再度思考起他们父亲的官司。孩子的思考总是离不开动作。他们想问题往往是手脑并用——只有边说边演示,他们的思路才会清晰形象。休玛斯·贝格很快就把那天警察来访的情景以哑剧的形式重演了一遍。灌木丛下的空地成了他们家农舍的炉石;他和布丽吉德成了那四个警察,休玛斯立刻拾起一块大石头,横眉怒目地做出挖尸体的样子。才挖了几分钟,他就觉得手中的石块磕到了什么硬物。当他们掘出了一只装满黄色星屑的小陶壶后,他们欢呼雀跃,飞快地把坑填平。他们久久地把玩着陶壶,黄色的星屑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流过指缝。待到玩累了,他们决定把这个壶带回家,可一到了戈特-纳-克洛卡-莫拉,他们就累得拿不动也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个壶留给他们的矮精灵朋友们。休玛斯·贝格在树干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他们的朋友就过来开门了。
“我们带来了这个,先生。”休玛斯说。可他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矮精灵一看见这只陶壶就张开双臂将它抱在怀里,用力擦拭着壶身,动静之大引得他的同伴们都蜂拥而至,想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又笑又哭,两个孩子也和他们一起激动,于是欢声笑语充斥着整个戈特。
可是矮精灵们的激情并没有持续很久。欢笑过后,取而代之的是懊恼和悔恨;愁云惨淡的哭泣声回荡在耳边,萦绕在心头。正是他们使孩子的父亲遭到了法律的制裁,他们又有何面目去感谢孩子们呢?那样的法律不给人弥补赎罪的机会,只有严苛的惩罚;那样的法律取自于敌意之书,而非友谊之书;那样的法律视仇恨为天性,视爱为骗局;法律铁面无私,仁慈日薄西山;盲目是昏聩自大的魔鬼;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冷酷的石头心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望而却步;人生枯萎衰败,死亡颤抖着步入坟墓。悔恨啊!他们擦拭着眼中浑浊的分泌物,以跳舞来发泄怨恨。他们爱莫能助,唯有亲切地喂饱了孩子们,然后送他们回家。
瘦女人烤好了三个蛋糕。她分给孩子们一人一块,另一块留给她自己,就这样踏上了寻访安格斯·奥格的旅程。
他们于下午时分出发,下午的天气非常好。早晨的清新空气一去不复返,烈日的曝晒使人备受炙烤的煎熬。沿途几乎没有可供乘凉的树荫,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又热又累,饥渴难耐——孩子们是如此,而瘦女人因为身量纤纤,所以除了饥饿以外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过饥饿确实没什么人能受得了。
她一言不发,按捺着心头的怒火,大步流星地走在路中央,此时此刻她在权衡二十个不同的想法,这才压下了一团火气隐而不发;然而平静的表象下蓄积着一连串即将迸发的咒骂。万般愤懑郁积于胸,她由此而发出了一阵低沉的轰鸣声,这是狂怒的前兆,可布丽吉德却偏偏在这时候哇哇大哭起来:这可怜的孩子实在是累坏了,再也受不了烈日的曝晒,而休玛斯倔强地忍受着恶劣的环境,可是男孩的自尊维持不了两分钟。为了安抚孩子们,瘦女人收敛了怒火,淡忘了自己所受的苦。
必须快点找到有水的地方:对于瘦女人这实在是小菜一碟,芸芸众生对水源的敏感乃是天性,她也不例外,她立刻领着孩子们轻手轻脚地往另一个方向去。几分钟以后他们在路边找到了一口井,这才放下心来。
井边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们就坐在树荫下吃蛋糕。
趁着这会儿休息的功夫,瘦女人传授给孩子们很多金玉良言。她没有一次性教给两个孩子,而是先后对休玛斯和布丽吉德传授两个不同的道理;据她所说,男孩所学的东西女孩不一定要懂。如何规避女人,这就和如何觅食一样,是一个男人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她把这些教给休玛斯。而与此同理,一个女人必须擅长于把男人控制在股掌之间,布丽吉德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些。
她谆谆教导,一个男人必须恨所有女人才能爱上一个女人,但是那样的话他就自由了,或是处于压力之下,他爱所有同性——男人。女人也必须像爱自己那样爱她的同性,她必须只爱一个男人而恨其他所有男人,并且必须把这唯一的男人也变成女人,因为女人拥有暴君和奴隶的双重天性,而且比起做暴君,她们做奴隶更有天赋。她解释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永远有打不完的仗,彼此都恨不得对方心悦臣服;可是女人往往被一个叫“怜悯”的心魔束手束脚,永远在男人面前自乱阵脚,从而一败涂地。她告诉休玛斯,当他爱上一个女人,他的世界末日也就到了,因为他会为了迁就那女人的任性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她会为了鱼水缠绵而索求他的爱。她告诉布丽吉德,当一个女人知道自己被人所爱,她的世界末日也就到了,因为男人对恋爱的激情并不能持续太久,女人却会全心全意地为爱付出,从而沦为爱的奴隶,不仅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还会如痴如狂,失去自我。命运女神从来就对男人宠幸优渥,然而她断言,女人必须是胜利者,因为敢于对抗神的人都取得了胜利:这是人生的定律,弱者必须奋起抗争。强者的力量总有一天要腐朽衰退,而弱者却无畏失去,狡兔三窟就是弱者的智慧。
综上所述,人生不可以停滞,女人必须千方百计地把丈夫变成女人;这样她们就可以奴役丈夫,人生就会翻开崭新的一页。
瘦女人越说越高深,她的思维终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她决定继续上路,等天凉快一些,再理顺自己的思路。
他们把蛋糕重新装进口袋,这时他们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胖女人向水井走来。这个女人走近水井,向瘦女人行礼,瘦女人也回了礼,陌生女人坐了下来。
“这天可真热,”她说,“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长途跋涉可真够呛。你是赶了很远的路吗,太太,还是你已经习惯了走这么多路?”
“不远。”瘦女人说。
“远还是近,”陌生女人说,“我喜欢在这个季节旅行,也喜欢找个地儿坐下来。你身边这两个孩子真是招人疼爱,太太。”
“是可爱,”瘦女人说。
“我自己有十个孩子,”女人又说,“我总是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把他们生下来的。一个女人生了十个孩子却一文不名,也没人感谢我,这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是的。”瘦女人说。
“你说话有超过两个字的时候吗,太太?”陌生女人说。
“有的。”瘦女人说。
“我要付一便士买你说话,”女人生气地回答,“我从没见过脾气比你更坏,嘴皮子比你更尖酸的女人。就在昨天我还跟一个男人说,瘦女人都是坏女人,并且没有比你更瘦的女人了。”
“你之所以这么说,”瘦女人冷静地说,“是因为你很胖,你不得不自欺欺人来粉饰你的惨状,你爱干嘛就干嘛。这世界上没人愿意发胖,好了我得走了,太太。你尽可以戳瞎你自个儿的眼睛,但拜托你离我远点,那么,再见了;若是我脾气坏一点,我会揪着你的头发拖着你山上山下来回跑两个小时,现在就到此为止吧。我已经赏了你不止两个字了;你给我小心收好了,否则我会赏你更多字儿,它们会变成水泡永远烂在你的身上。孩子们,现在跟我出发吧,若你们见到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你们就会知道,她会吃到站也站不起来,喝到坐也坐不起来,睡到脑子一片空白;若是那种女人开口和你们说话,可别忘了跟她说两个字就是对她天大的恩赐,并且这两个字也要越简短越好,因为像她那样的女人就是当叛徒和贼的料,因为她太懒了,只配当个酒鬼,上帝保佑她,好吧,再见了。”
瘦女人和孩子们站起身来,告别了陌生女人,沿着大路前行;而另一个女人却仍然坐在原地,一言不发。
瘦女人一路走一路生闷气,她的脸拉得老长,孩子们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因此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不再接近她,而是专心致志地玩起了游戏。他们绕着她来来回回地跳起舞来。
孩子们追逐打闹,高歌大笑。他们有时候扮成一对小夫妻,沉默地并排走着,时不时故作高深地谈论着天气、健康或是黑麦地什么的。有时扮成马和马夫,当马的那个撒着欢儿,鼻子里发出低沉狂暴的长啸,马夫则高声吆喝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扮成一个耗尽了脾气的车夫,吃力地赶着一头奶牛赶集去;他们还扮成两只耳鬓厮磨的山羊;他们的游戏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夜幕降临以后,巨大的沉寂笼罩着他们。空气中除了他们尖锐刺耳的吵闹声,什么也听不见。在这广袤无止境的寂静的渲染下,他们也渐渐安静了下来。他们放慢了脚步,一左一右走在瘦女人的身侧,小声地交谈,最后就连这嘀咕声也听不见了。接着,布丽吉德?贝格拉住瘦女人的右手,詹姆斯随后也轻柔地握住她的左手,孩子们的体贴与安慰抚平了瘦女人心中汹涌的愤怒。
他们走着走着,看见一头奶牛倒在一块地里。看到这只大块头动物,瘦女人若有所思地停下脚步。
“所有东西,”她说,“都归行路人所有。”说着她就走到地里去,把奶牛的奶挤到自带的容器里。
“我想知道,”休玛斯说,“那头奶牛的主人是谁。”
“也许,”布丽吉德·贝格说,“那根本就是一头无主的奶牛。”
“奶牛的主人就是它自己,”瘦女人说,“没人可以占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敢说它是心甘情愿挤奶给我们喝的,因为我们都是谦谦君子,不是贪婪虚伪的小人。”
被放开的奶牛再次躺倒在草丛中,继续它的沉思。畏惧于漆黑的夜幕,瘦女人和孩子们蜷缩着偎依在这头暖和的动物身旁。他们就着瓶中的牛奶,开心地分吃着口袋里的蛋糕。奶牛用自己温暖的怀抱欢迎他们。奶牛的眼睛亲切而温暖,对孩子们无比慈爱。孩子们不停地扔掉手中的食物,空出手来拥抱奶牛的脖子感念它的恩情,当着它的面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
“奶牛啊,”布丽吉德·贝格欣喜若狂地说,“我爱你。”
“我也是。”休玛斯说,“你留意它的眼睛没有?”
“为什么奶牛有角?”布丽吉德说。他们就此向奶牛询问,奶牛却笑而不语。
“要是一头奶牛和你说话,”布丽吉德说,“它会说什么呢?”
“那我们就扮成奶牛,”休玛斯回答,“那样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找到答案。”
他们于是就扮成了奶牛,吃了几片草叶,可他们发现一旦扮成了奶牛,除了“哞哞”叫唤以外什么都不想说,他们就认定奶牛同样如此,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也许,本来就没什么可说的。
一只身段细长的黄色苍蝇正往那个方向飞去,他停在奶牛的鼻子上休息。
“欢迎光临。”奶牛说。
“这是绝佳的行路夜。”苍蝇说,“可是我们有个伙伴飞不动落单了。你在这附近见过我们的伙伴吗?”
“没有,”奶牛回答,“今晚除了甲壳虫什么也没有,而甲壳虫是不会停下来聊天的。我觉得你的生活可真悠闲自在,四处云游,尽情享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苍蝇一边嘀咕着一边用右翅擦着腿。
“有人会像对待我这样压在你背上睡觉吗,有人会偷你的奶吗?”
“到处都是讨人厌的蜘蛛,”苍蝇说,“所有的边边角角都被蜘蛛占据;它们埋伏在草丛里,随时准备咬你一口。我扭伤了,我四处搜寻它们的踪迹。它们丑陋又贪婪,毫无礼貌,恶心至极,恶心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