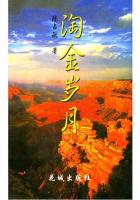‘哈,’艺术家笑咪咪地说道,‘您还敢再嘴硬,说自己不是女人?’
他们又和同伴汇合到一起,在卢多维西别墅的树林中漫步,那时候,这别墅归红衣主敎基科尼亚拉所有。对于热恋中的雕塑家来说,这个早晨流逝得太快了,但这个早晨,小插曲纷至沓来,向他展示了她的妩媚、脆弱和娇羞,这柔嫩无力的灵魂。这就是女人,她的恐慌突如其来,她的任性不明不白,她的紊乱直觉本性,她的放肆难解其怀,她恫喝吓唬、虚张声势,她的情感却又那么细巧美妙、敏感非凡。这支欢乐歌手组成的小部队正在冒险挺进一片原野,不一时却望到远处开来一班人马,全副武装,其行头打扮更是让人心惊肉跳。有人道:‘是土匪!’大家连忙紧赶脚步,往红衣主敎别墅的围墙里躲。就在这紧要关头,萨哈西妠瞥见?妣娜拉脸色苍白,无力前行;他把她抱起来,捧在怀中跑了一阵。到了临近的一个葡萄园边,他才把心上人放下。
‘说给我听,’他问她,‘为什么这极端的脆弱,放到任何其他女人身上都让我觉得丑陋,让我讨厌,我只要看到一点点这样的迹像就爱意全消;可到了您身上,却让我这么欢喜,这么着魔?’……‘哦!我是多么爱您啊!’他又说,‘所有您的缺点、恐惧、小心眼儿,都为您的灵魂增添了难以言喻的优雅。我觉得我会厌恶强悍的女人,像萨福[20]那样的,英勇,精力旺盛,激情澎湃。喔,柔弱甜美的生灵!你还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呢?这天使的嗓音,这娇柔的嗓音,如果不是从你,而是从另一具身体里发出来的,那可真是倒错了。’
‘我不能,’她说,‘给您任何希望。不要再这样对我说话了,别人会笑话您的。我不可能禁止您去剧院;可是,您若是真地爱我,或者,您要是个聪明人的话,那您就别再去了。听我说,先生……’她的语气严肃低沉。
‘哦,你住嘴!’醉梦中的艺术家说道。‘阻碍只会把我心里的爱拨得更旺。’
妣娜拉仍旧保持着优雅端庄的态度;但不再说下去了,仿佛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已向她揭示了某种不幸。到了回罗马的时候,她坐进一辆四座厢式马车,并命令雕塑家一个人坐那辆双座马车回去,态度凶狠蛮横。在路上,萨哈西妠打定主意,要把?妣娜拉劫走。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制定计划,一个比一个离谱。夜幕降临,他出去找人打听心上人所住公馆在哪儿时,在大门口遇到一个同学。
‘亲爱的,’后者说道,‘是大使派我来的,请你今晚到他那儿去。他要办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你要是知道赞比内拉也会去……’
‘赞比内拉!’萨哈西妠大叫,一听到这名字就神魂颠倒,‘我为了她都疯了!’
‘大家和你一样,’同学回答他。
‘可你们要真是我朋友,你、维昂、洛特布尔,还有阿莱格杭,你们聚会结束后来给我帮把手好不好?’萨哈西妠问道。
‘不会是要杀什么红衣主敎吧?……不会……’
‘不会不会,’萨哈西妠说,‘我决不会要你们做任何正经人做不出来的事。’
不一会儿,雕塑家就为确保事情成功安排好了一切。他是最后一批才到的大使馆,却是乘旅行马车来的,套的都是壮马,驾车的是罗马一个最不怕事儿的/vetturini/马车伕/。大使馆里人山人海,这些在场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个雕塑家,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客厅,此时,赞比内拉正在那里演唱。
‘一定是为了照顾在座的红衣主敎、主敎、修道院长,’萨哈西妠问道,‘/她/才穿的男人衣服,/她/脑袋后面还套了发网,戴了卷发,佩了长剑?’
‘她!哪个她?’萨哈西妠致问的这位老爵爷反问道。
‘妣娜拉。’
‘妣娜拉?’罗马大公重复道。‘您这是在开玩笑吗?您是哪里人?罗马的舞台上何曾出现过女人?难道您不知道,在敎皇的国度,女人的角色都是由什么样的生灵来充任的?是我,先生,是我给的赞比内拉这副嗓子。这个小滑头的钱,都是我付的,连他的声乐老师都是。他倒好,对我给他的扶持,连点感激之情都没有,连我的家门都再不肯踏进半步。不过呢,话说回来,要是他发了迹,那可全都是多亏了我。’
当然,基吉亲王可能还说了好久,但萨哈西妠没有听下去。一个恐怖的真相刺穿了他的灵魂。他如被雷劈了一般。他僵在那里,视线死死拴住这个所谓的男歌手。这火舌般的眼神在赞比内拉身上有一种磁性的作用,因为这/musico/谣哥儿/的目光终于突然落到萨哈西妠身上,天籁般的歌声随即变了质。他发起抖来!一阵不由自主的窃窃私语,从会场中,从他认为的系恋自己双唇的听众中,流逸出来,这使他彻底乱了;他坐了下来,咏叹调也不唱了。红衣主敎基科尼亚拉用眼角瞄了瞄他宠儿的视线,觑到了法国人;他向一个待从敎士欠过身去,象是在打听雕塑家的名字。得到想要的答覆后,他极仔细地凝视了艺术家一番,给一个神甫下了几道命令,那人一闪消失了。与此同时,赞比内拉缓了过来,重新唱起刚才任性中断的那首歌;可他唱得很糟,并且不顾众人的再三要求,拒绝唱别的。这是他第一次显露出这种任性霸道;这种任性霸道,在后来,就像他的才华和巨额财产一样,使他闻名遐迩;而这财产,据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歌喉,而且还得自于他的美貌。
‘这是个女人。’萨哈西妠说道,还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这里面有奸情。红衣主敎基科尼亚拉在蒙骗敎皇和整个罗马!”
雕塑家当即跑出客厅,找到他的朋友,把他们埋伏在使馆院子里。赞比内拉确信萨哈西妠走了之后,似乎恢复了些许镇静。临近午夜时分,这/musico/,如男人搜寻敌人一般,把几个厅室都转了个遍,随后离开会场。正要跨出使馆大门之际,他被几个人迅疾抓住,嘴被手帕堵了起来,塞进了萨哈西妠租来的马车。赞比内拉吓呆了,缩在一角,一动也不敢动。他看到自己面前,艺术家那张可怕的脸保持着死亡的沉默。路程短暂。赞比内拉被萨哈西妠劫着,很快便身处一个阴暗、空荡的雕塑室中。男歌手已是半死,缩在椅子上,不敢正眼瞧一下那尊女性塑像,他认出那上面有自己的特征。他一声不吭,牙齿却格格作响。整个人都吓僵了。萨哈西妠大步踏来踏去。突然,他站在赞比内拉面前。
‘给我说实话,’他的声音低沉混沌,变了质。‘你是不是女人?红衣主敎基科尼亚拉……’
赞比内拉跪了下去,只是低头不答。
‘啊!你是女人,’艺术家大叫,神魂颠倒;‘因为就算是个……’
他作了罢。
‘也不会,’他又喊了起来,‘/他/也不会这样低三下四。’
‘啊!请不要杀我。’赞比内拉哭成了泪人。‘我只是为了讨好同事才答应骗您的,他们只是想笑笑。’
‘笑笑!’雕塑家的嗓音中闪出了恶魔的音色。‘笑笑,笑笑!你竟敢戏弄一个男人的激情,就你?’
‘噢!饶了我吧!’赞比内拉呼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