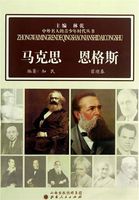辛弃疾赞许地点点头,说道:“问得好。‘词’这种诗体在隋唐时代就出现了,它起初产生于民间,是歌伎和乐工配合音乐的节拍所演唱的歌词,所以叫做‘曲子词’。后人因为它在句式上有长有短,参差错落,又叫它‘长短句’。这种形式的诗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一般词人都用来描写离情别绪和风花雪月,后人竞相模仿,连篇累牍,尽是靡靡之音,一点刚健雄浑的气概都没有。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才是词的本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词人生活的圈子太狭溢了,生活的内容太空虚了。尽管他们拚命加上华美艳丽的辞藻,但所写的歌词总是缺乏生气,对国家没有用处,对人们没有帮助。所以在我看来,要想写出好的诗词,不独要在技巧上下功夫。古人说,‘诗言志’。诗是这样,词也是这样。”
范开说道:“老师的意思,学生明白了。这样说来,‘婉约’的风格并不是词的本色,是吗?”
“对,”辛弃疾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不认为‘婉约’是词的本色,就同我不认为‘温柔敦厚’是诗的正宗一样。但是判断一首诗词的好坏,主要的还是看它对国家、对人们有没有补益。记得我幼年在亳州的时候,有一个叫刘瞻的,曾经做过我的塾师——后来他卖身投靠金人了。当时他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诗,道是‘厨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这两句诗在字面上对仗得十分工稳,但内容却是空空洞洞,言之无物。这样的诗,就是写了成千上万首,又有何用呢!今天要写诗填词,首先就应该想到神州陆沉,中原未复,应该把咱们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壮志豪情在诗词当中抒发出来,并且用这样的诗词去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心,鼓舞人们同仇敌忾,誓与金贼不共戴天!譬如韩老相公送给我的那首寿词,一开头就勉励我要关心消灭金贼、恢复中原的大业,而不是象一般寿词那样,什么‘寿比南山松不老’呀,什么‘福如东海水长流’呀……韩老相公这样的词,才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高昂,你说是吗?”
一声马嘶,从马厩里传了出来。辛弃疾携着范开的手,向马厩走去。
那匹乌龙驹——耿京当年的坐骑,正伏在马槽里吃草。看见辛弃疾来了,昂起头,眼睛直望着主人。辛弃疾走到它的面前,亲切地在马背上拍了拍。那马好象受到鼓励一般,竖起鬃毛,又发出了一声长嘶。
“廓之,”辛弃疾喊着范开的别号,满怀感慨地说道,“你看这匹马虽然老了,可是它还念念不忘驰骋千里!三国时曹操写过一首著名的《步出夏门行》诗,中间有这样几句:‘老骥伏枥(马槽),志在千里;烈士(有雄心壮志的人)暮年(晚年),壮心不已(不止)。’写得多好!”说到这里,他不禁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我再能骑上骏马,走上沙场杀敌呢?”
马被牵出了马厩。辛弃疾翻身上马,在带湖边上跑了两圈。那马虽然巳经衰老,但一刹那之间,它又仿佛恢复了当年的骠劲,再也不肯歇脚,仍然不停地在湖边奔跑,而且越跑越快。辛弃疾暗暗叹息道:“这马也象我一样,志在千里啊!”
经过一段难以忍受的日子,辛弃疾对于罢官闲居的生活,总算是逐渐习惯下来了。他很快就爱上了勤劳的农民和俭朴的农村生活。由于从小就在农村中长大,特别是经过四风闸的起义和在耿京部下的一段战斗生活,他对农民的看法和感情同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深深知道,在敌占区内,农民组成的义军是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没有这支力量,北伐的大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他曾批判了那些不愿意在农民起义领袖下面俯首听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的怨愤,是女真统治者必然灭亡的主要因素。对于农民的生产劳动,他也是抱着尊重态度的。他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就是说,人生在世,应该勤劳,而从事耕种,便是人生第一要义。所以他不但把自己在上饶盖的新居称为“稼轩”(“稼”就是耕田的意思),而且还用“稼轩”这两个字做了自己的别号。
在“稼轩”的左方,有一块稻田,是当年辛弃疾设计他的新居时特地留下来的。现在罢官在家,闲居无事,每逢耕耘收获的季节,他就常常来到田边,偶然参加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作为“以力田为先”的象征。这样,当稻谷放香的时候,他也能分享到丰收的喜悦。附近农民知道他做过大官,开始时跟他关系比较疏远。经过几次交往,特别是当他们了解辛弃疾曾经在农民起义队伍里战斗过的经历后,跟他的距离也就逐渐缩短了。
在“稼轩”附近,有一座简陋的茅屋。主人是几年前从苏州一带流落到这儿来的吴老汉。因为是邻居,所以辛弃疾同他结识得也最早。每次外出散步,辛弃疾总要从他家前经过,有时歇歇脚,聊聊天。
这年六月的一天,辛弃疾在带湖边骑马跑了一阵以后,感到有些疲乏,便牵着马慢慢地向家中走去。猛抬头,只见吴老汉那座低矮的茅屋前面,一株枇杷树已经结出了累累果实,在阳光下发出金黄色的闪光,吴老汉正兴致勃勃地采摘着。辛弃疾刚要招呼,吴老汉巳经看见他了,招手叫道:“来老汉家坐一晌,尝尝刚摘下的新鲜果子!”辛弃疾感到一阵喜悦,便把马拴在一株树上,走进吴老汉家的小园子。
“坐下吧,”吴老汉端来了一张矮小的木凳,筛了一碗米酒,捧了好几串枇杷,笑嘻嘻地说道,“喝一碗新酿的水酒,尝几个新摘的枇杷!”
辛弃疾在主人的盛情招待下,也不客气,一边吃,一边闲聊起来。
“吴老汉,”辛弃疾笑着说道,“今年收成不错吧?”吴老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瞒你说,今年幸亏风调雨顺,交了租税以后,还能勉强过日子。你还没见到我老汉往年的景况呢,不要说青黄不接的时候了,就是稻谷登场以后,用不着多久,瓮里就没有一粒米啦!哪一年不是靠糠、菜、树皮、草根来糊口呢!”
辛弃疾点点头,为自己和邻居在生活上的巨大差距而暗暗感到惭愧。
“老伴,你也来尝尝新!”吴老汉对倚着门边的老妻招招手,看样子他巳经有几分醉意了。
老妻微笑了一下,关切地对吴老汉说道:“你们吃吧。少喝点,小心醉了。”
“我不会醉的。”吴老汉敞开衣襟,又对正在院子里编织鸡笼的第二个儿子叫道,“你阿哥和阿弟呢?”
“阿哥在小溪东面锄豆子,阿弟睏在溪边剥莲蓬呢!”二儿子放下鸡笼,站起身来朝小溪那边望了望,然后征求意见似地问道,“要不要我去喊他们?”
吴老汉“嗯”了一声:“豆子是要赶紧锄了。也罢,留点果子下来给他们吃。”
吴老汉一家人说话,都是用的苏州话。辛弃疾曾经在江阴等地住过一段时间,因此对苏州话也能大体听懂。他喜爱苏州话的声调,但他更喜爱吴老汉一家的淳厚朴实。乘着酒兴,他对吴老汉说道酒喝足了,果子也吃饱了,怎样表示谢意呢?这样吧,我就用《清平乐》的调子唱一首歌词给你听,怎么样?”
“好呀,只怕老汉听不懂你那文绉绉的一套。”吴老汉笑道。
“你一定能懂。不信我念给你听听。”辛弃疾说到这里,满有信心地轻声吟道: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吴老汉听了,拍手笑道:“你这不是说的老汉一家刚才的事情吗?除了‘无赖’两个字,剩下的老汉都能听懂。”
“‘无赖’就是调皮的意思。”辛弃疾解释道。
吴老汉又笑了。“不过他脸色显得严肃起来,接着说道,“你把我们庄稼人的日子说得太美了。你还不了解我们。你没有仔细看看我们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说实在话,有时它比黄连还苦三分啊!”
是的,由于阶级的局限,出现在这一时期辛弃疾笔下的农村,往往是一幅幅恬静、安宁、欢乐的画面。他很少描写农民的苦难和艰辛,更没有讴唱他们的愤怒和抗争。因此这些歌词虽然也用清新的笔调,写出了农村生活的某一个侧面,但毕竟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出广大劳动农民最本质的东西。从立场到思想感情,他和劳动农民之间终究存在着一条鸿沟。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忘怀北伐中原。对女真统治者的仇恨,对中原的怀念,以及统一祖国的宏图和驰骋沙场的壮志,常常涌到他的笔底,虽在长期闲居期间,他还是写出了不少富有战斗豪情的词章。他一方面为自己被排挤的遭遇唱出了悲愤的高歌,一方面又用慷慨激昂的歌词来鼓舞老朋友抗金杀敌的壮志。不管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还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夜,每当他唱到自己写的“长安正在天西北”、“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之类的词句时,总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旁倾听的老朋友也都感动得热血沸腾。
辛弃疾绝不满足于用词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他渴望的是将这种爱国热情化为横刀跃马、沙场杀敌的战斗生活。他需要笔,但他更需要的是刀,是剑,是复仇的烽火,战马的嘶鸣,冲锋的号角……
这一天终究会来到的,是的,一定会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