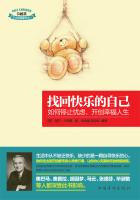第六章 诱惑8
威根姆改变态度
在你刚才听到露西和她父亲那次谈话后的第三天,露西趁麦琪去看葛莱格姨母的当儿,就设法和费利浦密谈了一次。整整一天一夜,费利浦一直认真地考虑着露西在这次会面中对他讲的话,最后他毅然决定采取行动了。他以为现在他和麦琪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可能改进,至少可以消除他们中间的一重障碍。他下定决心,将先后步骤耐心而仔细地安排了一下,就像一个刚开始对下棋感兴趣的棋手那样;他忽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天才的战术家,连他自己都感到诧异。他的计划不仅精细周密,而且颇富魄力。他看了父亲一会儿,发现父亲无急事要干,正在看报,就走到父亲背后,一只手搭在父亲肩膀上,说:
“爸爸,您愿意到我屋子里去看看我最近的写生画吗?我已经将它们陈列起来了。”
“我的关节已经硬得不能再爬你的梯子了,费尔,”威根姆放下报纸,慈祥地望着他的儿子说,“不过还是上去看看吧。”
“这地方对你很适合,是不是,费尔?——屋顶上照下来的光线好得很哪,你说是吗?”威根姆同平常一样,一进画室就这么说。他喜欢提醒自己的儿子:这一切都是父亲宠爱儿子才给他的。他一直是个慈爱的父亲。哪怕艾米莉死而复活,在这一方面也没法责备他。
“唔,好,”他夹上了双光眼镜,停下来之后,就坐在椅子上往四周打量,“你布置得好漂亮啊!我敢说,你的画实在和伦敦那个画家的作品不分上下——他叫什么名字——李本恩花了那么多钱来买他的?”
费利浦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坐在画凳上,手里衔着一枝铅笔,画出几笔有力的线条来消除胆小的感觉。他看着父亲站起来,慢腾腾地绕着屋子走,好心地停下来欣赏他的画,按照他父亲对风景画的欣赏能力来说,实在不可能看那么久。后来威根姆走到放着两张肖像画的架子跟前,停了下来。两张肖像画一大一小,小的一张镶在皮框子里。
“咦!你这又画的什么呀?”威根姆刚才看到的全是风景画,这当儿突然看到肖像画,感到惊奇,“我还以为你早就不画人像了。这两个人是谁啊?”
“两张都是一个人像,”费利浦镇定而迅速地回答,“只是年龄不同。”
“是谁?”威根姆严厉地问,眼睛盯着大的一张,越来越显出疑心的样子。
“塔利弗小姐。那张小的是我在金斯劳顿和她哥哥同学时候的她;那张大的是我从国外回来时候的她,不过画得不怎么像。”
威根姆猛地转过身子,脸涨得通红,听完把眼镜取下来,恶狠狠地看了他儿子一会儿,仿佛要将这个大胆的弱不禁风的人从画凳上打下来似的。可是他却又倒在扶手椅上,将手插在裤袋里,不过还是气呼呼地望着自己的儿子。费利浦并没有向他看,只是安静地坐着,望着铅笔头。
“那么,你是不是说,从国外回来之后,和她还有过来往?”威根姆终于花了很大力气才开口。人们在发怒的时候常常因为不能动手殴打,就尽量将话说得凶些来惩罚对方,但结果都是白费力气。
“是的,在她父亲去世前的一年里,我常常看到她。我们常常在道尔考特磨坊附近的树林——红苑——里见面。我十分爱她,我永远不会再爱别的女人。从她小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念她了。”
“说吧,先生!后来你还是一直和她通信?”
“没有。起先我什么都没有说,一直到我们快分别的时候,我才告诉她我爱她。她答应她哥哥不再同我见面或通信。我不敢肯定她是不是也同样爱我,或同意和我结婚。不过,要是她同意——她确实也很爱我——我一定要和她结婚。”
“你就这样来报答我对你的宠爱!”威根姆说,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费利浦沉着的反抗和坚定的意志让他无法可想,他气得哆嗦起来。
“不,爸爸,”费利浦说,他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他父亲,“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报答。您一向非常宠爱我,不过我一直认为您抱着一个慈爱的希望,要尽可能让我分享些不幸的命运所允许给我的福分,并不希望我来报答您,用我的一切幸福来满足您那永远不会有的感情。”
“我相信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儿子都会有他们父亲的感受,”威根姆异常严厉地说。“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是无知的疯狂的畜生,险些儿将我谋杀了。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她哥哥也是那么蛮横无礼,只是稍微冷静一些。你说他不让他妹妹同你见面,你要是一不小心,准会被他打得粉身碎骨,就为了你过得更幸福。可是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想你已经估计到后果了吧。当然,你用不着受我的管束。只要你高兴,明天你就可以跟那个姑娘结婚,你已经二十五岁了。你可以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以后我们互不相干。”
威根姆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却不知为何停了下来,不但没有出去,反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费利浦过了很久才回答,声调较刚才更镇定,更明确,听起来更刺耳。
“不,要是我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来养活她,即使她愿意嫁给我,我也不能娶她。我没有受过任何专门教育,干哪一行都不行。我不愿意她嫁了一个残疾丈夫又再受到贫困的折磨。”
“唔,毫无疑问,你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依靠我了。”威根姆仍旧严厉地说,虽然费利浦最后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二十几年来习以为常的感觉。他又倒在椅子上了。
“我早就料到这些了,”费利浦说。“我知道父子之间常常会发生这种冲突。如果我和像我这样年纪的青年一样,我就可以用更愤怒的话对付你那些愤怒的话——我们就可以脱离关系——我就会和我心爱的人结婚,和别人一样幸福。您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要是您现在要将这个目标废除,认为只有这样您才满意,那您比其他做父亲的更容易做到。您完全可以剥夺我生命中唯一的幸福。”
费利浦停了一会儿,他的父亲却默不吭声。
“那种可笑的深仇宿恨,只有到处流浪的野蛮人才有,您很明白,除了报这种仇外,还有什么事能使您心满意足?”
“可笑的深仇宿恨!”威根姆冲口而出,“什么意思?他妈的!难道被乡下人用马鞭子抽了,还得去爱他?还有他那个冷冰冰的神气活现的鬼儿子,我们结账时他对我说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要是值得,早将他一枪打死了。”
“我说可笑的是深仇宿恨,并非指您怨恨他们,”费利浦说,他也有理由同意他父亲对汤姆的看法,“不过也不值得这般念念不忘地报仇。我指的是您仇视一个无可奈何的女孩子,仇视一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一点儿也不赞同家里那些狭隘偏见的女孩子。她从不去管这种家庭纠纷。”
“那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女人干些什么,我们才不管呢!我们只管她是谁家里的人。想和老头儿塔利弗的女儿结婚,对我来说,完全是件可耻的事。”
在这次谈话中,费利浦还是头一次失去自制力,气得脸都红了。
“塔利弗小姐,”他尖锐地说,“是高贵的,只有粗汉蠢夫才会说她庸俗。她非常优雅,所交的朋友,无论是谁,都被人认为是非常正直而可敬的人。我想,在圣奥格镇上,人人都会说我配不上她。”
威根姆以凶猛、猜疑的目光望了他儿子一眼,可是费利浦并不看他,过了一会儿,费利浦忏悔似的继续说,似乎是在进一步解释他最后一句话:
“在圣奥格镇上,任何人都会对你说,像她那么漂亮的姑娘嫁给像我这样可怜的东西,真是太可惜了。”
“她才不配呢!”威根姆又站了起来,突然感到了父亲的尊严,忿恨地说,“才配不上呢。要是一个女人真正爱上一个男人,决不会讨厌他那因意外造成的残疾。”
“可是女人往往不会爱上残疾人。”费利浦说。
“那很好。”威根姆相当粗暴地说,他想要恢复以前的态度,“既然她不爱你,你何必自找麻烦来向我提及她,何必要我拒绝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威根姆迈开步子走到门口,头也不回地随手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费利浦根据以往的经验,相信他父亲最后一定会迁就他的,可是这场争吵震动了他那像女人般脆弱的神经。他决定不下楼吃晚饭。那一天他简直不想再跟他父亲见面。威根姆有个习惯,在家里没有伴儿的时候,晚上就出去,总是七点半就出去了。将近黄昏的时候,费利浦锁上房门,准备出去多散一会儿步,待他父亲出去以后再回来。他乘船划到下游一个他心爱的村子上,在那儿吃了晚饭后,一直待到可以回来的时候才回来。他以前从未跟父亲吵过架,他非常担心这次吵架不过是刚开始,也许会拖上几个礼拜,谁知道在这期间不会发生意外呢?他不愿弄清楚这个无意中想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结局。可是,一旦他能被公认为是麦琪的情人,他就不会模模糊糊地担心了。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画室,感到有些疲乏,往扶手椅上一靠,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画里的山山水水,后来他渐渐睡着了,梦中他看见麦琪从一条从前流过瀑布的、泥泞的、闪闪发亮的绿色山道上滑下来,他一筹莫展地望着她。突然,一阵听起来似乎很可怕的声音惊醒了他。
原来有人将门推开了,其实他并未睡多久,因为暮色看不出有何改变。进来的是他的父亲,费利浦在让坐的时候,他父亲说:
“你坐吧。我喜欢走走。”
他在屋里来回踱了一两次,接着站在费利浦跟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谈话从未被打断似的接着说:
“可是这姑娘似乎很喜欢你,否则她不会用那种方式和你见面。”
费利浦的心怦怦地跳得很快,脸上像掠过一道闪电似的飞起一阵红晕,如果要一下子说出话来,倒很不容易。
“在金斯劳顿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我了。因为自从她哥哥的脚受伤之后,我就常常去陪他。她一直将这件事牢记在心里,将我当作老朋友一样看待。她跟我见面的时候并没有将我当作情人。”
“可是,你终于向她求爱了。她怎么说的呢?”威根姆说着又踱起步来。
“当时她说她的确爱我。”
“他妈的!那你还希望什么呢?她是不是一个喜欢玩弄男人的人?”
“那时候她还很小,”费利浦犹豫地说,“我怕她还不能了解自己的感情。我还怕分离得太久了,而且我想到从那次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一定会将我们分开,说不定情况已经变了。”
“可是她现在住在镇上,我在教堂里见过她。难道你回来之后未跟她讲过话?”
“讲过,在迪安先生家里。可是由于某些原因,我不能再向她求婚。但是要是您能同意——要是您愿意将她看作您的儿媳妇的话,那么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可以解除了。”
威根姆沉默了一会儿,在麦琪的肖像前站住了。
“可是,她并不是你母亲那一类型的女人,费尔,”接着,他这么说,“我在教堂里看到过她。她比这张肖像更漂亮,眼睛灵活,身材苗条。我看到过的,不过看上去挺厉害,而且很难控制。你说呢?”
“她非常温柔热情,又那么单纯,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矫揉造作。”
“啊!”威根姆叫了一声,接着回过头来,朝他儿子打量了一下,“可是你的母亲看上去要比她和善。你母亲长着一头棕色的鬈发,一双同你一样的灰色的眼睛。你对她的印象不会很深吧。真可惜,我没有她的肖像。”
“那么,爸爸,要是让我也享有这种幸福,让我的生活过得更甜蜜,难道您不高兴吗?对您来说,没有一种结合会比二十八年前和我妈妈的结合更密切,而且从那时起您一直在使这种结合变得更加密切。”
“啊,费尔,只有你才了解我,”威根姆说着,将手朝他儿子伸过去,“只要可能,咱们之间可不能有一丁点儿意见。现在我该怎么办呢?你一定得告诉我。我是不是该去拜访一下那位黑眼睛的姑娘呢?”
障碍一旦消除了以后,费利浦就能和父亲畅谈他和塔利弗的关系了,谈塔利弗家想买回磨坊和土地的愿望,以及将磨坊让给盖司特公司来转一下手的方法。现在他可以大胆劝说并说服他父亲,威根姆的让步居然快得超出他的意料。
“磨坊我倒不在乎,”威根姆虽然恼火,却终于同意了,他说,“最近我为了磨坊,简直烦恼透了。只要补偿回我的装修费就行。但是有一件事,你不必向我开口,我决不会和那个小塔利弗直接成交。要是你为了他妹妹而轻信他,那随你的便,我可没有理由要轻信他。”
第二天,费利浦就去了迪安先生家,说明威根姆先生准备进行谈判。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愉快!露西向他父亲夸耀说这是不是证实了她伟大的交际天才时,是多么得意!这一切我都让你自己去想象吧!迪安先生却感到莫名其妙,疑心这些年轻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需要找出些线索。在迪安先生看来,年轻人之间的事和生活的正经事毫不相关,就跟鸟雀的飞翔和蝴蝶的嬉戏毫不相关一样,除非这种事会损害赚钱的事业。可是这件事却完全有益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