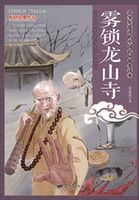我也闹不清楚怎么突然之间冒出一个光头来,当下一着急,便用另一只脚连连踹了几下。
“别……别……”
下面立即传来叫喊声,我一听是胡令堂的声音,急忙收回脚。
但胡令堂经我一番猛踹,已经撒了手,一边咳嗽一边向下面滚去,而且鬼使神差一般朝闸门口过去了。
如果胡令堂真得掉了进去,估计捞他就难了,所以当下一刻不敢耽搁,忙起身去追。哪料到那几层水浪跟长了眼一样,不见兔子不撒鹰,我站起来刚走两步,后面的水又到了,把我拍倒之后,往下冲去。
不过幸运的的是,我倒下去正好抓住了胡令堂的手腕。不幸的是,他现在大半个身子已经落入了闸门口。
要说胡令堂确实有那么两下子,眼见就要掉下去,瞬息之间,借着我的手,脚下一蹬石壁,身子一纵,竟然如同猿猴一样跳上了岸。
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长长的风衣裹着腿,滴滴答答往下滴水。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光头笔挺地站着,一串念珠挂在胸前,不时地左转身瞅瞅,右转身瞅瞅。
我指了指石碑下,胡令堂一弯腰将假发捡了起来,拧了拧水,卡在头上。
我心里暗暗好笑,但为了避免尴尬,强忍住没笑出来。
我见周围又恢复了平静,除了水坝上的水,一切又恢复如常。
照现在情况看,胡令堂这个人估计也靠不住。
要命的是,现在已是后半夜,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而我们两人浑身都湿透了,冻得不知该往哪里躲,隐约感觉身上结了一层霜。尤其是胡令堂把潮湿的假发套在头上,似乎一直觉得不自在,不时把手伸进去挠一挠。
“现在已经鸡叫头遍了,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先帮我找回亮子魂魄,再商量怎么收服它。”
“不行!”胡令堂咬着牙,斩钉截铁说道,然后周身上下摸了一圈,掏出两根蜡烛和一段红绳。
“有打火机吗,我要借兵!”
“借什么兵?”
“你的虎印雷击木已经不见了,我们就算把这东西引出来,估计……估计也降不了它。所以,我需要……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刃!”
胡令堂说着说着声音逐渐抖起来,两条腿不住地打摆子,时不时抬起那只没有鞋的脚一个劲儿在小腿上蹭。
原来他说的借兵,指的是兵刃,我以前听过借阴兵,借天雷,借星宿之气,或者请神请祖师爷,却从未听过借兵器。也不知道他要跟谁借,去哪里借。
胡令堂一瘸一拐上了水坝顶,我跟在他后面,心里不停地打鼓,这家伙前几年来过几次,也没能降得了这东西,还坑了不少同道中人,可见尽管他之前做了一些在我们看来看来很了不得的事,但是一码归一码,在这里他未必就能讨到便宜,更何况他爹当年都吃了亏。还有刚才闸门前想上来却被胡令堂打回去的鬼魂,会不会就是那些随他来的帮手?他们被胡令堂拽过来垫背,深陷这水下出不来,如果真是这样,那胡令堂的心未免太过歹毒了。
我心里正盘算着这里面的事,冷不防一个声音在耳边突然响起,“不能借!”
既真切又响亮,我浑身一抖,结结实实吓了一跳,赶紧转头四下看了看,但荒郊野外,暗夜如墨,哪里有半个人影。
是听错了?还是有人让我别去借兵?难道胡令堂借兵还要让我动手?
不知道是哪位鬼魂,或者神仙提点我,但一时也弄不清对方的身份,索性不去管他。
胡令堂在水坝上找了块相对平缓的地方,面朝水库,颤颤巍巍将两根蜡烛点上,左右相隔一米左右,照亮一小片地。然后他蹲在地上,颤颤巍巍给红绳子打结。因为天冷的缘故,他两个肩膀不停地耸动,身子不停地来回摆,看着像喝醉酒了一样蹲不稳,加上他的右手短了两个指头,所以打了半天愣是没打上。
“要……要帮忙吗?”
我冻得原地蹦了两圈之后,蹲在他旁边问道,胡令堂缓缓转过身来,微弱的烛光映在他脸上。
我见他脸色煞白如同宣纸一般,刀疤此时反倒不显得那么抢眼了,眉毛花白已经结了层霜,冻得发紫的嘴唇不自主地哆嗦,用细若蚊蝇的声音说道,“要……要……”
其实不仅是他,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哆哆嗦嗦伸出手,刚把红绳接过来,不料,一阵风吹过,将那两根蜡烛吹熄了。
我们两人抱着肩膀蹲在地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咬着牙,谁都不肯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我问道,“非……非得今天……今天借吗?”
胡令堂抱着脚,微微地摇了摇头。
“要不,改……改天吧?”
“好……好……好主意!”
他这么说,正中我下怀,其实从下面跟上来,我压根就没打算帮他借兵,现在诸多事情未明,我哪能稀里糊涂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谁能说的准我就是他爹嘴中的机缘人,万一不是呢。
其实胡令堂也是浪催的,你说现在都这样了,你还硬挺着要借什么兵。以他的性格推算,我估摸着可能是因为刚才吃了亏,脸上无光,因此想再露一手把面子往回找找。
何苦来的!
这是我与胡令堂第一次联手,也是最窝囊的一次,而且究其原因竟然是我们都觉得太过寒冷。多年后,每每回想此事,都暗叹可笑。
无话短说,我们各自回去,如何晾衣服睡觉搁下不提。
第二天,天蒙蒙亮,明叔就跑过来砸门,问亮子如何了,是不是要送医院。
我虽然躺在床上,但几乎没睡着,脑子一直在思考亮子的魂魄可能去了哪里,现在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却被明叔闹醒了。
我开开门,一阵冷气扑面而来,只见明叔站在门口正把手放在嘴边哈气,头上戴着遮耳皮帽,鼻子冻得通红,这倒没什么,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他那双眼。眼泡肿着,乌黑一片,俨然一双熊猫眼。
“明叔,昨个儿没睡好?眼咋黑成这样?”
明叔看了看我,幽幽说道,“还说我,你不是也一样!”说着进了屋,来到亮子床前,喊了几声,见亮子不答应,转头又看看我,“俺家老二这次是怎么了?以前也有昏迷不醒的时候,但过一夜睡一觉就好了,现在怎么还不醒?”
我叹了口气,安慰他说道,“明叔,你别着急,亮子现在走了魂儿,等他的魂儿回来自然就好了。”
我原以为明叔会吃惊,不相信,但事实上明叔显得很镇静,“魂丢了?不是只有小孩才会丢魂儿吗,这么大的人还能丢魂?”
明叔能这么说,我的心算是落了一半,毕竟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丢魂这一说的。但我没法回答他现在的问话,因为要是说开去,显得更玄,他未必就会信了。
明叔见我不回答,嘀咕道,“难怪我和你婶子昨天一夜都睡不好,心一直慌慌的,喘气都不匀,总觉得不对劲。还有那几口猪,嚎一夜,今天早上喂的时候,个个围着食槽绕圈圈,最后竟把食槽拱翻了!气得我挨个抽他们鞭子!”
我一听,也是诧异,人丁不安,六畜思异,确实是不祥之兆。不过,异象太显,且从时间上看,不像是亮子出事的前兆,难不成老太太要归位?也不对啊,老太太要是出事,最多子孙不宁,这些猪瞎掺乎啥!
于是我问道,“那老太太没事吧!”
“没事儿,刚才起床一个劲儿说想老二,就让我来喊你们去吃饭。谁想到,他丢了魂儿!”
明叔一句话点醒了我,俗话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说的是连气。所谓荫蔽子孙,积祖上阴德,其实说的也是上下贯穿之气,前人行善积德,后人得福。我想如果亮子的魂儿不在胡令堂那里,那就只有让老太太出马了。
我们知道,一般小孩子魂儿丢了,往往是最亲近的人才能把魂儿叫回来,亮子虽不是小孩,但生魂自囟门出,也遵循此理。
“这样,明叔,你等会把老太太领过来,把实话跟她说,让她坐在这门口给亮子叫魂!”
“这……”明叔脸上面露难色,“我怕老太太知道老二这样,会承受不了!”
是啊,这也是一个问题,老太太岁数大了,估计自己也知道时日无多,所以总是惦记家里的人,想多说几句话,多看几眼。这要是一听亮子半死不活的,还不心疼得死过去。
“我去找胡令堂,你在这守着!”说着我一指床前煤油灯,“千万别把这灯弄灭了!”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出门不远就听见后面有人叫我。
我回头一看,只见娟子拉着傻妞朝我跑过来,傻妞粉肥嘟嘟的脸上满是泪水,眼睛红红的,不住地抽泣。
我赶紧停下来,“怎么了这是?”
傻妞抢先说道,“爸,爸不见了!”
“你爸不见了?”我暗想,胖叔这么大的人,身上两条腿,肯定不可能成天待在家里,不见了就四处找找呗,用得着哭吗。但想归想,却不能这么说,“四下找过了吗?”
“找了,街坊邻居帮忙找了大半夜,就是找不到!”
我一听找了大半夜,便觉得事情没我想得那么简单了,“人啥时不见的?”
“昨天晚上,送那个老头儿走,就一直没回来。”
我昨晚害怕胖叔跟我谈傻妞的事,所以骗他去送刘瘸子,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也脱不了干系。
“那让三叔开车去刘瘸子家找找,指不定觉得晚了就在他家过夜了。”
“我爸住院了,去不了!”
娟子说得很淡然,并没有焦急的样子。我也纳闷,这娟子人性也太提不起来了。父女之间感情再不好,现在老子出事住院了,按道理,子女多多少少也会担心着急。她却处之安然,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三叔又怎么回事?”
“还是昨天喝酒喝的,后半夜一直吐,迈不动腿,清早起来找茶喝,一出门,被房上的瓦掉下来砸破了头,现在在村医院里包着呢!”
我一听,不由得哭笑不得,终年不遇的落瓦这么巧被他赶上了。不过,我似乎觉得更不对劲儿了,赵家人怎么了这是,才过了一晚,怎么接二连三地出了这些怪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难道昨天我跟胡令堂去招惹那东西,所以它过来复仇?可是这东西仅能乘雨而飞,现在风雨未动,它如何来得了。
“现在,怎么办啊!”
傻妞哭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