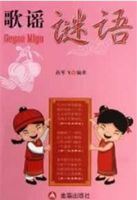在学术方面,由南宋开始的“浙东学派”,创立了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从而确立了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之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形成汉儒学经典以来的又一座学术高峰。明清和近代的江南学术思潮,如王阳明的哲学、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龚自珍的人学理念,形成了一条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并直接影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浙东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目的,注重关注现实政治事务,关注社会民生的实际状况,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坚持学术的根本价值在于服务于社会经济事务的方针,以增进社会成员的共识价值理念,维护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浙东学派”这种务实的学术精神,凸现了人的主体自觉精神,并赋予人的主体自觉精神以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人生意义。像王阳明对“心学”的探讨,其意义就在于强调任何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人,只要通过自我的不懈努力,都能够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至高无上的“天理”。王阳明在《传习录·上》中指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知兄自然是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良知,不假外求。”强调“心之本体”的自然特性,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心之自由”的本体意义。
“浙东学派”的这种哲学建构,其审美价值是对人的身心解放的强调,并强有力地支持了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最终定型。
从历史的维度上来考察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生成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的劫难是十分不幸和十分残酷的,但是,历史的劫难却又不自觉地造成一种原先人们并不能意料的现象的发生。对于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生成来说,历史的三次劫难(“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则是一个助推器。它促使了中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汇。显然,文化交流、交汇的结果,尤其是在同一质地结构内的文化交流、交汇,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互补,进一步促进文化自身特性得以更加强化的问题。通过南北文化的交流、交汇,“两浙”区域的江南文化(俗称“小文化”)并没有被淹没,反倒是获得了自身发展,形成自身特点的历史机遇。
文化人类学家指出:“一个文化如果将其形态完全展现,就可知道它是非常精致的,是一个在许多层次上交织着各种象征和意义的网络……任何元素都不仅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还受文化中象征秩序‘规则’的限制。”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的诗性审美品格,在南北文化交流、交汇中生成、发展和定型,除了受到江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环境的元素制约之外,受到大文化(即“中心文化”,或曰“整体文化”)和小文化(即“地域文化”,或曰“区域文化”)的双重制约,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受大文化制约上来说,大文化自身对诗性本体的强调,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陆性农耕文明的性质,在主张道德本体意义上的内心自觉,强调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对象存在的客体的和谐统一当中,形成了探究“心”之本源、突出主体“感时忧国忧民”的心智感悟,促成“心”之内向性活动的思想学说体系,尤为注重对文化的诗性本体功能的强调。从以“心”包容天下的特点来说,中国文化的文之“心”,是上对天,下接地,将作为主体的人与天地宇宙大化的灵气、灵性相融合,与心灵宇宙相融合,形成超越时空和世俗束缚的浩大的审美想象力。《淮南子·原道训》中指出:“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
为天下写“心”,在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中,就常常把世界的本体,宇宙的本体,看作是与人生、人心互为一体的现象,使人生、人心活动在不断的外化当中,以个体负载群体——民族、社稷、国家、天下之重任的方式,来走完有限的生命旅途,完成个体的使命——获得充实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最终超越个体的有限,进入无限的人生精神领域。从探究“心”之本源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心”,则是强调个体对于对象世界的独特心理感悟能力和主体智慧。探“心”之本源,是在“心”之内向活动中,向生命深处用“心”,实现生命的内在超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又表现为一种内倾性的审美意识导向。
“内省”的审美意识,使中国文学在审美形态上多呈现出沉郁、细腻、精致、优雅、平和的美学风貌,审美风格也多表现为含蓄、淡泊、和谐、空灵的艺术风采。可以说,大文化自身的诗性特质对“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的诗性审美品格的最终定型,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从受小文化制约上来说,“两浙”地域的江南文化,由于受到来自北方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汇与融合,不仅保存了大文化的诗性本体,而且还进一步发扬了大文化和小文化自身的诗性特色。其中,南宋时期文学艺术等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一个最好的脚注。历史的磨难,却在无意之中推动了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发展与定型。宗白华指出,魏晋六朝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形成这种审美特性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南北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叶舒宪在论述神话思维与诗性智慧问题时指出:“从文化比较的意义上看,每一种文明的建立和生长都伴随着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和逻辑理性的成熟,但由于在不同的文明中这种变革在方向上和程度上有所差异,所以由此铸塑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有的思维习惯和理性传统。”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在受到来自北方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之后,得以进一步的激活和铸塑。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后,这种情形则更是得以强化。所谓“柔风”渐起,实际上与南北文化碰撞、交汇与融合之后,对江南文化诗性思维、诗性特质的激活、铸塑有密切的关系。的确,江南文化有自身“柔美”特性的一面,这也正是古人在言及江南时,总是喜欢用“杏花春雨”和“小桥流水”来形容的一个原因,说的大多都是江南的“柔”和“小”的特征,即柔美多姿、柔情似水的诗性审美特征。这种情形反映在思维认知方面,也就是形成其“柔性”思维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柔”,《辞海》的释义是“‘柔’:嫩也;柔软也;温和特性;安抚,怀柔之意。”《辞源》的释义也基本相同。可见,“柔”不是“弱”的同义词,或替代词,而是主体的一种形态、方式、特征、风格的显现。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柔性思维,本身就具有一种诗性的特征。在文学艺术方面,其具体的内涵则是指: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受不同地域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以及作家自身主体诸因素(如个性特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作家的思维情感性特征往往呈柔性、温和的形态。
主体的柔情性特征十分突出,认知方面的感性判断、直觉判断十分明显,所表现出来的是主体对客观对象的诗意性、亲和性、怀柔性的认知与把握的特点;艺术知觉也多表现为对事物的表现性(非单一的再现性)、抒情性(非单一的叙事性)、写意性(非单一的写实性)的审美知觉;在思维的诗性成分、个性成分的构成方面,也多强调艺术的柔性元素和柔性表述,以形成艺术审美的柔美风格。所以,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的激活与铸塑,也是形成其诗性审美品格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的磨难,文化的融合,使“两浙”为主体的江南区域一度成为整个华夏文化的中心。历史学家在论述中国文化三次南迁现象时指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两浙”区域,特别是南宋定都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则又成为“江南的核心”。
“两浙”区域的江南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这对于“两浙”文化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历史学家在列举了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论证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既是吴越地区三次加速发展的机遇,也是吴越地区对中华文明的三次拯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最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地域文化。”虽然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不同意见,但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即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保存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的诗性本体。
这或许就是“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为什么会在近代激烈的文化冲突中显示出其辉煌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有学者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很可能潜藏着一个“江南元叙事”的心理结构。所谓“江南元叙事”,就是以诗性审美品格为根本内涵的,最大限度地摆脱、超越了现实功利利害关系的审美活动,从而形成了文学艺术中特有的“江南意象”,特有的诗性审美品格。当然,这一观点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论证。不过,如果从中国文化的属性上来讲,其总体特征是乡土性质和农耕形态的,本身就蕴含着诗性的智慧。这种诗性的智慧,虽不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但在文化的碰撞、交汇与融合当中,它却“发展得最充分、最普遍”。
由于它的发展本身是在区域间的文化碰撞、交汇与融合当中进行的,这不仅为“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为它自身原有的特性、特质得以更进一步的强化,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条件。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在充分消化了外来的影响因素之后,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已成定局,同时,江南文化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与中心文化双峰并峙的局面。因此,到近代,在中国文化整体性地遭遇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冲击,出现空前的“意义危机”而不得不进入历史的转型时期,由于中心文化积重难返,边缘的地域文化则反而相对地获得了自身开放、求变的空间。这样,一方面是大环境所驱使,另一方面则由于“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固有特性的驱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原先一向以“柔美”、“精细”而着称的“两浙”区域的江南文化,反而能够对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动作出迅速的反应,并强有力地激活自身,一举走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成为引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最活跃的因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