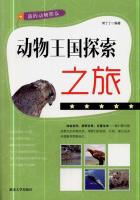这儿是哪儿?
晃动着还不怎么清醒的头,下意识的去摸手腕上的舍利,还好,舍利还在。温润的手感给了我一颗强效的定心丸,有这个在至少保命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转念又一想,舍利再厉害可还是比不过幕后黑手啊,别人一张袍子就能把自己给拐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要是再动动手指我不就死定了吗?
刚放下的心立马又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赶紧伸手把身体摸了个遍,直到确定自己没有受伤或者缺胳膊少腿的,这才扶着墙壁晃晃悠悠的站起身来。
头顶上的天空是圆的,小小的一方,夜风刚吹散了一朵厚重的乌云,皎洁的明月露出脸来,倾洒下银白的光辉,照亮了眼前狭小的空间。我一眼马上就明白了自己这是在哪儿,圆柱形的空间和石头堆砌的石壁,原来自己被扔到了井里。只是这井恐怕已经荒废了很久,脚下的淤泥已经干涸发硬坑坑洼洼的硌得脚底生疼,而石壁上面遍布着缺水而死的干苔藓,被手一碰便化作粉尘纷纷掉落。
我仰着头盘算着该怎么从这里出去,枯井地下的空间不大,仅容得下两个成年人肩并肩站立,所以自己看向井口的视角几乎是笔直的,这也导致了无法准确的判断这口井到底有多深。本想用手抠住井壁往上爬,但手一摸到井壁心就立马凉了半截,因为这井壁虽然是用石块堆砌而成,但挖井的人竟然用水泥将石块间的缝隙给填了起来,根本没有空隙能让人攀爬落脚。
扯着嗓子叫了几声救命,心想着就算把旗袍鬼引来也好,至少可以知道把我丢在这儿是个什么意思,总不会是想活活把我饿死,或者活埋?
“方雪翎,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头顶上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难怪别人说戏子无情biaozi无义,我二弟掏心掏肺的护着你,你竟然还想着别的男人,我娘说的对,你当真是只喂不熟的白眼狼!竟然敢跟外人合谋谋害我二弟的性命!”
欣喜若狂的心情转眼就跌倒了谷底,原本还以为自己可以得救,但那男人一番话下来,我突然意识到这事儿不太对劲。
“不,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一个娇俏如黄莺般清脆的女声紧跟着响起来,带着些许哭腔,直让闻者心碎。
可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粗暴的男声给打断了:“说什么!说你偷了府里的金银首饰准备跟一个低贱的戏子私奔吗!”
“我就说斩草该除根,可偏偏我那二弟是个软弱的主,竟留着你这祸害,白白糟蹋了我白家在这镇子上的百年清誉!“
“你不是还惦记着你那相好吗,当初看在二弟的面子上放了他一马,可现他不在了,我也就没必要跟你们客气,来人!把东西拿过来!”
我在井底,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一串凌乱的脚步声后,原本哭泣着没有说话的女声突然激动起来:“羽哥哥!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你……你……我跟你拼了!”
估计上面的人发生了撕扯,好一阵吵闹之后,男人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哈哈哈,戏子低贱命如草芥,奸夫死了,**也不能放过!李二,把这个贱人给我绑了拉倒祠堂去!今天我白岩以家主的身份执行家法,让这女人为她的放荡付出代价!把那东西给我扔废井里去,谁也不准动,这便是胆敢害我二弟性命和触犯我白家威严的代价!”
“不要!”
正疑惑着是什么东西能宝贵到让一个人发出那么撕心裂肺的呐喊,一个黑漆漆的东西就从井口掉了下来,直直的落进我的怀里。
条件反射的伸手一接,滑腻软糯的触感就在手心里蔓延开来,我低头一看,只觉得一股寒气忽的直冲头顶,身体猛地一抽惊恐的哇哇大叫起来。
尖叫着把手里的东西一抛,一条带血的舌头就脱手而出,掉落在井底扬起一阵飞尘。
可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那根断掉的舌头竟然自己在地上翻了个身,然后像虫子一样蠕动着迅速朝我爬来。
我吓得不轻,本能的想抓着井壁往上逃,可原本干涸的苔藓不知怎么的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湿润滑腻。手上抓不住,脚下的淤泥又软趴趴的不受力,于是整个人一滑,跌倒在了井底,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淤泥当中有浑浊的水浸出来,淹没了撑着井底的手腕,我想爬起来,可湿滑的苔藓成了最大的阻力,非但没能爬起来,反倒几次滚进越来越深的井水里,呛了好几口水。
水面已经到了胸口,借着水的浮力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可抬头一看依旧遥远的井口,恐惧和绝望抑制不住的涌现出来。
舌头轻飘飘的浮在水面上,顺着水波荡到井壁上又荡了回来,我恶心的不得了,正想用手把它拍下去,没想舌头却咻的一声自己沉进了水里。
完了,肯定又有古怪的事情要发生了,心里正想着,一种类似鸭子的叫声从水面下传出来。
心脏开始狂跳起来,不知道水底到底是多了什么东西,可自己又不敢去确认,只能小心翼翼的移动着脚步,退到井壁边上用背紧贴着石壁来减少心理压力。
随着“啵”的一声,漆黑的水面上冒起一个水泡,紧着着第二个第三个,一连串的水泡从看不见的井底往上冒,我吓得连尖叫都给忘了,只惊恐的盯着开始翻涌的井水发起抖来。
终于,一个漆黑的东西破水而出,缓慢却又平稳的不断上升,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一颗湿哒哒的人头正滴溜溜的转动着眼珠子,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脚软的几乎站不住,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民浩在河边遇见的人头,心中更是大骇,双手拼命地拍到水面想阻止人头向自己靠近。
但是,我忘了,要是物理作用能够阻止这些东西,那还需要道士法师做什么,直接一根棍子就能解决一切灵异事件。
因此,费尽了力气的挥打没起到任何的作用,反倒给了人头助力,借着水波的惯性直扑而来。
刹那间,心脏被几乎停止了跳动,只觉得呼吸一窒,眼前一片光影闪烁,本能的伸出手挡在面前。
可预想中的冲击并没有出现,反倒是背后一空,我猝不及防的摔了个四仰八叉。
“哎呀!”
我情不自禁的叫出了声,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没在井里了,因为背部传来的触感并不是井底的湿滑,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平坦。
我压住恐惧睁开眼睛,一根巨大又残破的横梁横在头顶上,而人头则不见了踪影。
站起身来观察着四周的环境,才发现自己在一个破旧古老蛛网交错的房间理,腐朽的雕花门窗,还有散落在地上的家居残骸都预示着这估计是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衣兜里是空的,手机恐怕是掉在了花田里,没了电筒,幸好有月光透过镂空的门窗照进来,照亮了大半个屋子和出去的路,而另一半的房间则隐蔽在黑暗当中,模糊不清。
我不打算去看,这种时候还要满足好奇心等于是找死,可脚刚一动,四周的门窗却疯狂的摆动起来,一关一合着啪啪作响,好像警告我不能离开。
衣服湿透了,我不知道身上湿嗒嗒的究竟是水还是汗,只能舔舔嘴唇壮着胆子往光亮的地方靠。
可桌案上的烛台忽然就燃烧起来,漆黑的地方也变得明亮,可此时我却更希望它还是黑的好,因为这亮起的并不是普通的烛火,而是绿幽幽的鬼火!
绿色的烛火忽明忽暗的摇晃着,照亮了黑暗,也照亮了我的恐惧,因为那颗人头,此刻却立在四四方方的桌案中间,一动不动直勾勾的看着我。
连番的惊吓已经让神经变得麻木起来,不知道是该叫还是该跑,
一人一头就这样僵持着,谁也没有动。
阴暗的角落里偶尔窜出两只老鼠,嚣张的从脚背上一跃而过。我见它半天没有动静,不像是单纯的为了吓唬我,这才抬手按着狂跳的心脏,壮着胆子问它:“你到底要干什么?”
可能是我终于明白了它的意思,人头高兴的张开嘴嘎嘎乱叫,晃晃悠悠的飞到我面前围着我绕了一圈,然后才飞那个烂的快要散架的梳妆台前,不住的撞击着镜面。
难道它是告诉我镜子里面有东西?
鼓起勇气走过去,人头见我跟来了,便飞快地退到一边。
我捡起一截烂木头问它:“你是想要我帮你?”人头闻言赶紧点头,可它没有身体,一点一点倒更像是在上下翻飞。
没理会这诡异又奇特的场景,我深吸了口气,卯足全力将木棍挥打在镜面上,把原本就破碎不堪的镜子敲了个粉碎,随即一本薄薄的小本子就跟着碎片掉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