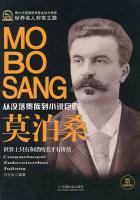萧红出院后不久,萧军就带着她离开了裴家。
他们找到一家由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在三楼顶棚下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了属于两个人自己的生活。
白俄经理来收房钱,一天2元,一个月60元。二萧手里只有裴馨园给他们的5元钱,雇马车来时用掉了5角,只剩下4块5。萧军递给白俄经理2元钱,经理要求他们明天把这个月的60元房租交齐,否则就必须搬走。
萧军说:“不走,不走——”
经理说:“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萧军急了,从床下取出剑来,指着经理道:“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
剑裹在纸里,经理以为是枪,慌张地跑出去报告警察所,说萧军带着凶器。
晚上,三四个警察闯入房间里来。萧军正赤着胸膛洗脸,两手还是湿的,就被警察架住了两臂。警察把箱子打开,翻弄了一阵,没有找到枪,最后把剑带走了,说:“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那你非吃亏不可,了不得的,说你是大刀会。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来取。”
警察走了,萧军和萧红的日子寂静下来。街灯的光漏进黑暗的房间,像是一股浸入时光的寒凉之味。他们就在草褥铺成的床上,拥吻着,相互搂抱着入睡了。明朝醒来,依然要为钱发愁,这个夜晚,他们只拥有彼此,也只有彼此才是最大的安慰。
铺盖要5角钱一天,他们租不起。于是茶房把软枕、床单、桌布都抽走了,原本洁白的屋子立刻变得斑驳芜杂。
夜饭要6角钱一份,他们吃不起。于是茶房手中端着的饭菜,连同饭菜的香气,立刻被送入了别人的房间。
萧军没有固定的收入,靠当家庭教师挣钱。萧红每天在旅馆里饿着肚子等他回来。每天只有饥饿和不尽的等待,只要听到有脚步声经过门口,她的神经就紧张起来。她盼着她的“三郎”回来,却也害怕他只是空着手回来。
房间的小窗那样高,就像关囚犯的屋子。这样日复一日的、无意义的日子,和之前被遗弃在东兴顺旅馆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萧红想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就像一架完全停止了运转的机器。
1932年11月初,萧军被中东铁路哈尔滨铁路局的一位王姓科长聘为家庭教师,教他的小儿子国文和武术,学费可用住房抵偿。
就这样,萧军和萧红终于有了第一个家,在道里区商市街25号院内,是雇主家的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半地下的小屋。
萧军借来了一张铁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又买回了水桶、菜刀、碗筷、水壶、被褥还有白米,一个小家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地经营起来。
萧军回忆道:
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够安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得的,也不想顾得的。我的任务,只是飞啊飞……寻找着可吃的食粮,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
而萧红也开始了小主妇的生涯,昔日的张家大小姐并不懂得烧饭——油菜烧焦了,白米饭是半生就吃的,说它是粥,比粥还硬一点,说它是饭,比饭还粘一点。
和在欧罗巴旅馆一样,依旧是萧军每天去工作,萧红每天在家里等他。她铺床、擦地、烧饭、刷碗,每天围着火炉台转走,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这是真正的过日子了,可是这样的为柴米油盐所消耗的日子却让萧红心有不甘。
还住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萧红写信给旧日学校里的美术老师,请求他的资助。
老师带着女儿来看萧红。小姑娘15岁,穿着红花旗袍和黑绒上衣,优雅地坐在藤椅上。萧红想起,上初中时的自己就和她一样美。
老师依旧和萧红谈艺术,他说:“你现在不喜欢画,你喜欢文学,就把全心献给文学。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只有艺术才是美,才是真美。”这些话,对于饱经风霜、饱受饥寒之苦的萧红来说仿佛那样遥远而空虚,但却让萧红的心触动了、潮湿了。曾经的她,也是那样爱美,也是那样倾心于艺术,也是那样有着天马行空的理想。而现在,仿佛一切都过去了。她并没有老,才只有22岁,却仿佛已经走完了几辈子,而今,早已“只有饥寒,没有青春”了。
看着眼前这个年少的女孩,萧红只有暗自叹息,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读书的时候只晓得青春最重要,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
搬来商市街的第一天,雇主家的三小姐来找萧红,说是萧红的初中同学。萧红并不认识这位王家小姐,王家小姐却说,张乃莹的名字她还记得很熟。她或许从未想过,当年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的“悄吟”,今天会落魄到这个地步。
“三姐!你老师来啦。”她的弟弟,也就是萧军辅导国文和武术的学生在外面叫她,她站起来,对萧红说:“我去学俄文。”她卷着发,涂着红唇,长身材,细腰肢,依旧是爽快的少女作风。萧红看着她,觉得自己怕是已经老了,或许残败得比30岁更老。
一天,萧红正在等萧军回家,在门口遇见王家的二小姐。一向生疏的二小姐突然问她:“没去看电影吗?这个片子不错,胡蝶主演。”
萧红说:“没去看。”
二小姐热心地继续说:“这个片很好,煞尾是结了婚,看这片子的人都猜想,假若演下去,那是怎么美满的……”她戴着蓝色的大耳环,永远吊荡地不能停止。
而此刻,萧红身上穿着单薄的袍子,已经冷得透骨了。
她忍不住在心里羡慕那些姑娘,那些还在上学,还能学着俄文的姑娘,那些戴耳环、看电影的姑娘。她也想抓住那些青春浪漫的情怀,然而生活却不由自主地滑向了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她才22岁,漫长的人生路,为什么定格得这样快呢?
在贫苦的日子里,萧红和萧军之间,除了“新婚”的甜蜜外,也有过一些隔阂与争执。
由于生存的重压,萧军必须整日忙碌地在外奔波,早晨起来要去南岗,吃过饭,又要给他的小徒弟上国文课,上完课,又要出去借钱。晚饭后,还要去教武术,教中学课本。辛苦的工作让他没有更多的心思去照顾萧红的感受,在萧红听来,连他对自己说话的语气都变得低沉严肃,完全没有声色。
白天,萧军不在家,萧红一人独守空房,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上,她多想和她的情郎好好说说话儿,然而萧军一躺到床上就一睡不醒。萧红觉得万分孤独,仿佛是空对着几件家具生活,虽生着嘴,却不言语,虽生着腿,却不走动,虽生着手,却什么也不做。甚至连视线都被墙壁阻隔着,连看一看窗前的麻雀也不能够,什么也不能够。这个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一贫如洗,只有寂寞和荒凉的地方,真的是“家”吗?
搬到商市街以后,萧红第一次上街是去当铺。她用一件新做的、还没穿过一次的棉袍,当了1元钱,于是从菜市、米店里买了许多东西回家,还买了10个包子。一路走着,她提着东西,手冻得很痛,腿也走得发软,好久不出门,太阳光刺得眼睛也痛了。
回到家,她把包子递给萧军。萧军兴奋起来,一个接着一个吃着包子,似乎完全没有想到此时坐在身边的萧红也饿着肚子,还走了那么远的路。萧红看着自己心爱的人狼吞虎咽地吃完了10个包子,竟然一个也没有给自己留下。
能让他吃一顿饱饭,她心里是欣慰的,然而这份欣慰中间,却也夹杂着一丝说不出的苦涩。
萧红的身体渐渐恢复后,也想出去工作,为萧军分担压力。她从报上看到一则招聘电影广告员(为电影院画广告)的启事,月薪有40元,这立刻让她动心了。
萧军陪她去商行接洽。第一次去,由于地址标注不明,他们找这家商行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找到了,商行的职员却说“今天星期日,不办公”。第二次去,又告知他们“请到电影院本家去接洽吧。我们这里不替他们接洽了。”
从商行出来,萧军就埋怨萧红道:“这都是你的主张,我说他们尽骗人,你不信!”
他们吵起来了。他觉得过错全在她,而她觉得他完全没有理由和她生气。回家的路上,他一直走在前面,仿佛不愿意和她一起走,仿佛因为她看问题没有眼光,让他很嫌恶。两个人一路吵着架回去。
后来萧红不再提这件事,萧军却因为南岗的学员不找他学武术了,自己主动到电影院去过两次。这两次又是无功而返,萧军发起脾气来:“我去过两次,第一回说经理不在,第二回说过几天再来吧。有什么劲,只为着40元钱,就去给他们耍宝!画的什么广告?什么情火啦,艳史啦,甜蜜啦,真是无耻和肉麻!”直到晚上睡觉时,他依然没忘掉这件事,又对萧红说:“你说我们不是自私的爬虫是什么?只怕自己饿死,去画广告,画得好一点,不怕肉麻,多招来一些看情史的,使人们羡慕富丽,使人们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就是这样只怕自己饿死,毒害多少人不管,人是自私的东西……”
萧红不喜欢萧军发火,然而此时,萧军终究是她崇拜的男人,她的眼里看不到萧军的虚荣、好面子,只觉得他对人性的剖析显得无比透彻。他的这番议论竟让她感动了。
又是一天,他们在街上散步时遇见了朋友老秦。老秦说,他在电影院画广告,问萧红和萧军愿不愿意帮忙。二萧都不答话。可想而知,萧红是不敢答应,萧军不是说过,这样的工作是毒害他人吗?她若是接受了这么“自私”的工作,萧军该会看不起她的。而萧军虽然嘴上也不答话,心里却是想去挣钱的。
老秦说:“5点钟我在卖票的地方等你们,你们一进门就能看到我。”吃过晚饭,萧军便催着萧红起身了。就连这顿饭吃得也分外急促,两人就站在炉边吃,饼还是半生的就吃下去。汤还在火炉板上蒸着气,汤锅还没盖起来,萧红连一口汤也没喝,萧军已经急切地跑出去了。萧红追着他,刚要出大门,突然想到火炉旁边还堆着一堆木柴,怕着火,于是又回去看了一趟,等再出来的时候,萧军已经跑到街口了,对萧红又是一番没好气地教训:“做饭也不晓得快做!摸索,你看晚了吧!女人就会摸索,女人就能耽误事!”
他们到了电影院,等了半个钟头也没有看到老秦,只好回家了。萧军的那套“自私”理论便又重新生发出来,他责备萧红道:“都是你愿意去……人这自私的东西,多碰几个钉子也对。”萧红任他愤怒地抱怨,她看明白了他,这前后矛盾的说辞和行为让她觉得可笑。原来贫穷不只是让人自私,也让人变得无理取闹啊。
当晚,萧军出去了,老秦找到家里来,萧红便跟着他去画广告了。10点,她画完了广告,回到家,见萧军正在房中生闷气——因为找不到她。
这一夜,他们又吵了起来。萧军去买酒,萧红心里觉得委屈,也把酒抢过来喝了一半。
她哭了,他也哭了。她醉了,他也醉了。她的心上像有开水滚,竟然为了钱和自己心爱的人闹到这步田地。他歪倒在地板上,嚷着说:“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
她看到他的样子,被滚水灼伤的心中又生出了无限爱怜,也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