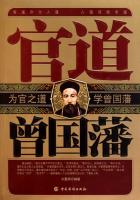一
大约在1879年的时候,我乘坐了一辆名为“勤奋”号的火车,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那列火车沿着诺曼底一条地势较高的铁轨行驶的场景。车窗外是一片辽阔的乡村景致:大片翠绿的田野,被树木围绕的农场,数座参差不齐的白色房屋组成了小小的村落。在我旁边坐着的是当时剑桥大学的教授威斯科特,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暑假。他穿着略显粗糙的黑色衣服,柔软的帽子压着有些灰白的头发,看上去很是抖擞,肩上披着的灰色方格披肩几乎从不见更换过,在他手里还握着一般的写生画纸。他安静地待在座位上,身体略弯,眉头紧锁,紧闭着双唇,明亮的双眼熠熠地盯着风景在窗外飞驰。他时不时会脱下帽子,仿佛在向什么东西致礼。我一直观察着他,最后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何总是脱帽。他似乎有些吃惊,然后露出疲惫的微笑,红着脸说:“我在向那些喜鹊致敬!”在乡村那一带的确能看到很多喜鹊。有时,三两只喜鹊就那样神态自若地稳稳站着,下一秒又陡然向附近杂木林的巢穴里飞去,将自己长长的尾巴愉悦地舒展在空中。威斯科特沉默了一下,接着又说:“这个愚蠢的习惯从我的孩子时期就已经养成了。只要看到喜鹊就会忍不住致敬,看!那里又有一只!”说完,他又将帽子取了下来。
我总是会回想起一些美好的过往。实际上,像威斯科特教授所说的天真“羞愧感”的情感,很多都可以归类成对某种迷信的敬意。威斯科特不能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也无法将这个习惯改掉。而我在看到喜鹊时总会吟诵一首古老的歌谣:一只喜鹊,孤单单,
两只喜鹊,喜洋洋,
三只喜鹊,必有一伤,
四只喜鹊,早生贵子,
五只喜鹊,其乐无穷。
有种神奇的喜乐感出现在最后一句中。不过,我更乐意看到两只或四只喜鹊待在一起,而不想看到它们“孤单单”或“必有一伤”。
令人费解的是,大部分人都会有几个专属于自己的“小迷信”。这些“迷信”出现的情景往往能唤起人们短暂的愉悦感。对于这种情感出现的原因,人们很难给出解释。我们究竟要把这种现象当成是灾难降临的预兆,还是我们对于无法避免的不幸所发出的警告呢?有些迷信是有解决办法的。如果将盐不小心撒到了地上,那么就要笔直地站着,用右手在高于左肩的地方,下与其相克的东西。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我都会这样做!也许,人们认为天使和魔鬼总是会出现的——右手是善良的天使,左手则是邪恶的魔鬼。邪恶的力量被撒在地上的盐瞬间激活,而越过左肩膀的右手则可以将邪恶从它的眼皮底下赶走。通常来说,大部分迷信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大多数人在打破一面镜子,或是看到初升的月光在玻璃杯上反射出来时,都只会“束手待毙”,颤抖的内心害怕着灾难会突然降临。另外,还有一些像“不能在梯子下面行走”这样迷信的心理,不过我在下意识里总是会去这样做。我认为,“以防万一”的心理状态才是这种迷信心理产生的根源。难道是害怕瓷砖掉下来砸到自己吗?能够肯定的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恐惧从远古的蛮荒时代就早已存在,那时的人类认为有一种无形的邪恶力量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随时惩罚犯下错误的人。而那些“错误”却显得如此琐碎与无害!更为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用“迷信”去惩罚那些故意犯下罪恶的人。然而,被恶意力量攻击的现象机会都是偶然发生的,并且报复的概率也叫人捉摸不定,完全随机。
不一定只有心灵脆弱或愚钝的人才会深陷迷信之中。很多精力旺盛或理智之人也有自己的迷信习惯。我有一位身体健康并且神志正常的亲戚,也同样痴迷于迷信。当时是一个冬夜,我的房间里点着三根蜡烛,而我则正在写作。他突然跑到我的房间案台前,小心地掐灭了一根蜡烛,面对我的不解,他解释说:“我不介意你点上四根蜡烛,可是三根不行,因为这是最不吉利的。”
更为奇怪的是,信奉迷信的人从来都不会进行深入研究。假如他们能将自己违反迷信原则时所产生的结果记录下来,那么他们就能确认或者将某个迷信理论抛弃。可是,他们从不这样做。我认识一位充满活力和智慧的女人,她一直认为就餐时人数为“13”就会非常吉利,我曾经对她说,“13”这个数字实际上只是一个百分比而已,假如“13”是吉利的,那么其他数字也可以一样吉利。她反驳我说:“哎呀!你们男人怎么都理智得让人讨厌呢!其他数字是不行的,我每次和教堂牧师聚餐时都会让人数刚好是‘13’位,结果没有发什么任何不好的事情。这是经过很多次证实的!”
历史上有两个关于迷信的最有趣例子,就是莫德大主教和约翰逊博士。莫德曾经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他的牙齿在梦里掉得只剩下了一颗,而他“将这颗牙齿用双手拼命地固定住”,他祈祷这个梦不会是什么灾难的预兆。这明显是一个将事情缘由与表现方式弄混的例子。就算这个梦境真的会引起某些灾难,他也无计可施。否则对于他来说,不过只是一个及时与善意的警告。不过,他诚心的祈祷又将他心智混沌时有趣的一面有所展现。莫德经常从圣诗与教义中寻找某些劝喻或是预告,尽管他精力充沛,为人刚愎自用,也不怎样体谅他人的情感,但是他紧张的神经和内心的焦虑,还是从这样的举止中显露了出来。而约翰逊博士则正常很多。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他睿智又幽默的思维背后,其实一直受着忧郁症的困扰。他在出门时总是先小心翼翼地将右脚迈出,在接触到支柱后开始念叨着祷词,又或者毫无预兆地大叫一声。这样“迷信”的行为实在叫人难以忘怀。而在古老的迷信故事中,最有趣的则莫过于西塞罗讲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但对这种习惯心态的本质进行了说明,还体现了拉丁字母发音的奇妙,让人很是好奇。西塞罗曾经在布鲁迪辛乌姆准备乘船前往希腊,一个商人到码头叫卖着东西,嘴里一直喊着“柯尼安无花果”。(“Cauneas!Cauneas!”)于是西塞罗立马改变了自己的行程,没有马上启程。其实“Cauneas”是很标准的拉丁发音,听起来与“Caveneeas”(不若归去)有些相似。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西塞罗却没有对同行的人进行告诫,叫他们不要登船,他只是认为自己足够幸运,能够参透这个预兆。没错,在这种事情上,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样做。所谓的天意在人们眼中,并不仅仅只是负责分配好运与歹势,使人无法避免灾难,它总是会以某种渺小却奇妙的方式向很小一部分人告知命运的前兆。整个事件因为这种心态而变得有些堕落的味道,因为这种暗示背后隐藏着的是变化无常的恶意精神,它就像是天卫十七星上那个野蛮而残忍的奴隶卡里本,总是将快乐建立在他人的失望或愤怒智商,因此总是会开一些令人难堪或尴尬的玩笑。
“勿爱,勿恨,选择就行。”
我总认为,迷信会在教育的逐步普及以后消失殆尽。可是,在某些偏远的地方或是小山村的角落里,它们仍旧顽强地生存着。在多塞特郡塞恩·阿巴斯白垩的草皮地上,雕刻着一幅长达200英尺的男性人物巨像,这位巨人手里拿着破旧的球棒,浑身赤裸,人们称他“塞恩的男人”。没人知道雕像的具体完成时间,不过能肯定的是在英国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从恺撒的生平记录中得知,有些俘虏是被柳条绑住,活活烧死在恐怖的仪式当中的。僧侣们宣称雕像手中的棍棒代表着鱼类,说明他曾经远洋,于是试图将其改名为圣·奥古斯丁,从而让庄严宗教意味融入其中。这幅雕像的寓意在这片盛产海鲂里,让人很是难以琢磨。唯一能够肯定的是,许多丑陋与邪恶的迷信都是因它而起。在这里举行过的某些野蛮残忍的宗教仪式直到近代才彻底绝迹。我想那些存在于偏远地区的各种黑暗古老的仪式,现在都应该消失了吧。曾经流传着一个坊间传闻,说是就在前几年,在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插满别针的蜡像。这些阴沉黑暗的传统究竟要到何时才会被彻底摒弃呢?毕竟,这些世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信念太过根深蒂固,想要连根拔起,是任何理智的争辩都无法做到的。
不过,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又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在面对这种迷信的行为与思想时,他们往往都抱着一种真诚的心态,他们依稀认识到,或许真的有一些内涵藏在这些思想行为背后,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认为,对于那些心理承受能力太弱的人来说,如果灾难真的在预兆之后降临,那将会是最坏的消息。相比起一百件没有灵验的征兆,这些饱受教育之人宁愿相信那一件征兆的灵验。人们只要转变思想,就能心知肚明地从迷信虚荣的魔爪当中脱离出来。
脚踏实地才能攀得上高山,长年累月的积累才会有更高的智慧,没有什么是能一蹴而就的。许多清楚真相后的明智之人,在善意告知他人真相后遭到冷遇或排斥,便会失去耐心,变得暴躁。想在这场直觉与理智的漫长战斗中获得胜利,就得长久地坚持下去。就像那些曾代表专制反动庞大势力的建筑,如今也坍塌成一片充满意境的废墟。一到夏季,这些废墟就会迎来许多游客。最终,这些古老的力量只是演变成了一些美好又有趣的习俗。可是,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毫无负面意义的习俗却总是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神秘与可怕的事情让人疑惑,不过,人们对于这些臆想带来的恐惧总是放任不管,任其增添自己的负担、折磨自己的思想,再试图从一些古怪或荒诞的仪式中得到解脱,这些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
二
对于梦,只有两点让我感到费解:第一点是,梦境的绝大部分是视觉的印象;第二点则是,虽然梦的制造者是我们自己,同时来用奇妙的情感和令人意想不到的鲜活场景冲击我们的达到。那么,我们可以在下文慢慢剖析这两点。
现在,一些研究思维规律的哲学家领导发起了意象重点在于对梦境进行解释的运动。到底我们大脑中的哪一部分在起着奇妙、强烈并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会不加理睬普通动机和管理?一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事物一样,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因此我们似乎忘记了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感到任何惊讶。对于梦,我们却感到非常费解。梦是我们所发明出来的现象,我们自己发明并创造出来,却试图用奇妙的情感和场面让我们大脑受到冲击。
如果在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对于梦中的情景还带有深刻的记忆,对于梦中的某些场景往往也会带有印象,可这种印象主要通过眼睛来接收。不同的人创造出不同的梦境,就像我自己做的梦,往往可以相当清晰地分成几种分类。其中,我们最经常做的梦则是我在一片安静当中观赏一片难以言喻的美景,例如在梦中,我看到了一条如同蓝宝石一般湛蓝的河流,它正沿着一块巨大的砂岩峭壁顺势浩浩荡荡地直流而下;又或者我会梦见身处一片繁花盛开的小山之间的树丛中;又或者我看到有着宏伟建筑群的林地,还有建筑上石雕的门和高耸的塔。这些神奇的梦境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开心以及刺激。如果从这样的梦境当中醒来,我们总是能对美和契机产生不同的领悟。又或者我会梦到透过窗户或阳台看到某种程序令人感到奇怪的隆重仪式,很多人衣着华服或者步行,或者骑马、乘车列队前进。又或者我梦到在某个昏暗、四周被柱子支撑的屋子里,很多人正在举行宗教仪式。一切悄然无声的梦境在一片宁静中上演着。我不知道自己的所在,也不清楚自己的经历,却又试图想要知道些什么。可是,我听不到别人大声说话,或者身边人做任何的交流。
另外,我还会做一种关于愉快生动谈话的梦。我在梦里正在与罗马主教、俄国沙皇等一些大人物推心置腹地进行交谈,他们正在引经据典地向我请教,可我却惊奇地发现它们是如此和蔼可亲,毫无一点架子。或者我会梦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和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在一起聚会,一个又一个的客人在我面前走过,向我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奇闻逸事的真相与细节。常常我还会做这样的梦,梦见一些早已过世的人,如我的父亲。在梦里,我们父子偶然间在一个火车站里相遇,并且我们都暗自庆幸这次愉快的相逢,父亲抓着我的胳膊,微笑并温和地向我述说着什么。可是,当我对于父亲最近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很久不见面感到疑惑的时候,就会立马从梦中醒来,这才意识到父亲早已离开人世多时。梦境也就成了我与父亲相见的唯一途径。我偶尔还会梦到自己在听音乐。我依旧清楚地记得自己听到了四位音乐家用银笛等四种小乐器演奏四重奏,曲调优美。可是,最让我感到兴奋异常的还是在梦里可以浏览各种美景,以及和亲密的人进行交谈。
在我的孩提时代,经常反复做同一个梦。当时我家在林肯郡一所叫钱斯里的旧宅里。那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有着某种意思的中世纪建筑特征的建筑,在那里可以看到螺旋式石头楼梯,镶嵌在墙上的都铎式木制屏风,这些都是过去这所小教堂留下来的摆设。另外,还有一些相当神秘的空间,与一些房间大小非常不衬的通道。在这种格局当中,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刺激,或许那也正是我梦的源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