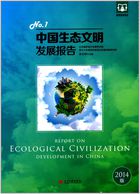车子停在会展中心门口,这里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营叶来的次数有限,只有农博会盛行时才会被爸妈拽着来游玩。
“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徐健轻笑:“宝贝,你是本地人吗?茶展览会没听过?”
“我说实话,你别生气,我对茶的认知真的少的可怜,最常喝的是瓶装的康师傅冰红茶,所以……”
她倒诚实,所有接近自己的女孩都会以茶作为幌子,说出来的话一听就是谷歌出来的,还要装的很懂行一般。
徐健抬起她的马尾:“那你叫我一声师傅,我就教你品茶怎么样?”
“叫你师傅没问题,只要你别满嘴叫我宝贝。”营叶真的不明白男人为什么都爱这么叫女人,随口叫来,是不是在街上喊一声,一堆人要回头。
在这等着自己,徐健的胳膊伸出,这次营叶明白他的动作,上次周总给的教训还记忆犹新,他带自己出来办事,作为她的助理当然要给Boss面子。
展会还没有开始,商家已经紧锣密鼓的张罗着布置自家的展台。
“对了,我上次给伯父带去的茶他似乎很喜欢,你天天在家都没被熏陶吗?怎么连品茶都没练出来。”徐健可记得营父笑弯了眼。
营叶的右手抓着他的T恤:“徐总,你干的好事,今晚我爸妈让我过去跟他们解释清楚,你最好把你说得话统统给我重复一遍。”
瞧她生气的脸,真是有意思,她的指甲真干净,应该只涂了一层亮油,自然地色泽让人看着很舒服。
“你紧张什么,不怕,有我呢。”徐健感觉得到她的抗拒,也对,才认识不久,可让人抓狂的是,本少爷觉得跟她是旧识,上辈子有渊源吗?
讨厌他无所谓的态度,倒不是他父母了,说糊弄就糊弄,感觉到她不开心,徐健主动承认:“我只是说你是我的,是我女朋友,你在跟我闹别扭,你跟你的前男友早就分了。”
“你?我什么时候是你女朋友了,你这人怎么说话不打草稿呢。”
一吻印在她的额头:“我盖章了,你就是我的。”低哑地嗓音在她耳边,很轻却决绝。
雷鸣般地掌声让营叶清醒,后退一步,羞红了脸,垂下眸不看他。
“徐少,展台布置完了,请您视察。”冰冷地女声打破掌声,用眼神警告周围沉浸在老板大胆地举动中的员工。
男人抬头看了看牌子,不禁摇头:“牌子换掉,我从B区进来雷同的牌子不下十五家,如果你是顾客,不会视觉疲劳吗?”
“还有地毯,太艳了,清新雅致的格调被你们当下酒菜了吗?”
觉得脸蛋不发热的营叶缓缓抬头,他的话让大家哑口无言,只是连连点头,感觉到有人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一抬头,营叶一愣,是她。那晚麻将桌上坐在他旁边的浙江女人,她的目光太过肆无忌惮,明显就是敌意。
“梅子,你耳聋了吗?是你负责我本该放心,这就是你给我的展台?”徐健眉毛轻佻,质问着。
杨梅扬起头:“对不起,是我心不在焉,给我一天时间,一定会焕然一新。”
“一天?半天。”徐健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别让我怀疑你的专业能力。
凡是投入工作的男女身上都有一层光环,此刻的徐健让营叶刮目相看,他的不正经隐藏了,一切都以他的专业眼光行事,每一个视察的动作看起来都那么优雅,若是初见,定会认为他就是如此。
那晚坐在麻将桌前他与梅子轻笑低语都是那么契合自然,而今他却能做到眼里没有一丝情意,或许这就是男人的理智,抑或无情。
“梅子,为营小姐沏茶,拿出你的茶艺让她欣赏一下。”
杨梅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营叶赶忙说:“不必了,我不懂茶,给我喝好的也是浪费,赶快忙去吧,不用招呼我。”
“是她不喝的,我还是赶紧准备展板好了,营小姐,你是客人,招待你是应该的,小李,交给你了。”杨梅加重客人二字,嘴角上扬。
徐健搂住女人的肩膀:“那好,你们忙,我们去约会。”
这次营叶可以确定,他就是故意的,太可恶了,难道看不出那个女人对他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吗?
走出展馆,营叶就从他臂弯中挣脱,费解地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跟她本就该是上下级的关系,是她越级了,认为我带她出去就是男女关系。”
不然呢?营叶才不信他们如此单纯:“如你所言的话,她何苦一副你要了她贞洁的样子?”
徐健大笑,奇怪,这会儿她怎么不脸红了,说的这么露骨:“我可没有,是她想多了,她想要我,我可没同意,为你守身如玉呢。”
不愧是周总的朋友,真是物以类聚,都是厚脸皮。
见她不理人,徐健牵起她的手:“吃饭去吧,小懒猪,起那么晚这个时间该饿了吧?”
哎,早上就不该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明很勤劳的,只是偶尔不再状态,开了小差,被他逮到嘛。
车内,轻音乐让人放松。
“叶子,你跟前男友分多久了?”徐健不想耽误任何一秒了解她的机会,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今日她还睡那么久,白天在一起的时间那么有限,真是不够用啊。
瞥了男人一眼:“问这个干嘛?”
“好奇,我谢谢他把你甩了,这样我才有机会。”徐健从他父母口中听出他们对那个男人不是很满意。
可恶,坏人,不知道这么问很不礼貌吗?营叶忍不住回嘴:“谁说他把我甩了,是和平分手好不好。”
只是提到,就热泪盈眶,徐健将卫生纸递给她:“不许流下来,以后只能为我流眼泪。”
仰起头,营叶嘴硬:“谁哭了,睫毛掉了进去。”说完,还把镜子放下,假意寻找未掉的睫毛。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营叶却忍不住合上镜子,扭头看向窗外。
将车靠边停下,徐健抽了几张纸,因着急胡乱地替她擦着:“该死的,是我不好,以后都不问了,乖,不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