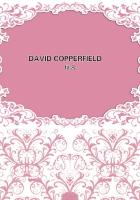赵墨早就摩拳擦掌,一听之下,正待起身,紫微却伸手拦住,微微一笑,道:“恐怕要让世侄失望了。克非昨日修道岔了真气,正在调息之中,多有不便。这样罢。不如让其他弟子和世侄互相印证道法。”赵墨一呆,只得乖乖坐下,齐承祯一脸失望,望向东方靥。东方靥暗骂两声,转头望向赵墨,道:“世侄这真气岔得可真巧啊。我们都知道缘故,这也罢了,日后传出去,外间的人不知道,恐怕还要说是世侄是害怕呢。”慕容轩一旁干笑一声,道:“就是。”
冰砚顿时大怒,拍案而起,飘然而出,道:“既然想要向我哥哥挑战,那就先赢了我再说。”齐承祯乍见人群之中,飘出一人间绝色来,看得几乎魂灵出窍,正呆呆不知所措,听得东方靥喝道:“承祯!”承祯立时惊醒,望了望冰砚,稽首道:“请教师叔尊号。”冰砚瞪了他一眼,道:“不必了。出手罢。”承祯笑道:“师叔是长辈,弟子理当礼让。”冰砚哼了一声,冷冷道:“那你就自求多福罢。”
说着也不出剑,只是一跺脚,天上顿时生出一层厚厚的乌云来,那乌云渐渐变厚,慢慢吹下一阵阵冷风,冷风之中,慢慢带出雪花来,不到片刻,八卦台中心之处便累了一层厚厚的积雪,空中也飘着片片雪花,如琼花,如玉屑,天地之中,顿时生出一股淡淡的凄凉之意。却听冰砚缓缓念道:“不是宦游,胜似宦游;恰倒是孤馆经秋,羁旅眠愁。”念动之时,已经轻挥襟袖,握剑在手,飘然而舞,其舞身姿飘摇,飘摇之间,别有一种闲愁,叫人莫名惆怅,承祯长刀在手,捏好法诀,这刀却辟不出去。只呆呆的望向冰砚,满心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
却听冰砚长叹一声,又念道:“井梧叶凋,窗竹影透,怎禁得絮绪暗生,绵思别有;思量时,时时更深,怨句哀吟,吟不到清昼。”冰砚舞动之际,承祯瞧得痴了,手脚只管随了冰砚的舞姿,搔首弄姿,邯郸学步;东方靥瞧得大怒,聚齐真气,喝道:“承祯,出刀!”他这一声,有如炸雷,惊得承祯一呆,却未清醒,只是下意识的飞刀出鞘,喝道:“玉清,凤舞!”那刀一飞出,却莫名其妙“铛”一声响,飞入雪中,却是被冰砚暗地里飞出承影击飞;冰砚悄然融在雪光之中,欺近身来,承祯只见他浮在风雪之间,弱如飘絮,柔若落红,再寻不回一丝的敌意,只呆呆的瞧他,却见他媚眼如丝,秀发飘拂,神色哀婉,似有万种孱愁,不可名说,只这眸子之间,便叫人神魂颠倒,冰砚在他身边缓缓念道:“辗转处,处处残漏,起徘徊;但见宫墙柳,斜扶敧依,学人凝眸;似问痴人,底是为谁淹留?”
他字字嘶哑,字字如敲在承祯心头,承祯猛然荡起一股自哀自怜之意,修道清冷,数十年弹指即过,寿延虽长,却觉天地更远,岁月更无情,人世无可恋之人,天地无可爱之物,茕茕孓立,形影相吊,长伴身侧的,不过一团蒲团,一盏青灯,待冰砚那句“似问痴人,底是为谁淹留?”响起,不禁流下泪来,泪水才落,猛然惊觉脖子一凉,一柄光华夺目的长剑架在脖子之上,冰砚歪斜了个头,道:“你服输了吗?”承祯一呆,回过神来,满脸愧色,垂头道:“师叔道法绝世,弟子心服口服。”说罢转身回座。东方靥气得脸色赤红,半晌不能言语。洞玄一旁冷笑道:“老三把他的这点压箱底的**都传给他了吗?哼,万象功,我看叫摄魂术还差不多。”
冰砚挥挥手,台上烟霭散去,那乌云,那雪,立时无踪,不过是他施法幻出的幻象罢了。冰砚微微一笑,道:“还有谁不服,要挑战我哥哥的吗?”却听慕容轩喝道:“兰亭,你出来。”昆仑弟子立时走出一人,稽首对冰砚道:“昆仑三代弟子燕兰亭,请师叔赐教。”冰砚看他双目瞳孔灰白,甚是奇特,心中甚奇,忖道:“这人莫非是个瞎子?”却听紫微道:“这是淇水燕帝后裔吗?”东方靥道:“是。燕帝世家,代代都是洞灵眼。这是假不来的。”少君忍不住问道:“什么是洞灵眼?”紫微道:“洞灵,顾名思义,就是洞察灵机;燕家的人,世代遗传,他们的眼睛,能够看穿幻象,幻术对他们起不了作用。”
冰砚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兰亭行礼,道:“师叔,请。”冰砚道:“好,我就会会你这洞灵眼!”说着背上飞出纯钧,纯钧纤巧秀美,气象尊贵,浮在冰砚掌上,更是动人。冰砚一声轻叱,纯钧飘然飞出,击向兰亭,兰亭掌中旋风起处,已经飞出一刀,这刀刀身镌刻日月星辰、山川河岳,刀背文饰精灵古怪、魑魅魍魉,光华灿烂,不可逼视,是一把极其贵气的宝刀,连洞玄看了,都忍不住赞道:“好刀。真是好刀。”慕容轩昂然道:“武帝刘裕,永初元年所铸,名曰定国,是镇国之宝。自然是好刀。”
兰亭的定国宝刀已经迎纯钧而上,两人均未施法,纯以神兵对砍,刀剑交鸣,“铮铮”之声不绝于耳,赵墨忍不住在对少君道:“刀重剑轻,神兵对战,咱们不施法,岂不是吃亏了?”少君微微一笑,道:“胡说。谁说他们没有施法,你看那个白眼睛的左手。”赵墨凝神看去,却见兰亭左手单手成印,印成之后,指掌之上便腾起一道红光,只是那红光一闪即灭,瞧不出所以然。赵墨诧道:“他这是在做什么?”少君“咦”了一声,道:“你看不见吗?”赵墨摇摇头,少君飞出平波,道:“看里面。”
赵墨朝镜中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却见兰亭手中腾起那红光,那红光一闪之后,便化成一股黑气,黑气之中,聚一只黑气萦绕的山魈,山魈人形而似鬼魅;披头散发,鼻上穿有骨环,耳上挂有骨刺,颈项之上环有骷髅,浑身黑毛,手中握有一根狼牙棒,形容狰狞,面目可憎,鼻翼之中呼呼直喘,喷出黑气,挥舞着狼牙棒扑向冰砚。
山魈乃是白日隐身之鬼,只有月光下才能显形,冰砚本瞧不见它,只是山魈呼吸之间,喘息甚重,天狐灵胎,耳目聪慧,冰砚瞧不见,却能听见这妖怪的声音,暗中唤出承影,承影何等神器,冰砚也单手结印,暗中使出术法,承影将那山魈一剑削灭。兰亭瞧得见山魈,却瞧不见承影,只见自己召唤的山魈刚刚出来,飞到冰砚身侧,才一近身,便烟消云散,重回冥间,只得一次一次重新召唤,浑不解其中奥妙。
冰砚也十分毛躁,不知道这白眼睛在捣什么鬼。刀剑剁砍多次,兰亭心中发急,眉头一皱,结个法印,念道:“玄元,坎水之术!”地面顿时“噗”一声开裂,裂口处泉水奔涌,那泉水却不流淌,只卷起巨浪,扑向冰砚,冰砚一拂袖,身形腾空,那泉水却奔涌腾空,卷了过来;冰砚笑道:“自找苦吃!”说着双手结印,叱道:“万象,胡灵镇移**!”那泉水立时顿住,瞬时凝固化冰,再陡然飞起,仿如一座冰山,拔地而起,再向兰亭迎头压下,兰亭吃了一惊,急飞后退,冰山压下,“砰”一声响,爆成一滩水渍,慢慢的浸润地面,消逝而去。
冰砚笑道:“叫你看看真正的御水之术。”说着身形在空中一转,双手结印,朝兰亭一点,喝道:“万象,禺强秘法,翻江倒海!”八卦台上的玉石地板猛然破裂,地底腾起翻天的巨浪,四面八方,将兰亭团团围住,迎头卷来,兰亭大惊,身子一蜷,速结法印,掌心飞起一符,符光一闪,符火腾起;那巨浪虽将兰亭卷起,水却压不进那符光之内,冰砚嘿嘿一笑,承影暗自飞出,暗结法印,暗自念道:“七变,神针!”承影便化成一根细针,“嗤”一声刺在飞符之上,符光立熄,兰亭“呀”一声叫,已经给卷在浪中,给浪头抛来抛去,立身不住。东方靥面色铁青,喝道:“百辟!”
兰亭给他一喝,头脑清醒,捏指成诀,喝道:“玉清,百辟!”定国瞬时飞出,“唰唰”数刀,竟然将滔天的巨浪切开,浪头一断,兰亭御刀飞起,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丸,吞服下肚,立时双眼放出幽幽阴冷白光,那白光在波涛映照之下,显得微蓝。冰砚一怔,却见兰亭茫然喝道:“洞灵,鬼视之术!”那一双眼中的白光顿时旋转起来,白光照处,那巨浪瞬时凝结,再瞬时破裂,散作一地。兰亭御刀飞来,那双眼之中的白光,便照向冰砚,冰砚给他眼睛一照,顿时只觉手脚发硬,肌肤似乎凝固,内里血脉却又沸腾欲炸,一步都挪动不了。
东方靥一旁忍不住叫道:“兰亭,你在作什么!比试道法,怎么能用这么危险的法术!”兰亭凝视冰砚,却不发一言。冰砚给他一双鬼眼看得无法动弹,心中恼怒,兰亭缓缓道:“你认输罢,再撑下去,我控制不了了,恐怕你会受伤的。”冰砚“呸”道:“胡说八道!”手脚僵硬,无法结印,只得喝道:“纯钧!”再暗唤承影,纯钧承影飞出,飞到兰亭身前,却给那鬼眼罩住,一样无法动弹。兰亭求胜心切,一挥手,定国瞬时升起,疾快砍来,冰砚无奈,猛然张口,口中飞出一物,这物什光芒发黄,“铛”一声响,将定国辟飞,兰亭一怔,这黄光继续飞来,辟向兰亭,兰亭凝视双目,紧盯这黄光,不料他的鬼视却定不住这道黄光,黄光将他的鬼眼的法力结界一下剖开,当胸撞来,兰亭全力施展鬼视,无暇闪躲,给撞个正着,立时倒飞,冰砚瞬时收回黄光。
兰亭给一撞,倒飞数丈,“砰”然倒地,胸口衣衫却给击成碎片,一片片散落在地,上身**,只见胸口留有浅浅一道划痕,若不是冰砚收得快,只怕人会被辟成两半。东方靥忍不住站了起来,道:“什么法宝?”冰砚扮个鬼脸,道:“不告诉你。怎么样,认输了罢?”兰亭心有余悸,稽首道:“师叔道法精妙,弟子佩服。”冰砚微微一笑,转头望了望赵墨,赵墨朝他吐了吐舌头,冰砚大是得意,朝昆仑众人道:“还有谁想要来的吗?”
却见昆仑众人之中,飘然而出一少年子弟,眉目轩昂,气质卓绝,举手有玉树之风,移度有章台之秀,令人喝彩,只见这少年稽首道:“昆仑三代弟子楚广陵,自不量力,想要请师叔指教。”却见紫微转头对东方靥道:“听闻贵派世家有五,前所见为燕帝后裔,这位世侄气宇不凡,莫非是汉水寿春世家之后裔?”东方靥道:“掌教真人所言不差。”紫微点点头,道:“名门之后,果然不同凡响。”洞玄道:“汉水寿春楚家?就是高阳帝的后裔那个楚家吗?”东方靥点头道:“正是。”洞玄哼了一声,道:“天生就是六只手的那个家族罢!多几只手而已,也不见得就有多利害。”
赵墨擦了擦眼睛,道:“六只手?在哪里?我怎么只看见两只手?少君,把你的镜子借来照一下。”少君给了他一拳头,道:“鬼扯,我这又不是照妖镜。”紫微朝俩人一瞪眼,正色道:“寿春楚家,世代居住汉水,是帝王后裔,他们家族血脉相传,族人都是莲胎骨。与常人不同。”赵墨皱眉道:“莲胎骨是什么意思?”紫微道:“莲胎骨,就是骨如莲花,他们的骨头每一根都是由很多小骨头拼凑而成的,也叫做碎叠骨,可以变化,只要施展真力道法,通常他们都可以化出三头六臂的神通来。”赵墨不由得道:“那冰砚能打得过吗?双拳难敌四手,何况还是六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