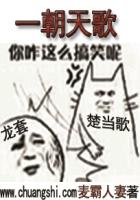拱卫司的衙门有两个,一个在皇宫内院,那是指挥使处理事物的地方,还有一个……自然就是比大理寺天牢还要令人闻风丧胆的拱卫司的刑讯部,在城郊外的一处高墙内。
对于这个地方,众人议论纷纷,不过都是什么那边的墙都是用死人的骸骨堆积起来的,又或者说里面怨气熏天,常年闹鬼,环绕那宅子的溪水上游的时候还是清澈见底,下游的时候却是猩红的血色,至于拱卫司的天牢,那就是有去无回,还没有人能活着……噢,不对,应该是四肢健全的出来,进去时候是个大活人,兴许回来的就是一个人彘。
伍泉从家里骑着马跑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初秋的雨说下就下了,他淋了一身,衣服贴在身上,浑身湿冷的很,却面无表情,似乎这些不过是身外之物,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黑色的骏马在主人的驱使下,犹如闪电一般来到了一处宅子前。
高高的墙壁足有九尺来高,门外有兵士把守,虽然下着雨,却是身姿笔直,大檐帽下的面容很是肃穆严苛。
“什么人?”
“我是伍泉。”伍泉机械性的把腰牌拿了出来。
片刻之后,伍泉就被小兵士带到了一处厅堂内,一整套红漆描金的檀香木家具,太师椅,八仙桌,正中的墙上挂着前朝吴道子的真迹,靠墙角的长几上则摆着两盆宋梅兰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家的主宅,这般奢华的不动声色,其实不过是拱卫司待人的厅堂而已。
屋内点着火盆,驱散了外面的潮气,显得很是温暖,这让伍泉终于感觉到湿淋淋的衣服贴在身上很是难受,可是他却浑不在意,甚至有种自虐的快/感,齐瑾萱死了,他却独活着,这种说不来的愧疚感,失去的爱人的茫然,撕心裂肺的让他痛苦不堪。
也只有这么自虐的时候,他才会觉得稍微对得起齐瑾萱。
邓启全很快就就走过来,他穿着一身红底洒金的拱卫司官袍,走路生风,很是急促,显然有些忙碌,腰上的佩剑上的宝石在屋内微弱的灯光下,闪耀出异样的光彩来。
“你怎么过来了?”邓启全和伍泉是兄弟,小时候恨不得穿一条裤子,长大后更是亲如兄弟一般,所以邓启全在伍泉面前毫无遮掩……这会让他正皱着眉头看着一脸失魂落魄的伍泉,心底的不满越发浓重。
“你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伍泉深深的吐了一口气,背靠在红色柱子上,眼中带出说不来的痛苦压抑。
邓启全终于按耐不住怒意,他朝着半空中狠狠的挥了挥手拳头,恨铁不成钢的说道,“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太后谋反,朝中一片混乱,正是用人之际,你却称病请假,浑浑噩噩的在家里喝了一个月的酒,整日的醉生梦死!可是陛下怪罪过你吗?那侍卫司的指挥使的位置还好好的给你留着!你这样对得起谁?”
伍泉眼中上过痛苦之色,他揪着头发蹲在地上,像是一个茫然无措的孩子一样,说道,“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是我这里空了,你知道吗?”伍泉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活着却像是行尸走肉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