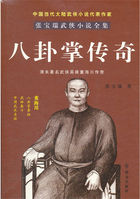我打车回到梦境圆,精神有点好转,甚至想到应该搂着那个叫文静的女孩子好好做上一夜爱。我走过大厅散座的时候,翘鼻头迎上来问道:“先生回来啦,吃过晚饭没有?”我说:“送到房间吧,一个小时以后再送来。”翘鼻头笑了笑说:“好的。”她抢上前去帮我摁电梯。等电梯的时候,我悠闲地扫视了一圈散座上的那些男侍应。我突然发现其中一个有点面熟,额头上还有个青紫色的拳头印。我赶紧扭过头去,但他早就看到了我,这时候已经向我蹿过来,并试图揪住我的衣领。我赶紧把拳头挥过去,两个人在别人的目瞪口呆中扭打起来。我挨了几下,觉得很受用,不禁勇气倍增,一拳更比一拳狠,一直把他打到楼梯口。其他人这才拥上来分开我们,小帅哥骂骂咧咧不肯干休,我则揉着脖子走上了楼梯。
爬到二十层时我已经像长跑一样喘气,我决定休息一会儿。我趴在楼梯扶手的拐角处,把头探出去朝下望。我估计小帅哥不敢追上来,他应该清楚他不是我的对手,但是我不敢肯定他会不会报警,但愿他为俱乐部的收入考虑,咽下这口气去。
我推开楼梯旁的安全门,看到是一个同样古色古香的休息室,与整座大楼不同的是,这里灯火辉煌。我走进去,仔细欣赏这里的每一件装饰,竟然有一幅“贵妃出浴图”,不知道挂在这里是什么用意。我入神地欣赏这幅隐隐约约的粉红色调的画,突然听到一声女人的轻咳。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安全门呀地响了一下,被推开一半,我看见一只女人的手反掌推着门把手。那里有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缓缓地问:“今天来的那位客人谁陪着?”
一个少女的声音答道:“文静,她在客人房间里待了整整一天了。”
原来那个女孩真的叫文静。
“客人一直没出去?”
“天快黑的时候出去了,他不让文静离开房间。真是个怪人。”
“不要随便议论客人,要尽量让他们满意。”
“嗯,我会告诉文静的。”
一直扭着头偷听别人谈话很别扭,我转身坐到那幅画下的沙发上。我看到那半扇门慢慢地开了,走进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来。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礼貌地问道:“您在这里休息吧?”我赶紧点点头。
老妇人坐到我对面,自我介绍说:“我是这里的老板,看上去您像个文化人。来了多长时间了?”
我欠欠身,客气地回答:“今天刚到,您这里环境很好,很别致。”
老妇人说:“谢谢,您满意我很高兴。”然后她思考了一下,小心地问我:“您对文静还满意吧?她有没有让您生气?”
我说那姑娘挺好,安安静静的。老妇人放心地笑了,随即又叹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您提出来要个文静的,要不然不会让文静去陪您。”
我有点奇怪,问她:“文静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吗?”老妇人赶紧说:“不是不是,文静是最好的,她很听客人的话。只是……”
“只是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怕。老妇人又叹口气说:“她曾经爱上过我们这里的一位客人,人家走后,她割腕自杀,好在发现得早……这是她出院后第一次陪客人,我担心她调整不过来。所以……”
我吃了一惊,但嘴上说:“没事没事,她挺正常。”
老妇人笑着说:“那就好,不过您最好不要问起她这事情。如果觉得不满意,我们再给您换人。”我说:“满意满意,不用换了。”
老妇人又笑了,显得很善良,像隔壁大娘。然后她站起来告辞了,剩我一个人在“贵妃出浴图”下不知该干什么好。我想刚才忘了问一下老妇人为什么把“贵妃出浴图”挂在这里,而客人的房间却挂着一副《蒙娜丽莎的微笑》。
我推开房门,屋里没有开灯,文静正坐在床上看电视,两条腿盘在一起,怀里抱着一袋豆类零食。她显然是在等我,但想不到我会这么快回来,正把一颗零食往嘴里放,看见我进门来,愣了一下,顺势把那两根指头也咬住了,侧着脸看我,样子很调皮。我走过去坐到她旁边,抚着她的头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电视的荧光下五彩斑斓。她做了个笑模样,甜甜地问我:“回来啦?”
我点点头,依然看着她。她又问:“要不要开灯?”
我说不要,这样挺好。我把手从她头上滑下来,抚摸她光洁的脖颈。她低下头,喃喃地说:“你要是什么也不做,我怎么好收你的钱。”
我说你急什么,我这不正打算做嘛。她伸手打了我一下,把脸从头发里抖出来说:“讨厌,拿人开心。”然后我们就纠缠在一起。
天知道我们竟然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在一起打闹,我们互相挠对方的痒痒,叽叽咕咕地笑着,像一对笼子里的鸽子。真到听到有人敲门。
一刹那我们像断了电的机器人,被敲门声定格住了,其姿势滑稽至极。我仰面朝天,探身摁了一下门铃对话器,外面问:“先生现在要晚饭吗?”我看看文静,她两臂撑着身体伏在我头上问:“你饿吗?”我说不,她说:“我也不。”然后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冲着对话器喊:“No,Go!”然后我们又扭打在一起。
平静下来后,我打开了灯,想赶走那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文静伏在我的胸口,像阳光下一团正在融化的雪。她低声问:“你喜欢我吗?”我说,嗯。我装作不经意地捉住她的左手,依次吻着每一根半透明的手指。我看到她的手腕上果然有一道疤痕。
“假如这女孩是为我割腕的,我会怎么对待她呢?”我陷入遐想。文静显然觉得有点异样,她抽出手来,在我的胸脯上摩挲。我问她:“你们这里的客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有钱人!”她随便地回答,“有不少是像你这样的公家人。”
“都是公款消费嘛?”
“可能是吧,反正出手都比大款阔绰。”
我想不到她竟然用了“阔绰”这个词,这不是一般的小姐会用的形容词,于是我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同时我感到她惊悸般动了一下,抬头盯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学生?”
“猜的。”我与她对视着,想从那眼睛里发现些什么。
她的眼神亮了一会儿,渐渐黯淡下来,叹了口气说:“不说了,反正我是个不错的女人!是吗?”
我不干休地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做小姐?”她瞪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在大学时就陪客人赚钱了。只要不让学校知道就没事。”
这种事我也见过,并不十分惊奇,于是微笑着问她:“你谈过恋爱吗?你这么漂亮,一定有很多人追你吧。”
“当然啦,”她有点骄傲地说,“但我从没爱过任何人,跟他们玩玩而已。”
我忍不住刮了一下她的鼻头说:“你说谎!”她有些慌乱地强辩:“没有,我做小姐是为了生活得快乐一点,并不是感情受了挫折。”
我抓起她的左手举到眼前问:“这是什么,你的手天生有条疤吗?”她想挣脱,但力气不够,只好认输说:“好吧,我承认,我被人抛弃后割腕自杀未遂,心灰意懒,找不到活着的快乐,就做了小姐。”
我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她说:“当然是在学校的时候,那个男的是个高干子弟,玩腻了我,又跟别人好去了,还诬赖我有精神病,我一气之下……”
我看见她有些神伤,就打诨说:“你床上功夫这么好,换了我,一定舍不得离开你!”她羞从中来,说你这个家伙真坏,抡起另一只拳头打我。我一把捉住,想把她两个腕子捏在一起。突然,我的眼前电光火石般一闪──她的另一只手腕上也有一道疤痕!
我猛然想起那位老妇人的话,文静曾为这里的一位客人割腕,如果这不属于小姐的表演项目的话,她先后两次为了爱情准备放弃生命了。我不知如何是好,把两个带伤的手腕并在一起仔细地审视:它们是那样的相像,像工笔线描的两道细细的红线,隐隐约约地陷在半透明的皮肤里,惊艳绝伦。
文静挣扎了半天,抽不出手腕来,急得眼圈都红了。我放开她,把她的头抱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世上真有你这样的女孩子,要是为了我,我会一辈子把你当宝贝。”
我显然触动了她的隐衷,她开始抽泣起来。我紧紧地抱着她,仿佛这是我千年修来的奇缘,我开始考虑怎样永远地拥有这遍寻不见的稀世珍宝。
等她稍稍平静了,我捧起她的脸,像哄孩子一样给她拭着泪水。我温柔地望着她问道:“你愿意跟我走吗?”她显然没听懂,傻傻地看着我。
我用目光逼视着她说:“你愿不愿意离开这里,跟我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她很凄惨地笑了:“你别开我的玩笑了,我够惨的了。”
我翻身从我的口袋里摸出那张卡,递在她手里说:“这里是十万块钱,你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永远离开这里,找一个安静的小地方住下,过一种实实在在快快乐乐的生活,你愿意吗?”
她有点受宠若惊:“让我考虑考虑,我连你的名字还不知道……”
我激动地说:“不用考虑了,难道这种生活你能过一辈子吗?我看得出来,你跟我一样不快乐,为什么不离开该离开的地方呢?说吧,说你愿意。”
文静显然被我感动了,她小心地观察着我的眼神,渐渐地相信了我,最后轻轻吻了我一下说:“我愿意,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她胸部剧烈地起伏,显然激动万分。
我说我恨不得现在就离开,但是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不过明天早上一定要走,我一秒钟也不想多待了。文静同意了我的安排,把那张卡还给我说:“你先收起来吧,我身边还有些钱,我们明天路过我存钱的那家银行,全部取出来带走吧。”
我说:“有多少钱,要不也办上一张卡?”她说不用了,就三万多。于是我们彻夜未眠,搂在一起商议定居到哪里比较合适。黑暗中我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快乐的光彩,像两个梦中的人物。
从此,我们都将成为生活的当局者!这是多么让人振奋的事情。半夜里我们趴到窗台上看星星,像一对真正的情侣那样──原来夜里也有阳光在闪现,我怎么从未发现过!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从从容容地吃过早餐,把车钥匙交给翘鼻头保管,告诉她我们去散步。文静软软地偎着我,与她的姐妹们招手告别,我们在大家客气的微笑中走出玻璃门。
砖蓝色的清晨让人听觉灵敏,我们并肩徜徉在干净透明的阳光里,一切都在为爱情存在着,为一夜情的延续一生辉煌着。我们迎着太阳走,像一对金色的璧人,一对爱情的鲜活标本。
路过银行,为使别人不起疑心,文静一个人进去取钱,我站在街对面的广告牌下等她。阳光渐渐驱散晨蔼,我周身涌动着兴奋的潮水,一种偷到王冠般的幸福和惊恐交织在一起,在这如水的清晨里荡漾。
然而手机响了。是家里来的电话,老婆在电话里用哭腔喊:“儿子病得厉害,你快回来啊!”我像个失忆的人被猛敲了一棒子,想起自己竟然还有个幸福的家。周身的潮水开始退却,初夏的朝阳冰凉冰凉的,毫无生机和暖意。
当文静笑靥如花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她急切的目光没有看到那个痴心的人微笑着站在阳光里等她──她在那个世界里永远找不到我了,我刚从梦中悠悠转醒,带着满心的歉意看着我熟睡的贤妻和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