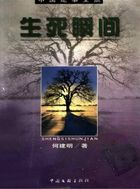那是一个木头镜框,檀紫色,里面有一个穿着红毛衫的女孩子站在草坪上,她的脸和身材充满了青春气息。教授用手指抹了抹玻璃镜面,说,是我女儿,小苋。我每次外出都带着的。教授的眼睛在上面停留片刻之后,很快地就又去翻转其他的袋子了。果真不错,一个又一个包翻了出来,可结果就是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教授本人的一些毛票,那还是他不久前去首都开会时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人家找回的钱,他当时就放在包里,现在还在包里,上面似乎还沾有着都市的气息。他把它们抓在手里一把放进了起初打开的包里,一个硬币还滚进了教授团在一起的裤头里面。教授已经懒得去理。在另外一个包里,我们看见一个白色的衬衣裁制成的袋子,袋子的表面已经发暗,白色上面还有黄色的污点,像是一道菜的菜汁。教授指着它对我说,这就是当初用来盛钞票的袋囊。现在袋囊还在这儿呢,钱却不见了影子,真是活见大头鬼呀。你说说看,真是活见大头鬼。其实当时教授在睡前脱衣服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过,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教授真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呢。事实上不是,他当时还拍了拍叠在肚皮上的这个白色的袋囊的。“这个妙招是你的师母想出来的,怎么样不错吧。”他当时还这么说的呢。我已经想不起来,这具体是哪一天了。只记得教授开始的时候将之贴着肚皮睡觉的呢。后来有一次我发现他的那个所谓的肚子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才明白教授已经不知何时将之作了位移。事实上,教授对我的防备实质上是对我的负责,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我来自农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万一我会冲动起来,这是有可能的。这为什么没有可能呢,这是很容易诱发人去犯错,甚至是犯罪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因此我恨不得当时是目睹了教授藏匿钱款的全部过程的,哪怕是偷偷地不为教授所察的情况下进行观察的也好。两个人的记忆力怎么也强过一个人的记忆力啊。
我看着始终是阴沉着脸的教授将一样样的东西折腾着,毫无办法。毋庸置疑,我们翻箱倒柜的结果就是一无所获,而天又下起雨来。
26
岑画家坐在屋子里,一动不动,他几乎每晚都独坐在桌前,凝神思索,然后猛地从座上起来,用笔在铺展开来的白纸上挥毫而作。这已经是他形成的多年的习惯了,窗外落雨的声音,使整个空间陷入寂静。他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有一丝丝痰音,他瞥了一眼桌上的香烟盒,还有几支在里面。他有点责怪自己刚才过于鲁莽,现在想起来,在他们面前过于那个了,他在心中责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再坚持下去呢,自己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了。他的烟史几乎先于他的学画史,他已经记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抽第一根烟的了。但他记得在岛上的东溪洗手的情形。那时他是狠下决心与那根根焦黄的手指告别了的。他当时瘫坐地上,反复打量着手指,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丑陋,骨节突出,上面的焦黄色使它们看上去好像长长的细石,他将它们插进了水流。而现在,这些焦黄色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乎无限透明的白色。这使他略感安慰,因为自己终于战胜了自己。自己战胜自己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这需要相当坚强的意志。而这些,他已经具备了。
只是现在,我将自己的长矛戳向了自己的盾,这样瓦解了。
瓦解了,他喃喃自语道,事实上一个人和自己战争到底是多么的不易啊。
窗帘还是那样拉着,他喜欢这样,整个房间里密不透风。他习惯性地看了看脚下,脚下的猫已经不在了,当时他上岛的时候,除了那些细软之外,唯一的活物就是一只波斯猫,起初,很喜欢岛上的日子,时间久了,这只白色的波斯猫几乎是他唯一的娱乐。猫的失踪使他此刻想来还是那么揪心。那是一只多么玲珑的小东西啊。他去囟簧采风回来后,就不见了猫的影子,去囟簧采风和去南岩买旧床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门,他基本上都是一直待在这个旅社里的。他的最大的活动范围绝对不超过旅社方圆一里路。而且这又是由于他寻找猫的缘故,如果不是猫的失踪他可能不会跑那么远下去,而一只猫,则有可能。他最后是在旅社东北方向的丛林里找到了猫的尸体,猫的尸体已经不全了,几乎只有半截,看过去像一个沾满了血污的手套扔在了丛林的草上。他伤心欲绝,就像他当年看见自己那个叫古燕娜的女人一样他向它奔了过去,草丛绊倒了他,他跌跌撞撞抱着半截猫的尸体痛哭流涕。他一直搞不清楚,猫是怎么出去的,他记得门是关得好好的。那些日子,他几乎有失常态,他的头发就是在那时候留起来的,岛上的人经常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在丛林四周游荡。那就是画家,他现在想来,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当时是太伤心了。
他的房间也是很少有人光顾的,这么多年来,除了景教授和那个张姓的学生,另外就是那个神秘的老女人,不过她并没有进来,只是在门口张望了一下,严格说来是谈不上光顾的。
另外对他的房间里有所了解的就是南岩的那几个男人,他们帮他将那张古老的床抬回了旅社,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就在旅社的门前,他们吆喝着将床卸成了数块。然后一块块的搬进了房间。画家的那只白色的猫和墙上的画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仅仅如此,他们后来回到了距此有十里之遥的地方,岑画家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再说,他此后一次也没有去南岩地带。
27
他敲门进来的时候,画家正在回忆燕娜,燕娜是他的模特,也是情人,死于一场溺水。1989年7月份燕娜的死最终促成了岑画家心灰意冷离开首都,来到了遥远的孤岛之上。当然这仅仅是众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古燕娜,他可能现在正活在京郊的圆明园艺术村中,然而他现在的情形使他没有感到不满,相反,他感到很满足,有时他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他迟了一步,他奔向古燕娜的时候,古燕娜已经横尸水上,在阳光的河面上有如白莲花盛开。他正在追忆自己当时正在干什么的时候,门被敲响了。小张探进来半个身子,脸色慌张。他说话显得吞吞吐吐,他说:
请—请——你过——来一下——一下,我的导——师——他——他——
画家跟着小张进了隔壁房间的时候,教授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他正笑着,看两个人进了门。他说话的时候,还很虚弱。房间里显得凌乱不堪,一个个包袋开着,里面的衣服也显得很凌乱,画家还以为是遭劫了呢。他笑着对半卧在床上的教授说,我以为,来了歹人了。
小张站在一旁,绞着手,不停地说,刚才可把我吓坏了,你那样子把我吓坏了。
刚才他的样子确实吓人啊,真的,他又对旁边的画家说。脸上的恐慌色彩似乎还没有消去,看他的样子,他刚才确实是吓得不轻呢。
画家在这个房间里坐了很久才离开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的画家已经将这里视如己家,而他们无疑是两个不安的旅客。我起初来的时候,也是跟你们一样,不太适应,过过就好了。这几乎是规律。他安慰小张道。小张现在已经坐到了椅子上。椅子背上的那个疤痕还很清晰,那是有人用烟蒂烙的。这里的寂寞是谁也顶不住的。他看到这苦黑色的疤痕心想。
小张是一个年轻人,岁数大概二十二岁。画家对他很有好感,他的肤色很好,他的脸上惶恐之色,画家觉得都很迷人。他记得他们初次接触是在厕所里,而且是通过语言。那时年轻人手纸用完了,而他的不适宜的粪便还没有完。他就是向他求助的,他在隔板的那边,看见年轻人的手,很纤细从板底档里递了过来,他的手细皮嫩肉。
他很有礼貌地在那边说,谢谢!
后来画家还给小张画过几幅素描,小张回到了落城后,将之拿给了落城铅笔画派的冯项看时,令他大为惊异。他很快就断定这是岑三变的笔迹。事实如此,岑三变由于在消失前因画风善变而得这一雅号,画坛几乎无人不晓。谁也想不到,当年的岑三变竟然就悄然入岛,归隐了山林。据说,后来有人不辞辛劳去探访过,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再也没有遇见过他。
画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想再次沉入对往昔的回忆中。其实,他几乎早已对这些淡漠了,就像镜面上的光,由于积年的尘埃漫布那样黯淡了。而现在,他想起了这些。说实话,对于那师徒俩,他的心中是怀有一丝感激的。因为由于他们的到来就像上天的手指抹过了镜子,尘埃被拂去,使那光亮显露了出来,将过去照亮了。
他看见了自己奔向了出事的河边,他跌跌撞撞地飞奔着,他看见自己的歪歪扭扭的影子眼睛不免有点湿润起来。
28
先生和他的弟子下车的时候,那个坐在他们对面的红唇女郎也下车了,他们两个人看见她拖着一个行李箱在人流中消失了。就像水消失进水一样。先生说,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而现在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看情形还是个不小的集镇。他们从车站出来后,在一家车站饭店吃了饭,车站饭店里人很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先生进门的时候,里面雾气缭绕,玻璃拉门的内壁上爬满了水珠。
他吆喝了一声,来两碗面条。可是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应。
学生跟在老师的身后继续往里走,过道显得很狭窄,他们时不时地还会碰到那些坐着吃饭的人的腿。那些腿就像旁逸而出的枝头,在他们的膝盖下部附近闪闪烁烁着,还有人嗷吆地叫出声来。然后是一两声咕哝的骂人声。
雾气中,那些人低着头忙着嘴上的活。仿佛很久没有吃了。
他们继续向内走,这个狭长的房间很长,通向雾气的深处。在那深处,先生和他的学生能够听见里面烹烧的声音。先生再次吆喝了一声,来两碗面。这时候,他们已经快要走到了顶头,雾气不断地从旁边的房间里喷薄而出,里面的操作间里人影幢幢,盆勺叮当。他的学生在他的身后向那门内喊了一声。
有人吗?——
先生看见桌子上的一张脸忙着的同时嘀咕了一句,废话,这都不是人吗。
操作间里好半天才有人应和了一声,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要他们先找一个位儿坐下来。坐下来再吆喝,啊。她的声音穿过雾气,来到了先生的耳朵里。
他们在中间的过道上搜寻着,终于发现在东北角上有一个空位。他们走了过去,放下了包坐了下来。桌面上还有一些骨头残渣,一些菜汁和米粒。先生对他的学生说,出来就是这样,这还算好的呢。
他显然在安慰学生,他怕学生不习惯。事实上学生却没有这么想过,他觉得很好,他向先生笑了笑说,没关系。
吃完面条,他们就去乘公共汽车了。公共汽车倒很准时,他们刚到那儿,车子就晃悠晃悠地来了。人很多,挤了半天。他们才像两个楔子塞进了人群的缝隙。
那时候,哪有这么多的人啊,中国人真是多,到哪儿都是这样。先生嘴里不停地嘀咕着,车上的那些人根本不在乎一个外地老头说了一些什么,他们表情显得很淡漠,视线像一只只苍蝇努力地飞向窗外的那些明亮的建筑上。
学生看得很清楚,他的脸朝内,他只能这样,有一个小姐的坤包塞在了她和先生的身体中间,先生动了几下,他感觉到了腰间的坚硬。小姐也试图努力将包从那个缝隙里拔出来,可是她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先生停止了身体的扭动,前面的人请他放自重点,这使先生一阵耳赤,在他的前面一个男人,从背影上可以判断他是一个魁梧的男人,他的身材略略高过先生,学生可以看见他的白色衬衫在外衣领的边缘上露出来的一条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