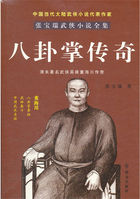65
我开始对教授热情感到十分紧张,他走东串西,一副非打听清楚不可的意思。我的劝说教授听都不听。他为了弄清楚这个事实,也就是昨天晚上杀人的事实,这几乎也是大家目睹的事实。教授显得很执拗,他敲开一个一个门,可是最后一个门一个门在他的面前关上了。他不停地问我,这是不是真的,实际上,他不必这么紧张的,这也是常见的事,只不过离我们不远罢了,以前我们也在晚报上见过不少,所不同的大概就是我们心情有所诧异吧,在晚报面前,和在几十米远的距离毕竟不一样。然而,教授的举动确实是令人费解的,因为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和他著作?和他的性命?在那一刻中,我相信这的确是一个好奇心足透的人。比我还过之不及呢。我开始的时候还向他解释得很清楚,这是大家都见到的,那时候,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插在尸体上的刀。清楚得很。但是半夜里,这些早就弄干净了,地面上再也看不到什么痕迹。餐厅里跟过去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疑点。或许他们半夜里就处置了尸体,他们处置尸体还不是很简单吗。这教授也不是没有见过,那对来到此一游的男女不就是被他们用一抔土埋了吗。我们还被迫参加了呢,我以为教授经过了那个事件后,见识大概长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忘了,或者其他什么因素。显然事实上,旅社方面是不想让人们有这个记忆从而认为这里没有安全感,而影响了生意的。现在正是个好时机,高朋满座,生意兴隆。谁愿意自己住在狼窝里呢。你这么打听,并不是什么好事,你这叫惹火上身。你看看那些人,他们为什么不说呢。就是因为这个,你打听干什么?再说,你要看什么情况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不清楚,我清楚得很。正由于我清楚得很,才不让你去干傻事,那绝对不利于我们的。你想想,其实你那不叫打听,好奇了。那分明是提醒人家,这里是狼窝,难道不是吗?假设旅社方面知道你在这儿作梗,是呀,现在大家都好好的,你这么着,不是作梗吗。人家知道了。说不定真跟你挂上钩了。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们往楼梯走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吗?他们说,睡你们的大头觉去,就当什么没有看见。说完,还将那把刀插在了桌子上呢。你不知道吧?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语气过于那个了一点,实际上我是担心你呢。万一你遇到不测我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交代啊。我毕竟是你的助手,您当初既然选了我,我就要对您负责。可是你又不听我的劝,这种事情知道的愈少愈好,偏偏你还去挨户似的打听。这不是把自己置于刀口上吗?实际上,我们还是作我们的事比较好,不要管得太宽。好奇心谁都有,看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有,不瞒您说,我也作过一些傻事。后来我停止了,不停止也是大麻烦。我想通了,就是现实毕竟是现实,这和幻想毕竟不同。而我,您知道,是一个幻想惯了的人。因此,我想或许这是我来此一趟最大的收获了。当然这要归功于您,没有您当初做出那个选择,也就没有我今天的选择。现在我们最明确的事实就是去做好手头的事情,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许是挑战吧,也许还算不上。也许早就是了。这些日子来,我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起初的时候,说得坦诚一点的,我当时是带有一丝庆幸的,就是自己有了一个幻想的地方,或者说时间,甚至可以依附的事件。你知道吗,我对您的经历也猜测过呢。那个时候,是有点庆幸自己有这么个机会,真是难得啊。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本来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就像地上的路,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关于青瓷蟒,你还记得吗?我和你一样是坚信她的存在的,尽管有的人说没有,甚至将我们视为疯子,或许是他们出于对那稀有动物的保护而众口一词呢,也说不定。这样一来,这些在他们的眼里是疯言疯语了。其实他们确实懂什么呢。他们又能懂什么呢?我们坚持就是真理,事实上,你有时埋头于学术了,似乎我们的事情已经忘了似的,我当然没有忘记,我很清醒,我只是寻机而动。你有时候是清醒的,不过很短暂,很快就又模糊了似的,当时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如果进行下去的话就必须先找到那一笔款子,这是必须的,有了它,我们才能有了基础,有了基础,我们才能又进一步地拓展。事实上,就是如此,而现在使我们摆脱困境的就是您的记忆,这最重要了,记忆。一个人的记忆。您必须反复地往那里想,往那个盲点,那个黑暗的地方想,你只有愈想那儿那儿就愈明亮,不想那儿就亮不起来,亮不起来怎么能看见那个蓝色布囊呢。当然,您现在的学术不能中断,在您的著述中间,也就是闲暇时光里您使劲去想想吧,啊。因为,这才是我们最终的希望,等看见了蓝色布囊,不就等于看见了希望,那时候,我们就离家不远了。说实话,我有点想家了,想校园的生活,我尽管嘴上没有和您说过,但是心里是惦念着的。不过话说回来,想归想,但是还总不至于坏了我们的事。我相信您。您的执着是最令我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向您致敬的地方。我有点激动了,言辞不当,还请您原谅。我主要是太担心您的安危了,才拉拉呱呱说了这么多。不仅仅是您,也是我,其实是大家的安危。难道不是吗?
66
张禹还是觉得自己是激动了,尽管教授不怎么在意他的言词。他的内心里还是隐隐地感到自己的过意不去,张禹觉得自己将在饮食起居上更好地照顾好教授,这才是一个有效地减轻自己内疚的途径。下午天终于撑不住了,开始下起了雨来。窗户扑拉拉地响着,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很快具有一股散不去的凉气,张禹在床边停止了他的写作。他看了看教授,教授已经埋头写作,情形很好,他的那种投入让张禹心里再次升起敬意。张禹挪开那个倒地的凳子,他原本想将教授的衣服找一件来披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无法去打开他的行李箱子。行李箱在床肚里露出一角,还可以看得见箱子把手上面的红带子。他是没有权利打开别人的箱子的。张禹知道这一点,这是隐私,即使再亲密的人,这一点都要注意遵守。他知道自己再不能增加自己的内疚了,从此之后,他所作的都应该以此为准则,应该深思熟虑,小心翼翼。最后,他将自己的那件牛仔服给他披上了。他从自己的行李包里翻了出来,尽管有点皱了,甚至还有点脏,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抵抵风寒,还是说得过去的。张禹将衣服终于披在了教授的肩上,教授似乎没有在意这点,他已经完全入了境界。他匍匐在桌上,几乎整个身体盖住了他的书稿,张禹一点也没有看清,一个字也没有看到。他笑了笑。
他离开了教授的身后,站到了窗前,窗户已经潮湿了,木质窗框上面沾满了大大的水珠。窗户的缝隙被风拉得愈来愈大了,甚至看见了窗户外的雨丝,张禹感到了一股凉风袭了进来,直接冲撞在他的脸上。他伸手想将窗户合得再严一点。
就在他伸手合窗的时候,从外面的草地上有一个穿雨衣的人慢慢地走了过去,他为了看清楚,将窗户掩了一些,张禹始终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究竟是谁,他慢慢地消失了。张禹看见草地上的一块块黄泥巴,显然那是那个人走路时蹭留在草上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张禹不得不将窗户猛地合上,两扇小小的窗户像士兵的脚一样狠狠地靠在了一起。风雨关在了外面。
张禹默默地坐了下来,他的脑海里盘旋着那个神秘的影子。
教授在盯着看他的时候,张禹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不是教授开口说话,他还以为教授一直在埋头工作呢。事实上,教授已经将身子从椅子上转了过来,脸早就朝向了发呆的张禹。你怎么了?教授问话使张禹暂时从自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
没有,没有什么。张禹感到自己内心有点慌张。你忙你的,老师,张禹说道。
张禹终于想起来了,他想起那个胖子的房间,在房间的东南角上,有一件雨衣挂在那儿的,长长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张禹决定自己去看看,他跟教授说了一声,他要出去一下。教授嘴里唔的一声,脸上还是很疑惑。张禹就当做没有看见一样,他走出了房间。走廊的灯已经亮起来了。
张禹还是用他的那个老花招,就像当初他寻找那个幻想中的通道一样,他对那个给他开门的人说,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了吗?
给他开门的人不是胖子而是一个剃着平头的瘦子。瘦子颧骨凸高,看着他,一脸狐疑。张禹正将视线从他的肩膀上漫过去,他搜寻着室内,仿佛他真有这么个朋友就藏在这间房间里似的。他为自己的猜测和表演感到很愉快。
张禹看到了墙上,那个钉子从墙面上露出来,钉子上空荡荡的。
那个瘦子似乎想起了什么,动了动他的高颧骨,说道,神经病,滚蛋。
张禹尽管遭到了上次一样的待遇,其实斥骂又算什么呢,他的猜测是对的。
门很有力地在他的身后关上了。张禹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房间内的人将画家押出了旅社。关门声似乎比上次还重,张禹感到自己的耳朵猛地一震。
他上着楼梯,他现在预备到房间里跟教授说一说,这是需要长一长心眼的。看得出来他们是有什么目的而来的。
来者不善。张禹边爬楼梯边想着这件事,他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词汇。
是的,来者不善。他小声地蠕动着嘴唇伸手推开了门。
67
胖子推开门,瘦子正在抽烟。胖子脱下了雨衣,将它挂在了墙上的钉子上。然后他挥了挥手,像是要赶走那些往鼻尖上飞过来的烟缕。
瘦子掐灭了烟蒂,对胖子说,那个神经病又来过了。
胖子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他问瘦子,哪个神经病?哪来的?
瘦子笑了起来,说,你看看,你这个脑子,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瓜,他的脑袋上头发齐竖,犹如立着的针芒。
那个来找朋友的家伙,这一次又是来找朋友的。
瘦子的提醒,使胖子马上醒悟了过来,长长的哦了一声。
哦——是那个家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瘦子看见同伴坐了下来,他的衣服上还有一点点潮斑呢。他盯住胖子的膝盖头这儿的潮斑说道,会不会这个家伙来打探我们的?
胖子说,按理不会,我们基本上还是比较注意行头的,按理说不会,那天晚上,出了那么个事情,我们也没有站出来管就是怕暴露了,再说,我们的目的是揪出那个家伙。
瘦子说,还是注意一点为好,我们快要抓到嘴边了,不要因此大意失了荆州。
胖子说,好的。好的。
然后他们开始压低声音说话了,胖子说他已经出去走过一遍了。
瘦子梗住嗓子问胖子情况怎么样。
胖子告诉他说,周围没有什么人家,看来还要跑远点看,这个天气最好,下雨,那些人都在屋里,万一白天出去,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自己的事情就不好办。还真是老天有眼,希望它再下个两三天。
瘦子一拍大腿,像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他站起来走到靠北墙放的旧木橱,他打开了橱门,将里面的包拖了出来,包顺带拖出了几粒黑色的老鼠屎,散落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