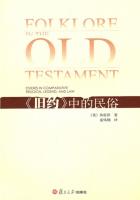孙昌武先生在其《中国佛教文化序说》的“序言”中对佛教做如下概括:“作为宗教,佛教具有一切宗教所共通的特征,那就是……佛、法、僧‘三宝’。”[5]](P.5)
方立天先生则在《佛教哲学》一书中精确地阐明了佛教的主要构成部分。“佛教是指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各国的佛教流派都声称崇奉三件事物:佛、法、僧。这三者被称为佛教的‘三宝’。三宝就是构成佛教整体的三大支柱。‘佛’,指佛教的创始者、祖师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指释迦牟尼传授的教理,实际上是包括释迦牟尼以及后代佛教学者所阐发的佛教教义,是教化、开悟众生的理论学说。‘僧’,指释迦牟尼建立的教团,泛指信奉、弘扬佛教义理的僧众。佛、法、僧包含了佛教的信仰目标、信仰理论和信仰群众,由此三者而展开为更复杂、更全面的系统结构,如由对佛的信仰而有各种礼仪制度,由法的演变而形成若干宗派,由僧众而有一切清规戒律等。佛、法、僧正式反映了佛教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简单地说,佛教就是由佛、法、僧三者综合构成的宗教实体。”[6]](P.2)
本文主要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从汉传佛教的佛、法、僧三宝角度分析其汉民族本土色彩的出现时间,以此界定汉传佛教的形成时间。
二、汉传佛教的佛、法、僧三宝特征形成于三国时期
笔者认为,最早在三国时期,汉传佛教体现在佛法、僧尼、佛像等方面的汉民族本土特征才全部出现,直到此时,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汉传佛教。以三国时期为界限,前后分别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两大阶段。之前为印度佛教在汉地有选择地汉化,并至三国形成汉传佛教;之后为中国佛教中汉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1.从僧尼角度来看
如前文所述,汉传佛教最显著的特征是信仰的民族以汉民族为主,汉族僧人出现应是汉传佛教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于汉民族信奉佛教的提法有多种。其一,即为郭朋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是楚王刘英,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是桓帝,而笮融,可说是早期信奉佛教的官僚‘居士’。”[7]](P.51)而楚王刘英、桓帝刘志、笮融等人都只是一般的佛教信徒,并不是事佛的僧人。他认为,汉代严佛调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出家僧人,并给予其极高评价,“汉代唯一的汉籍僧人严佛调,曾经同安玄合作,共同翻译佛经。”“对于严佛调这样一位在汉代佛教的初期传播中有所贡献,且有相当声誉的,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汉籍僧人,僧佑、慧皎竟均未为他单独立传,这实在不能不令深感遗憾!”[7]](P.49)其二,黄忏华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他说:“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的。”[8]](P.9)又说:“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8](P.12)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严格地界定“僧人”这一概念,而戒律是界定这一概念的重要标志。
戒律是佛教仪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传戒、受戒制度的佛教体制是不完整的。所谓“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就求戒的人说是受戒、纳戒或进戒”[9]](P.335)。早在唐朝,道宣就曾说过:“一方行化,立法须通;处众断量,必凭律教。”[102]“佛教建立在戒律上,戒律是佛教的基础,其他定慧等学,都是它的上层建筑。”[10]由此而论,只有真正受戒的人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僧人。也就是说“流传在中土的佛教戒律正是中国佛教汉化的基础”[10]。
事实上,佛教的汉化过程本身就应包含佛教戒律的中国化。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戒律在中国社会里进行了自身的扬弃,一些不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条文被淡化和搁置,同时一些适合中国社会的条文被推崇光大,甚至发挥出新意来,并随着社会的变演而有所发展。由于宗教信徒的行为准则及其实践决定着该宗教在社会中的形态,所以戒律在中国的推陈出新造就了有别于印度的中国佛教”[10]。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佛教戒律引进中国并逐步汉化是汉传佛教形成的重要基点,而受戒的正式沙门的出现则是汉传佛教形成的关键环节。
正如黄忏华所指出的“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三国之前,由于没有戒律,信徒出家的情况是比较混乱的。“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由此说可以推论出,东汉的严佛调并没有受戒,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僧。“到了魏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诃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循佛制,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本》,即摩诃僧祗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8]](P.11-12)
吕澂也认为中国真正的汉僧第一人应是朱士行。他说:“他依法成为比丘,与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11]](P.12)
据以上分析,中国流传戒律的最早时间应该在三国时期,在此之前没有接受戒律的汉僧。笔者支持朱士行是汉土真正沙门之始的观点,认为“严佛调乃是一位兼通梵、汉语文,既能助译又能撰述的最早的汉籍佛教学者。”[7]](P.47)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汉传佛教的僧宝特征,即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汉族僧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
2.从汉传佛教信奉的佛经角度来看
中国汉传佛教在佛经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以大乘经典为主。孙昌武在论述汉传佛教形成时说道:“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在中国传播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一方面,它按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调整了自己的面貌,依附于中国思想学术而取得人们的承认并迅速得到普及;另一方面,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突出了教义中的本土特征与新鲜内容。这样,在实现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建设起中国化佛教。”[5]](P.5、P.82)据此,笔者认为,孙昌武所论中的第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后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中,而第二方面则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佛典翻译的主要特征,三国时期即为汉传佛教法宝特征形成的初始阶段。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8]](P.3)“实际,中国佛教史,至少亦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始于永平十年后约八九十年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桓灵间,西域之译经师,相继东来中国,广事宣译。”[12]](P.12)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可以分为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安系”和以支娄迦谶为代表的“支系”。
“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他所译述、弘传的禅观之学,则可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佛学’。”“在安世高的译经禅学之中,仍然显示出了佛教初传时期的那种特征。”[13]](P.131)安世高主要翻译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小乘禅经。黄忏华说:“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观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8](P.6)“高所传译之经典,多属小乘,且以关于实际上之禅观修行者为多,罕涉理论。故世高者,小乘之学者,又小乘禅观之行者也。”[12]](P.3)吕澄指出:“从安世高的译籍见到的学说思想,完全是属于部派佛教上座系统的。他重点地译传了定慧两方面的学说,联系到实际就是止观法门。”[11]](P.4)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安世高一系的禅学,似乎并未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只有到了南北朝时的北方,同样也由于历史的原因,禅学成了当时佛教的‘北统’”[13]](P.131)。据上述分析,安世高所翻译的主要是小乘经典,而且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汉传佛教的僧宝特征并未体现在安世高身上。
支娄迦谶是与安世高同时代的译经大师。“他是第一位传译空宗经典,且重点在‘般若’的人。”[14](P.154)“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11](P.6)支谶译《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而“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实系《般若经》的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失”[8](P.3)。吕澂评价支谶所译经典时说:“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言译)’为标准。”[11](P.7)虽然支谶所译经典与安世高迥异,但其历史影响是相似的。“支娄迦谶译《般若》,同样是这种情况;《般若》思想,在汉代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到了魏晋之际(特别是两晋),却‘大放光彩’,到了了南北朝时,进而形成佛教的‘南统’。”[13](P.131)由以上分析可知,尽管东汉时期支谶已经突显了大乘经典,但并不具备很明显的汉族文化特征,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支娄迦谶的译出《般若》系经典,却也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进入了一个由汉代佛教的质朴无文而发展为大兴佛教义理之学的时代。所以,支娄迦谶的译出《般若道行经》,一方面,意味着汉代佛教的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佛教传播新时期的即将到来。”[13](P.137)也就是说,虽然支谶所译《般若》经典不具备汉传佛教僧宝方面的全部特征,但他为三国时期汉传佛教大乘经典居主导地位,并逐步在文辞、义理方面实现本土化做了准备,并“意味着佛教传播新时期”,即三国时期汉传佛教形成并得到广泛传播时期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