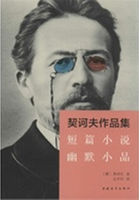9
黄松离开黄家坳那天晚上,黄虎手上提着一根短棍,带着两个愣头青,在复兴楼里里外外四处找不到他,最后黄虎把短棍往土楼墙上狠狠一戳,坚固的土墙硬硬地发出砰的一声,只留下一块浅浅的痕迹。
黄松从黄家坳消失了,开头几天还有人念叨着他,特别是黄虎到处找他,扬言要给他好看,但黄松就像冬眠的蛇一样,不知藏匿在何处。有一天晚上,黄世郎终于出现在黄松家的灶间里,正式地问起黄松的下落,黄莲和黄素只是摇头,黄槐说:“他又不是妹子,土匪不会抢他去当压寨夫人。”黄柏说:“他到外面赚了钱就会回来。”黄世郎沉着脸,显得很不高兴,每年都有人离开复兴楼到外面去谋生,但还没有人像黄松这样不辞而别,这后生子越发像他那个九叔了。几天之后,黄家坳人也渐渐忘记了他。浑圆阔大的复兴楼居住着三百来人,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对它来说,都没什么不同,太阳每天升起,每天落下,日子似乎都是相似的。
每天晚上睡觉前,黄龙都要在油灯下看书,最近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手抄的古药书,叫做《金匮要略浅注》,册页发黄,还有虫蛀、鼠咬的陈迹,但他看得津津有味,那端正的小楷字里似乎有魂魄附到了他身上,使他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妻子张良妹走进卧室,插上门闩,看到黄龙埋头看书的背影,像挂在墙上的弓一样,一动也不动,她故意弄大一点声响,他还是毫无反应。
“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啊。”张良妹说。她脱了外衣裤,上床爬进被子里,眼巴巴地望着丈夫的背影,忍不住又说,“考状元也不用这么认真啊。”
“你先睡。”黄龙头也不回,只说了三个字。
张良妹眼窝一热,全身钻进被子里,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心里委屈得直想掉泪。她是去年三月从张坑嫁给黄家坳的,都一年多了,她的肚子还没有动静。开头几天,黄龙一到天黑就向她使眼色,那是火烧火燎想把她往床上拉的欲望,可是没多久,他就对她冷淡下来了,最近迷上古药书之后,他更是对她熟视无睹,总在她睡着之后才轻轻地爬上床,碰也不碰她一下,有时她醒过来,用手去摸他,还会被他粗暴地推开。张良妹知道是古药书勾走了他的魂,有一天她在枕头下找到那本该死的古药书,想把它烧掉,又怕他跟她拼命,只能从发髻上拔出银簪,在发黄的册页上狠狠地刺了几下。
黄龙终于从药书上抬起头,把灯芯捻亮一点,又埋头下去,眼光在药书的字里行间慢悠悠地晃荡。他所置身的土楼,沉浸在安静的睡梦中,他身后的床铺上,张良妹翻动身子的响声,像老鼠从屋梁上爬过一样,他早已充耳不闻。
张良妹半夜里醒来,发现黄龙趴在桌上睡着,茶油灯还亮着,火舌几乎要舔到了他的头发。她又气又恼,爬起身一口吹灭了油灯。
“你吹我的灯做什么?”黄龙猛地抬起头,原来他没睡着,只是趴在药书上打盹。
“油不要钱呀……”张良妹气得说不下去,全身又钻进了被子里。
“你别来烦我,我想睡就会睡。”黄龙说,摸索着又把灯点亮了,他起身打开门,走到栏板下的尿桶前,丁丁东东撒起尿。
天井对面的那一间卧室也亮着灯,黄龙一下想起这是黄素黄莲姐妹的房间,她们这么晚了还不睡,在做什么事情?他很想过去看一看,但她们是姐妹俩共住一间,这就不方便了。十几年前,黄莲刚刚来到复兴楼时,还是一个挂鼻涕的小女孩,比她大一岁的黄素时常欺负她,有一次抓了一只死蟑螂放在她的头发上,她吓得哇哇大哭,黄龙快步跑了过来,从她头发上捡起死蟑螂,一边放在鞋底下研碎了,一边安慰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等下把黄素抓来揍一顿。从那开始,黄龙差不多就成了黄莲的保护神。年岁渐长,黄素也不会再欺负黄莲了,却是对黄龙颇有微词,有一次公开抢白他说,你喜欢黄莲,那你快娶了她吧,我看你这个傻妹夫真是傻到家了。去年黄龙结婚时,他意外地发现黄莲背着人抹眼泪,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黄龙的撒尿声像会传染一样,接连有人出来撒尿,给宁静的土楼制造了一些声响。黄龙回到卧室里,倦意袭来,便吹灯上床,呼呼地睡去。
土楼里最后一个睡不着的人是黄莲。黄莲一直和黄素睡同一间房,许多人家子女多,分配的房间不够,只好两个人住一间了。黄素白天风风火火的,像后生子一样,晚上一沾床就入睡,她的睡相也很男性化,两腿叉开,鼾声阵阵,本来就不大的床铺,她至少占去了三分之二,黄莲只能像小猫一样蜷着身子,在她的脚下躺下来。如果白天干的活多,累得不行了,黄莲也能很快睡着,但更多的时阵是身子疲惫,脑子里却不停地转着许多莫名的念头,全身上下像长了毛刺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就是这样,她也不知怎么了,眼前一直晃动着许多重叠的影像,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呼呼大睡的黄素踢着腿,差点把她踢到床下,她索性爬起身子,坐到桌前,把桌上的油灯点亮了。她发呆地坐了一阵子,走到对着廊道的窗前,撩起窗帘往那边的房间看,一眼就看到黄龙的卧室透出微弱的灯光。她连续几天注意到了,黄龙的卧室是土楼里最晚熄灯的地方,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她很想过去看一看,有一次还神差鬼使地打开了房门,走了几步才退回来。
黄莲听到了黄龙卧室前传来了丁丁东东的声响,在寂静的土楼里显得非常洪亮。床上的黄素突然翻起身,迷迷瞪瞪地打开门,走到栏板前撒完尿,像梦游一样回到卧室里,盯着黄莲说:“你怎么不睡觉?”
“我睡不着。”黄莲干脆地说。
“想哪个阿哥想得睡不着……”黄素嘟哝着,爬上床又立即睡了过去。
黄莲不由问自己:我是在想他吗?他都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还能想他?她心里一片茫然。
10
黄虎闯进灶间,叫了一声:“饿死我了。”黄莺正在洗着碗筷,说:“我以为你吃过了。”黄虎一看桌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急得瞪起眼,说:“我没回来吃饭,你们全吃光了。”他啪地拉开壁柜的门,里面也是空的。
“锅里还有点饭。”黄莺说。
黄虎一屁股在板凳上坐下来,比了一下手,说:“给我端上来。”
黄莺端上一碗剩饭来,说:“你很大啊,像老爸一样,我还要给你端饭。”
黄虎双手捧起饭,说:“我至少是你老哥嘛。给我来点霉豆腐。”
黄莺从灶台上抱起一只陶罐,用筷子挟了几块霉豆腐,装在小碟里放到黄虎面前,发现黄虎已经把碗里的饭吃完了,正用舌头舔着碗沿,不由惊讶地说:“你真是饿虎啊。”
黄虎把空碗递给黄莺说:“给我倒一碗酒娘。”
黄莺从地上抱起一只瓮子,把泥封的盖子打开,一股酒气就冒了出来。酒娘倒在碗里,红彤彤地闪亮着。她突然想起来,说:“对了,刚才老爸交代我对你说,饭后到他卧室去。我看你就别喝了。”
黄虎偏偏把头埋下去,啧的一声,就喝了大半碗,说:“老爸找我有什么好事?我先喝点酒壮壮胆。”
黄莺说:“等下老爸闻到你全身都是酒气,小心他打你。”
黄虎微微一笑,端起碗一饮而尽,说:“反正都有酒气了,干脆再来一碗。”
黄莺一把抢过黄虎手里的碗,说:“行了行了,你要被人打才甘愿是不是?”
一碗酒娘对黄虎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过既然父亲找他,他也不能多喝了,起身抹了一下嘴,就出了灶间往楼梯走去。
天黑下来了,土楼人吃过晚饭,女人们收拾灶间,男人们有的在天井里冲凉,有的聚在楼门厅一边剔牙一边闲聊。黄世郎吃过晚饭便上到四楼的卧室,泡一杯铁观音独自品尝,不停地咂着嘴,有时和躺在床上的妻子说几句话。这几年妻子黄杨氏患了头晕病,双脚一沾地就头晕目眩,整座土楼在旋转,只好整天躺在床上,每天喝下大碗大碗的草药汤水,这大半年来不见好,也没有更坏。长期不见阳光和卧床,使她看起来病怏怏的一脸苍白。
“你要喝一杯吗?”黄世郎说。
黄杨氏摇了摇头。
黄世郎端起茶杯,在嘴边轻轻地啜一口,脸上露出赞赏的表情,然后把杯里的茶全喝了下去。
这时,一阵拖沓无力的脚步声从楼梯口响了过来,黄世郎一猜就能猜到是黄虎,不由皱起眉头,他心里最看不惯后生子没精打采的,连走路也是软塌塌,这样还能做什么事业?
黄虎走进卧室,先弯下身子,问躺在床上的母亲“吃了吗”、“好一点吗”,然后起了身,双手垂落,一副老实相地站在父亲面前。
“今年多大了,你?”黄世郎淡淡地问。
黄虎屏着气,房间里草药汤的气味让他的鼻子有些发痒,忍不住抬起手揉了几下鼻梁。
“你不知道你几岁吗?”黄世郎的语气一下就严厉起来了,“我告诉你,二十,二十岁,流石公像你这么大的时阵,上山下田,犁地割禾,一个人就养了全家七八口……”
哈——啾!黄虎终于憋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连忙掩着嘴,诚恳地说:“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黄世郎脸色缓和了一些,接着说,“你二十也不小了,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今年中秋后、最迟明年就把玉华娶进门,我这几天请先生排排日子。”
黄虎愣了一下,说:“我、我不想这么早……”
黄世郎眼光立即像麦芒一样刺在黄虎脸上,说:“这事能由你做主?什么早,你流石公二十岁就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我们家当年和林坑的林家订亲,你娶玉华,黄莺配给玉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你们都到了时节,稻禾成熟了就要开镰收割!”
黄虎感觉心头痛了一下,好像父亲的镰刀从他心上划过一样。早几年定的亲,他心里不乐意也无可奈何。这大半年里,玉华时常放羊放到黄家坳的地界来,黄虎在山坡上见到她几次,第一次还是她先叫他的。黄虎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头一歪说,我当然知道啦。黄虎伸手想拉她一下,没想到,他的手还没伸过去,她却是受到炮烙一样尖叫起来,把他着实吓了一跳,他心里觉得很扫兴,很别扭。她说,你别碰我。黄虎说,你都要嫁给我了,还不能碰?她跺着脚说,不能碰!不能碰!黄虎就是在这时阵突然觉得不喜欢她,玉华在他面前一下变成索然无味的人。尽管那天他听说黄松调戏了玉华,还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想揍他一顿,但他心里对玉华却是越来越不喜欢,他甚至觉得她的鼻子有点塌,让人无法忍受。
“今天跟你说这事,只有一条,”黄世郎站起身,踱了几步,很严肃地说,“就是要你给我振作精神!结了婚,你就是大人了!”
黄虎心里叹了一声,说我当个小人好了,什么狗屁大人,我讨厌,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愣愣地点了一下头。黄世郎挥了一下手,他便得到敕令一样退了出去。
从四楼下到一楼廊道上,黄莺正从灶间走出来,看到黄虎懒洋洋的样子,扮了个鬼脸说:“被骂了吧?”
黄虎鼻子里哼了一声,脸上立即换了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黄莺转身向楼梯口走去,后面的黄虎叫了一声,她回过头来,说:“怎么了?”
黄虎说:“我想问你,你要说实话。”
黄莺抬起头看了看黄虎,他脸上一半亮着,一半黑着,像阴阳脸一样让人捉摸不清,她不解地说:“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说。”
黄虎把脸偏了过去,整张脸便在背光中,只有眼光幽幽地闪亮,他的声音显得低沉凝重:“你给我说实话,家里要把你配给林坑的林玉石,你喜不喜欢?”
黄莺怔了一下,这问题问得她措手不及,她只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不能违背,至于自己喜不喜欢,这似乎不重要,她只能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你给我说实话。”黄虎说。
“我真不知道。”黄莺说。
“我明白了,你是不喜欢……”黄虎说。
“不是,我没这么说。”黄莺说。
“那你给我说实话。”黄虎说。
“我就说实话,我不知道。”黄莺说。
黄虎微微一笑,笑得很奇怪,他转身要走,黄莺叫住了他,说:“哎,你问了我,我也要问你呀。”
“你问吧,我都给你说实话。”黄虎说。
“你不喜欢玉华吗?”黄莺说。
黄虎像是噎住一样,第一次感觉到说实话的困难,在黄莺目光的逼视下,不得不点了点头。
黄莺咧嘴一笑,突然模仿黄世郎的口气,拖腔拖调地说:“后生子,好好过日子,别胡思乱想啊。”
黄虎挥起手要打黄莺,她像泥鳅似的从他身边滑了过去,咚咚咚地跑上楼梯。举起的手无奈地落了下来,黄虎更是显得百无聊赖,啪哒啪哒地向楼门厅走去。
楼门厅的槌子上和大门的石门槛上坐着几个人,他们嘴里的烟头一亮一亮的。在复兴楼,每天晚上都有人带着守门的职责坐在这里,警觉地观察着土楼前方的动静,提防土匪偷袭。这是平时的状况,守在这里的人都是自愿的,不用指派,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习惯了。如果是收成时节,那就不同了,因为土匪最有可能在此时出现,土楼门前就要有人专门站岗和巡逻,由江夏堂宗亲会安排,每晚至少四名男丁,一旦有异常情况,立即鸣锣通知全楼的人,紧闭大门,将土匪挡在大门之外。
黄虎走到楼门厅,心想这么寂寞的土楼,要是有土匪来才好玩。他记不清上次土匪来的是什么时节,好像是前年了,采完油茶子的那天晚上,一股土匪偷袭复兴楼。他们从小竹溪方面摸来的时候就被发现了,迎接他们的是轰地关上的大门,巨大的关门声像是扇在他们脸上的耳光,他们身上的几把步枪根本就派不上用场,面对坚固的土楼狂叫一阵,最后只能往土墙上胡乱射了几枪,以泄心头之愤。黄虎记得那天晚上,他和好几个人挤在三楼的射击孔往下看着暴跳如雷的土匪,一个个放肆地哈哈大笑,心里比过节还高兴。
“阿虎头,看你走路像大蛇过田埂,有什么心事?”有人说。黄虎伸手向他要烟,他便把嘴里正在抽着的烟卷递过去,黄虎接过来猛吸了两口,心里似乎平静了许多。
“能有什么心事?想妹子了吧。”有人接着话头说。
黄虎没应他们的话,他们说的也对,他是想妹子了,可他不知道在想谁,反正不是想林玉华,林玉华就像篮子里的菜,不用想,他想的是面目蒙胧、叫不出名字的妹子。
有人抽的是旱烟管,在地上轻轻磕着烟管里的烟灰,叹口气说:“天天刮南风,明天又不落雨,地都要裂开了。”
11
一连十多天,天空晴得像假的一样,日头白花花地照得人发晕,田地里禾苗正在拔节、分蘖,一下被晒蔫了,地上像癞瘌头似的,湿一块,干一块。天不落雨,看来今年的收成有麻烦了。每天吃过晚饭,黄家坳男人就扛起锄头带着戽斗,走出土楼往田地里走去。
黄家坳的稻田主要集中在毛畲坡的南北两面,从坡顶上有一条水沟蜿蜒而下,因为久旱无雨,水流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