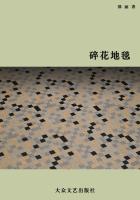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谢谢。”
“不要对我说‘谢谢’好吗?”
“好的,你慢慢吃吧,大专记得用功点。”
“我觉得你像在道别耶。”我停止吃饭。
“对啊,我要走了。”
“不会吧。”
难道必须短暂才能叫做“邂逅”吗,必须匆忙的瞬间才能成为永远的记忆吗?可能是饿了,累了,困了,思想也麻木了,所以只能专心的吃饭。我照例还是走到吧台买单,顺便问候了下老板的病情。
“你真是抠门,小气,没有风度。”
我还来不及做任何反映,榴莲小姐咄咄逼人的语言,劈头盖脸得往我身上攻击。
“啊……什么小气风度的”
“啊什么,人家美丽的小姐已经买单了,你一个堂堂大男人连这单也让小姐买,不是小气没有风度那是什么?”榴莲小姐教训起人来真的有我老妈的风范,真天生一副相夫教子样。
“是这位小姐深深地被我吸引,然后不可自拔地爱上我,最后要千方百计地讨好我,以便于能得到我的心,这不行吗?”我真惊讶这种没有天理的话我也能说出来,突然有一种杀人放火然后被通缉的心慌。
然后我逃了出来,很快地回到了家。
接下来我的生活的重心除了枯燥乏味的教学之外,还有为蝴蝶小姐完成一篇演讲稿,而什么大专、小专之类的只能算是电视剧里那些路人甲或路人乙,很难引起注意。
如果说教学是生活保证,那么为蝴蝶小姐写稿则是生活享受,至于考大专只能算是生活囚牢。这几天,蝶影小姐都会发短信来关心我的准备情况。我是个理智的人,虽然我对大专视如天敌,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吃药而让病情加深吧,换言之,蝶影成了我和大专之间沟通的桥梁。所以这些日子充实得像流感时的鼻塞,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自考的脚步声仿佛在耳畔回响,是那般的刺耳和恶心,就在自考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至少设计出一个放弃自考的理由。有些理由充分得像诸如“日出东方”、“花开花谢”等命题那样的不可质疑。不过,血管里流的血毕竟还是热的,已经有了随时就义的准备了。
的确,人生中有些事情根本不想面对,可越是不想面对就越是你不得不面对的,因此,周遭的环境才会充斥着这么多的无可奈何,身不由己。
宿命论的人,一定会说:这就是命运。
科学论的人,一定会说:这就是现实。
但,不管是命运还是现实,我们始终在生活着。不管这条路是如何的艰辛和曲折,方向总是向前的,不是吗?
最让我欣慰的是蝶影的演讲稿也已经完成了,该把这篇演讲稿命名为什么呢?这成了我此时的难题,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天王巨星成龙如果改名为“成虫”,会大红大紫吗;“邂逅餐厅”如果改成“找死餐厅”还会一如既往地人山人海吗?可见取名字是一门很讲究的艺术。
权衡了许久,我最后决定把这篇稿子定名为《满足》。至于原因,我不清楚,就好像我知道花会凋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凋谢。我只知道演讲并不是吟诗作对,不能把名字取得太诗意,但又不能太土。之前,我如果完成任何作品都不会露形于色的,如今区区一篇演讲稿的完成竟然会让我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吗?当然不是,因为我有了可以和蝶影约会的理由了。
就在我在选择哪一个黄道吉日去约蝶影的时候,她打来电话。
“睡了吗?”她依旧是这个开场白。
“我……”我只说一个字。
她又说道:“大专准备得怎样了,好像是这个星期六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安了,没问题的。”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撒谎,赶紧转移话题,因为只要说道“大专”两字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对了,演讲稿我已经帮你写好了,什么时候拿给你呢?”
“你寄颜老师带过来就行了,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我差点把演讲稿给吞了,本以为可以借这个机会约她吃饭,没想到被她这招“四两拨千斤”,震个内伤。
“里面有些问题和句子需要当面推敲一下,见下面会比较好。”我试着力挽狂澜。
“不用了,我可以的,你好好地准备考试,别让大家失望,知道吗?不要不在乎了,这次无论如何应该过关,不能再拖时间了。聪明的人不可以干愚蠢的事,有些路还是要自己走,别人帮不了你的。何况你以你的能力前面是一片坦途而不是荆棘。”蝶影说得像虔诚的观音。
我则像“古惑仔听圣经”一样,全听到刮风打雷,脑子里一片模糊。
“其实,应该要一起……”
我话又被蝶影抢着说了。
“好了,别说了,去读书吧,不要偷懒了。”
“我……”
“想说的,考完再说个够吧,好吗?”
“咳,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
“什么,你在念什么呢?”
“奈何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别再吟诗作对了,大文豪,我挂电话了。”
然后是冰冷的“嘟……嘟……”的声音。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像被抽光了魂魄,打开电视,又刚好看到2米26的姚明被一个小个子的三流球员盖一个大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的世界没有天理得一片漆黑。
裹上被子,合上眼睛,电话又响起,是蝶影。
“还在流眼泪吗?”她说。
“整个房间已经泛滥了,你说呢?”
“明天还有力气吃饭吗?”
“先问问我明天能不能看到太阳吧!”
“为什么?”
“因为水分快被我流干了,然后干涸而死。”
“喂,怎么那么大了还这样口不择言。”蝶影像是在教训。
“这个教训好甜哦!”连我都觉得这句话很恶心。
“恶心,那明天晚上有力气和我一起吃饭吗?”
“什么?”我兴奋得从被子里跳出来。
“我是问你明天有没有力气和我一起吃饭。”
“有,当然有,叫我去举重都可以,力大无穷啊!”
“房间还泛滥吗?”
“谁说的,我的房间春暖花开,阳光普照。我正在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还在……”
“好了,别恶心了,明天晚上七点来接我,赶紧读书去吧!”
然后是温暖地“嘟……嘟……”的声音。
毫无疑问,晚上伴我入眠的依然是这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五、约会
今天上班显得格外的有精神,校长还以为我嗑药差点拉我去尿检,连拖地、夹报纸这种芝麻小事我都抢在前面做。今天我的表现不只像个“四有”新人,连“八有”都够格了,倘若要让一个人大彻大悟,改头换面,不是叫他去信佛或者信耶稣,而应该叫他去信女人,而且是美丽的女人。
下班之后,我还是顺路去了邂逅餐厅询问了老板的病情,顺便和榴莲打了声招呼,便回家准备晚上的约会了。
说真的这次和蝶影的约会其意义和重要性绝不亚于1956年毛主席与尼克松在中南海那次划时代的会晤,所以这次的约会准备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吹毛求疵。出发前,我刻意检查下车子,以防万一在途中来个熄火什么的那就糗大了,然后启动车子往中南海,不,往蝶影家的方向。
这是她一贯的装束:一袭黑衣,长发披肩,略施粉妆,突然想起一句诗——淡妆浓抹总相宜。那只美丽的蝴蝶衔着一个发结,又在温柔地摇曳,明亮的眼眸是这个夜晚最璀璨的灯火。如果蝶影生活在唐朝宫廷里那么“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就不只杨贵妃了。
我们选择在一家叫“忘不了”的咖啡屋吃饭,因为里面典雅静谧的气氛犹如是蝶影身上散发着的气质。蝶影还是习惯坐在靠近落地窗的位置上。刚点完菜,蝶影就问我。
“大专准备得怎样,大后天就要考试了。”蝶影拿起装水的杯子。
“今天不谈政治好吗?”我拿起杯子。
“好吧。”她放下杯子。
“很好。”我也放下杯子。
然后我们对视几秒,察觉到彼此都没有要开口的意思,为了避免尴尬我拿起手机,她则把脸朝向窗外。其实不是开不开口的问题而是不知道说什么的问题,看到外面阑珊的霓虹,我突然来了灵感。
“不要看了,最美的霓虹已经在我对面了。”
“又在恶心了吗?”
“你知道吗,我此时的心情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你猜猜?”
“不会又是些感激、幸运等恶心的字眼吧?”她张大了眼睛。
“是恐惧。”我说。
“恐惧!”她仿佛是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下意识地站起来。
“是啊,就是恐惧。”
“那我是不是马上走开,来消除你心中的恐惧感呢?”
“如果你走开,我的心情也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什么?”
“绝望!”
“喂,小女子资质驽钝,请张大文豪指点迷津好吗?”
“你知道引起人与人之间纷争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吗?
“是嫉妒!”
“那你知道引起男人与男人之间纷争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吗?”
“是女人!”
“可以再深入一点,这个答案太广泛。”我说道。
“是漂亮的女人。”蝶影说道。
“那就对了,在这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伴随着我的是一只连女人都会垂涎欲滴的蝴蝶,人人得而爱之,纷争在所难免。所以我得保护你,但纵使我有超强的功夫也不免担心于这现实的十面埋伏啊。你说,这不是恐惧,是什么呢?”
突然蝶影的笑声弥漫整个咖啡屋,她说她曾很多次被人称赞漂亮,但这种拐弯抹角的称赞还是第一次,所以觉得很新鲜。
菜上来了,我和蝶影也默契地停止了笑声。
“很好吃。”我说。
“是饿了吧!”蝶影附和道。
大概是十分钟,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有一个同学她结婚了。”蝶影突然说道。
“那很好啊。”
“可是他们好像快离婚了。”
“不会吧!比好莱坞的明星还开放啊!”
“喂,我在说正经的。”
蝶影的脸突然严肃,我的心突然下起了霜雪。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问。
“大概是因为个性吧。”
“既然知道个性不和,为什么还会走在一起呢?”
蝶影突然停止了吃饭,脸朝向我说道:“可是结婚前彼此不知道啊。”看得出蝶影的情绪有些许的激动。
“两个成年人为什么会想不到结婚的责任与严肃呢?”
“你知道你问我几个‘为什么’了吗?”
“不知道。”
“三个。”
“然后呢?”我说。
“这正是我想问你的。”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答案。”我说得很直接和坦白。
看得出蝶影很失望,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婚姻这种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两个年龄加起来刚到半百的大孩子所能堪破得了的。
婚姻不是数学题,可以很理性地体现在几组数据的关系上。婚姻也不是语文题,可以很感性地体现在几组因果关系的句子上。
“在想什么呢?”蝶影问到。
“想你想的。”我说
“结婚那么痛苦,为什么偏偏得结婚呢?”
“药那么枯涩,为什么偏偏得吃药呢?”我反问蝶影。
“吃药是在治病,可以使身体健康。”。
“那结婚也在治病,可以使灵魂充实。”
“我突然想到张晓风说的一些关于婚姻的话。”
“说吧。”蝶影显得很迫切。
“就结婚的态度而言,这个世界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升华,因此结婚;另一种是认为爱情是一种必须的任务,所以结婚。就结婚的动机而言,这个世界也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认为结婚可以获得利益,因此结婚;另一种是认为结婚是种无名的责任,所以结婚。现实中有很多婚姻不是爱情在主导,有的人为金钱,为地位,为面子,为虚荣,但往往空虚了灵魂,背叛了爱情。一座几百平方的豪宅除了供你无聊的游荡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有些女人为了金钱却失去了自己期待的幸福,有些男人为了金钱却失去了赖于生存的自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
说完之后,我喝一口水,自己俨然成了爱情咨询专家。
“你经历过很多吗?”蝶影问到。
“应该说是我的书看很多,但在这方面我是个白痴。”
“今天几号?”我问。
“13号。”她说。
“两个月了。”我小声地说道。
“什么两个月了。”蝶影问。
“没有。”
“现在几点了?”蝶影又问。
“八点多了。”我说。
“该回去了。”
“不会吧,都还没有进入正题了。”
“以后再说好吗,我突然觉得好沉重。”
其实,晚上我们都没有吃饭。从她开始谈到她姐妹的事情之后,就很难再看到她的笑容。
也许是夏夜的风潮湿了蝶影的声线,刚才那清脆的声音已经消失了,坐在我后坐的她,突然有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感觉。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觉得后肩一阵冰凉,我没有回头,但我可以知道那是蝶影的眼泪被冷空气冷却成水滴渗入我衣服后的感觉。
我们在这条洒落着灯光的大道上疾驰,一直奔向远方,真希望可以一直延伸到地老天荒……
“先生,停车。”完了,是交通警察。
我刚反应过来。
抓钥匙、编号、牵车、开开罚单,动作干净利索。
“大哥,通融、通融吧,车先让我们开走,我明天再来交罚款,好吗?”我委屈得像窦娥。
“哈……哈……你也通融通融吧,车我们留着,你明天再来拿,好吗?”
“不会吧,我们新中国的交警都是慈悲为怀的吗?”
“难道有个人开着一辆车飞速疾驶,然后撞倒一个人,我们还要过去告诉那个人,说‘亲爱的以后开车要慢点,像这样撞死人不好的,知道吗’”
说完后,他将罚单递给我说道:“找辆车回去吧。”
“我是个教师,可以通融一下吧。”
“难道教师就可以骑着无牌车在路上嚣张啊,别说摩托车就是开法拉利也照抓。”
“我……”
我刚要说,蝶影一把拉住我说道:“还是回去吧,明天再一起来吧!”
“什么。你说什么,一起来?”我丝毫不相信自己。
“我是说我们再一起来拿车。”蝶影朝我笑了一下。
就这个笑容,别说是车被扣住了,就是人被扣住了,也是值得的,说不定是一出现代版的万祁良与孟姜女,因祸得福啊!
我叫了辆车让蝶影先上车等我,我又转向那个警察。
“你刚才和那警察说些什么啊?”
“我问他明天什么时候上班。”我把头转向窗外一脸坏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