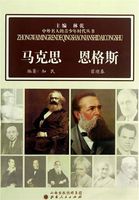吃晌午饭时菊仙倒在人家的麦秸堆上睡着了,郭玉芝可怜女儿,想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加上风大坡陡,山路难走,天黑以前赶不到借宿的村子。李发全指着不远处山洼洼里的一座小庙说:“咱们就到那庙里过一夜吧。”庙里有一个看庙的,俗称善友。正殿供着一尊菩萨,供桌上有香炉签筒,也断不了有人来烧香许愿、抽签问卦。这里的情况,李发全很熟悉,他认识看庙的善友,于是一家人就在小庙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郭玉芝说:“咱们求签问上一卦吧,看看在平顺能不能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李发全说:“你去求吧。”郭玉芝的本意是让李发全去,看来他不乐意,便双手按摸几下头发,抖起精神去找善友、拜菩萨。这时全部家当都已收拾停当放在禅院里,顺达和弟妹们守在殿门口等候。
善友念念有词,他们听见了:“脚踩两只船,进退两为难,要问翻身日,铁树开花时。”铁树开花这个比喻,乡下人也听说过,顺达有几分不服气,鼓励爹妈说:“铁树开花也不过是迟早的事。”郭玉芝也自我宽慰说:“咱已舍弃了东山底,脚踩两只船,已放跑一条船,就剩下逃荒这条船!到了路家口就开船。”……
李顺达一家人走走歇歇,一天只吃两顿红薯干。就在把所带红薯干全吃完的那天,一家人忍着饥饿,拖着疲惫的步子,在天黑时到了路家口。
顺达的舅舅郭双龙,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佃户,他有心把姐姐一家留下来住些日子,可是瓮缸里也舀不出多少米面来。
郭双龙四处打听,得知路家口有个人称二地主的郭召孩,他想转租平顺西沟的五亩二分坡地和三孔破土窑,便再三去求情,经过几次谈判,二地主看在都是姓郭的这份情面上答应每年出三石租子,把坡地和土窑转租给了李顺达一家。由于郭双龙力劝姐夫李发全重返晋城干他熟练的木匠活,租契上就写着李顺达的名字,十四岁的李顺达正式当家了。他二话不说,当起佃户,担负全家人生活的担子。
西沟就是半里长的一条石头沟,还有三条小沟岔,连李顺达一家才十九户,散居在三岔口、南沟、后背、北沟、磨石凹、水上、桑掌凹等七个小山庄。李顺达住的地方叫三岔口,算是西沟的一个小中心。他租的五亩二分地,分散在南山坡上。这里三条一耙宽的,那里四块尖三角的,大大小小竟有三十二块,有几分像他娘积攒下的布块。三孔破土窑,是圈过羊的,又脏又臭,一股子羊膻气。换上别人,也许会嫌弃,他们一家却满不在李顺达一家在3孔破窑洞一住就是25年。
少年当家乎,虽不懂得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人生哲理,但也懂得只要吃苦耐劳,总能让一家人不受饥寒。
李顺达把逃荒担子一放,就拾掇破窑。垒炕,砌火台,修理门窗,把他从爹那里学来的手艺都用上了,二弟富达和大妹菊仙,都是听他使唤的“小工。”郭玉芝进进出出,一边拾掇手头零碎活一边与来看望他们的人说话。
西沟十九户人家中,有十七户是从河南逃荒来的佃户,过去互不相识,一说起来就亲如一家。宋金山、王周则是两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们听说李顺达一家也是从河南逃荒来的,便把顺达当成自己的亲兄弟,担水的担水、和泥的和泥,放下扁担又搬石头,帮助顺达安家。
李顺达肯帮助别人,实实在在;别人帮助他,他也不会客套。就像刚才吩咐弟妹们一样,学着晋城工地老师傅们做活的架势,高喉咙大嗓子叫喊着:“来泥!”沉默寡言的王周则赶快铲起一锹泥,不声不响地送到李顺达面前。
李顺达又喊:“石板!”“来啦!”宋金山亮着嗓门答应一声,搬起一块石板“噔噔噔”一路脚步声朝李顺达跟前飞跑。
李顺达嘿嘿地笑着,感激地看了宋金山一眼。金山不像周则那样高大,可是他浑身都是劲。顺达接过石板,稳稳地盖在炕洞上,拣起两块小石片垫平。他正要喊叫来泥,王周则已把一锨泥送到他面前了。顺达跟爹到过几个县城,与不少工人在一起做过活,他觉得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走到一起互相帮助就是一家人。每逢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感到格外高兴,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他想起爹在东山底说过的话,便问王周则:“周则哥,这儿有这么多山坡,咱们能不能开荒种地?”提起开荒种地,周则就气愤不平,话语也多了:“荒坡石山都是有主的,不许咱们穷人碰一下,我家刚逃荒来到西沟时,看见这么多荒坡,以为只要肯劳动就不愁过日子。可是只在坡上刨了两镢头,叫老小子看见了,说这山是他家的,拦住大骂了一顿还不算,晚上把我哥叫到沙底栈村公所。村长、闾长都是替有钱人说话的,先吃拉面后评理,最后评了我家没理,还得给众人出拉面钱。我家没有钱,村长说先向老小子借上。老小子掏出五块钱,驴打滚的利钱。打那以后欠下阎王债,老小子年年逼债,我家年年还,总还不清啦!”郭玉芝听了周则的话,心头“咯噔”又压了一块石头:逃荒到平顺谋生,是不是又错了?顺达却想到另一边,他抱打不平:“这荒坡石头山,咋就能成了他家的?”“我和我哥也这样说。你猜人家咋讲?”周则双手叉腰,学着老小子的腔调说:“你们都是从河南飘来的草灰,这山是你们从河南背来扛来的?我就是当地人!”顺达又问:“老小子是个什么人?”“老小子是石匣的大地主,他叫张孝则,我们都叫他老小子。他说西沟的这些山和地,有一半是他家的,一年要刮走几十石租子。这地方山多石头多,是个苦地方,可是要没有那些地主老财霸占,咱们靠自己的两只手也能养活一家人。可这里地主说我们是草灰,只配当佃户。”顺达听到人家叫河南人草灰,只是无奈地一笑。河南人口多,不少人四处漂泊,居无定所,让外人讥讽为随风飘散的草灰。
他低下头一边做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山坡不是房屋,怎会成了他的?宁可让荒着长野草,也不让穷人刨开种庄稼!其实,这些地也都是穷人开出来的,有钱人谁摸过一下镢把儿!”顺达这几句话,引起了正在与郭玉芝说话的一些长辈们的注意,都回过头来瞧他。这时,一个猴脸尖腮的人顶着瓜皮帽大摇大摆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长条儿账本子,装成办官事的模样,斜起黑豆眼装腔作势地说:“新来的这一家姓什么?掌柜的出来说话。”李顺达一看他那架势,心里就很不舒服,他只管低头做活。一院子的人都不想答理,他又大声说:“听到吗?掌柜的叫什么名字?”宋金山碰了碰李顺达,凑在他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个人叫老秃子,住在沙底栈,因为西沟全是穷苦人,又与沙底栈是一个行政村,让他来当西沟的闾长,管咱们。”老秃子见人们对他冷冰冰,心里窝着火,凶神恶煞地扫视了人们一眼,盯着李顺达走来说:“嘟囔什么?要守规矩。我对你们说话,不听可不行!”李顺达没有停手里的活儿,也不看他一眼,有几分故意怠慢: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初来乍到,不知道你们的规矩。”老秃子反倒口气和缓了一些:“你就是掌柜的么?”“我爹出去了,有什么事就对我说吧!”李顺达从容不迫,很像个当家人的样子。自从离开路家口舅舅家那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要支撑起这个门户,替娘分忧,保护好弟妹们。
“明天一早,提一升米来支公差。来晚了要受罚!”老秃子连唬带吓说罢转身就走。
宋金山和王周则追上老秃子,拦住他说:“人家才来,还没安下家,就支公差?”老秃子打量着两个穷小伙子,刁难地说:“你们西沟十九户,挨门子派差,十八天轮一回,明天挨到他门上,他不去谁顶替?”王周则和宋金山同时说:“我顶替。”老秃子冷笑着说:“你们要顶替他支差,还有一块银洋的门头捐,你们也替他出!”说着便伸出一只手:“来,拿出来!”李顺达见老秃子难为金山、周则,便扔下手里的活计,大步走到老秃子跟前说:“我去就是。支公差做甚事?”老秃子打着官腔说:“给过往的官家带路,转送公文信件,碰上甚事做甚事,现在我也说不清。”老秃子一转身,宋金山就朝他的脊背唾了一口,向李顺达说:
“你别听他说得冠冕堂皇,像那样的公差一月二十天也遇不上一次。
支公差,就是给他家白干活儿。”李顺达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给他家白做活,还要自带口粮?
也太过分了吧。”宋金山提起这事就有气,无可奈何地说:“要不然,老秃子为甚叫派公差?明天是你,后天就挨上我啦,一天一个人给他家白做活。
当个闾长就这样压榨咱们受苦人!”“什么鬼世道!就是不叫咱们穷人活。他不叫咱活,咱偏偏要活!
立在石头上,也要生根站稳。”顺达的话语掷地有声,脸上却没有带出多少气愤,说着,又返回土窑里干活。他心里憋气的时候,做起活来就特别狠,二寸多厚的石板,他双手端起来在别的石头上一碰,就刀切一般成两块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郭玉芝把从路家口弟弟家带来的一些小米用粗布手巾包上,让顺达提着去支公差。自己又领着小儿女们安顿家里。郭玉芝是个有心计的人,她知道不论什么地方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横行霸道,穷人走到哪都不会有好日子,初来西沟的那份轻松又没了,可还是决心在西沟扎根熬受,死活也不再往别的地方挪窝了。
富达和贵达毕竟年纪小,还沉浸在新环境的兴奋之中。他们到山坡上割来两捆荆条,母子们坐在院子里编成荆条囤子,挨墙根摆着,再把囤子里面抹上泥,准备在秋后放粮食。贵达好学习,跟着别人认了几个字,他用心地在泥囤子上刻了“玉茭”、“谷子”等字样,用锅底黑描画着。
郭玉芝见孩子们那样天真地向往过上好日子,心里感到一阵酸楚。她担心今后的道路还会有许多坡坡坎坎。她在心里给自己鼓劲:
孩子们快长大吧,庄稼人与土地打交道,只要肯出力,舍得流汗,兴许能熬煎得吃上个肚儿圆。
原以为这里山坡多,能多开些地,眼下是没指望了。一家人只有在租来的五亩二分山坡地上熬煎。犁地没有牲口咋办?孩子们说:
“人拉犁吧!”于是顺达拉着一股绳,富达和贵达轮换着拉一股绳,郭玉芝把着犁拐子,开始为播种准备。菊仙带着四弟在地头玩,还要捎带挖野菜。种地不能没有粪,一家人起早搭黑拣羊粪。地里尽是石头子儿,一家人便整天蹲在地里拣石头子儿。做完自家的活,顺达还给别人打短工。天不亮就来到“短工市”上,手拄着镢把等雇主。雇主不仅以貌取人,还要判断哪个人厚道肯出力,就看镢头,哪个人的镢头大,就雇他去做工。顺达总是早早地就被人领走。
李顺达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没明没夜地在地里干活,在院里打了一眼旱井。饭前饭后有一丁点儿空闲,还要在院外栽几棵树。仅仅一两年工夫,不仅那三十二块山坡地变了一副模样,院里院外也长满了树,一片勃勃生机。就连窑顶上也长起了果树苗,那是顺达娘郭玉芝种下的桃、杏和核桃,如今也亭亭地长起来了。
天旱时,他还担上旱井里存的水浇地。庄稼也比别人家的长得好。这天,顺达刚从外边打短工回来,站在窑顶上望娘在哪架山上搂柴草,忽然看见老秃子又朝三岔口走来,便暗暗想道:黑煞神上门,又没好事!
他转过身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老秃子走上坡来,朝窑顶上喊:
“窑顶上干活的!派官烟喽!快下来交款!”李顺达粗声粗气地应答:“派什么官烟?”“官烟就是大烟,知道不知道?公家分派下来的,各家各户都有一份。”山西的土皇帝为了聚敛钱财,鼓励广种罂粟,用手中的权力摊派推销什么官烟。可是这个“官”字出在老秃子嘴里,很难说不是敲诈勒索。不过,李顺达反正是不买账的。他说:“俺家连小烟也不吸,要大烟做什么?”老秃子把胳膊一挥:“你吸不吸烟,公家不管,但烟款你得付。”李顺达知道,跟这种人有理也说不清,多说白费口舌,回答得挺干脆:“俺没钱!”老秃子哼了一声,伸直脖子喊:“你给我下来!没钱更得早给,这是官家的规矩,谁也不能违犯!”“没钱怎么给呀?”“我给你记在账上,驴打滚的利息。”李顺达双手叉住腰,挑战似的说:“我就要违犯这个规矩哩,你能把我怎样?”老秃子气急败坏直跺脚,李顺达脸上倒显出轻松的笑容。他来西沟这两年,见老秃子专门欺压穷苦人,对外来佃户更厉害,心里早窝下一肚子气。今天他成心要气一气老秃子。自己家是一担子挑来的,如果欺侮得不能在这里活下去,无非是一担子再挑走。不过,自己不会轻易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