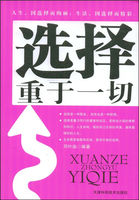房子落成后,又精心培置庭园。在培置庭园的同时,就把杨月娶进门来。天蓝得发紫,有许多温煦的感觉。房屋背后,那一岭赫然耸起的山脉,浓云一般贴在东边天上。一片一片的松林和青杠,枝枝丫丫,伸张得自在而得体,衬着天空,如高手弄出的剪纸,十分受看。
一楼一底的新居,就敛息在云影般的山下,与背景相协相生,颇有韵味。
总之他是这样感觉的。
他叫马波,也许住在江村的缘故,父亲给他取了个波字。其实父亲只是江村一般农民,无非会掌舵摇船、撒网放钓而已。父亲给他取名后不久就葬身波涛,便有人说,儿子取名“波”字,“克”父。
有人建议改过来,母亲想他父亲已死,再改何用?何况“马波”这名,挺洋气挺逗人。
母亲的感觉果然正确。杨月所以喜欢他,起码一半与“马波”这名有关。杨月与马波,天造地设。所有人听了,都首先表示一番如此之类的赞叹。
———杨月,快出来,看蓝花又出了一朵!
便有一声甜甜的回应,从楼上滴下。随即楼梯上吧嗒吧嗒的脚步响。一听就知是拖鞋。
杨月现身了,一头长长的头发,尚未来得及用手绢绾住。季节已入夏,却并不热,一大早,还有点微微的清冷。杨月穿连衣裙显然为时过早。不过是她早晨或上午的习惯,随手一套,简单明了,关在屋里,不觉怎样,下到园中,不由得收肩缩颈。杨月奔向那簇花间,看那刚出的又一朵蓝花。其实那是一簇十分健旺和野势的紫罗兰。杨月不肯叫花名,夫妻作一个别致的规定:只根据颜色或形状称呼花草。故而园中就分蓝花、红花、白花、黄花。当然,每一色中,又分深浅。比如白色,分雪白、粉白、青白;黄色,分金黄、深黄、浅黄等等。
他们一起议论花时,确有捉迷藏之感。
———那一大捧金黄谢了。
———又一朵深黄开大起来。
———我见一枝浅黄,颜色正在变深。
实在不知金黄、深黄、浅黄三种,是同属一株?或不同属一株?是同类?或不同类?
各人说各人的,各人领会各人的。杨月觉得有趣,马波完全赞同。
如此倒给这小小庭院,罩上了一层似是而非的神秘面纱。二人毕竟都读过高中,并东拉西扯读过一些书籍,便朦朦胧胧觉得,有了这一重氛围反而更好,似乎有点悟着生活真谛的沾沾自喜之意。
庭园虽是新培置的,但一是主人精心料理,二是适逢春暖花开,便如领受仙气一般,三蹿五蹿,丛丛簇簇蓬勃兴旺起来。
几丝雨,几缕风,大大小小花蕾就鼓胀起来了。在星月的夜半,嘁嘁嚓嚓绽放开来。太阳一出,花光反射,陡然间姹紫嫣红,若彩云之降落。与这崭新的一楼一底,奶黄色涂料、透明玻璃窗的新居互相映照,确是气韵非凡。
这儿并非马波的老家。老家在大江中心的岛上。马波和人办厂赚了钱,成了十万元户,就迁到小镇背后的半坡上来,立了这幢新居,娶了杨月。
在女人上,马波还保留着学生似的清正品性和浪漫幻想。
杨月是三月前才认识的。那是初春,杨月着金黄色紧身毛衣,绷一条黑色弹力健美裤,身材颀长,线条凸出,楚楚动人。
使马波心摇神荡者,还是杨月给他的感觉,他无法确切道出来。总之当时杨月的沉静与寡言,不易觉察的微笑,使他感到神秘莫测,用江村的话说:落不透。马波的情感还没这样被激发起来过。于是狂热地恋起她来。
那时新居刚落成,庭院正培置。杨月之所以同意嫁马波,除“马波”两字与人配起来使她感到舒服外,另一半原因,就是这独处半坡的新居了。特别是占据了大半个半坡的庭园。其时庭园正草创中,杨月当然就参与了关于谋篇布局、栽花植草之类重要策划。实在是她感兴趣之事,因为这是建设她自己的家园。
及至繁花怒放,璀璨耀眼之时,杨月几乎夜不成寐,频频推窗倚栏,俯视花影。特别是月夜星光之下,更陶醉在花魂草魄之间,便也带入梦中许多奇异的景象。
杨月是城里人,父亲是一般工人,家居狭窄简陋,做梦也没想到,会来这幽绝静地度美日子。
那是下午,夕阳将落,二人厮守庭园。杨月看花、看草,轻风微拂,花叶颤动,目不转睛。马波却只看杨月。看她窈窕身姿,丰满的前胸,凸起的乳房,披垂的头发,红润的脸蛋。也是眼都不眨。
马波你看,那株红花,多鲜,只是……
哦,红花?———马波才回过神来。杨月转身看他,止不住掩嘴而笑。
你说只是……什么?
我说只是……你太眼馋了。
我有你眼馋么?
我是看花。
我也是。
花算啥?我比花好———杨月头一扬,长发一甩。
我那是比喻。
你那比喻太臭。我有个同学叫李晓平的,诗写得好,他才会比喻。他把女人比成柳树,多新鲜!
马波不吭声,有点不舒服。是杨月的整句话使他不舒服,不是味道。并不是因为杨月抬出了李晓平来。他不嫉妒人家。他只是觉得杨月话中有些不是味道的东西,朦朦胧胧的东西……
幸好夕阳完全落下去之后,抛射出的红光更浓更艳,把新居罩在红纬之中,杨月整个身体如披薄纱,给马波一种迷离的美感,马波便忘记了刚才的些许不快,又重新醉入对杨月的感觉中。
马波听说了许多关于半坡的故事,便于闲暇与杨月相伴时对杨月讲述。杨月当然想听。既是关于半坡的,就非听不可,因半坡与她已经相互依存了。
马波说,看见么,半坡左边,一道崖。崖下就是大江。有一个雨后的下午,两个男的来崖下垂钓。谁知经一夜雨水侵蚀,崖畔泥土松动。松动着的泥土上面,正有一块巨石,便趁势落下来。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巨石滚下崖去,落入江中。待水花平息之后,垂钓的男人不见了,只有几截砸断的鱼竿在水上漂着。亲属闻讯,沿江寻访。好容易在下江十多里处,发现一垂钓人的尸体,早已泡得面目全非,只额上那块红痣为唯一标记。而另一垂钓人的尸体一直未见。
杨月听了,久久不能言语。嘴微微张开,似作无声之“哦”字状。
晚饭时,杨月食之无味。饭后,独步园中,面对那风中摇曳的花卉草木,似有凄然之情绪产生。尽管那尸体随江流而去了,仍多少与半坡有关。
下午,马波从厂里归来,见杨月坐底层正屋内,面对锦簇花团的园子,正读一本什么通俗杂志,便未惊动,独自上楼去了。
推开房间,不由得眉头一皱。明明有带电脑的高级洗衣机和自来水,一点都不费事,杨月偏偏让换下来的脏衣服码了一件又一件。并且,无论沙发上,床上,写字台上,都码着该洗的衣物。马波说过几回了,杨月仍不改这习惯。她不是不洗,而是一回回大洗,要积成堆了才洗。
唉,有什么办法。马波不愿过分唠叨,由着她吧,反正迟早她得洗。
只是今天有客人来家里,总不能这个样子接待客人吧。
马波便要动手去收拾那该洗的衣物。但又觉得不对,便将杨月喊上来。
杨月知是马波回来了,十分高兴,笑盈盈跨进屋。马波见她进来,便没说,低落头一件一件收拾那些衣物。
杨月站在一旁问:今天回来这么早?
今晚有客人来。
我很高兴。客人来,热闹些,比如那回那位姓张的,太风趣了。
马波眉头又皱。觉得杨月近来话太多。凡她听见有趣事,就毫不客气地介入进来,并且滔滔不绝。所以,近几天,凡有客来,马波尽量将话题拉到与厂有关的事情,其他闲话不讲,免得杨月兴趣来了又滔滔不绝起来。他不愿意杨月是这个样子。
晚上7点,客人来了,是一位酒糟红鼻子的矮胖男子,四十余岁。杨月帮着泡了两杯茶后,就出去了,以后再没到客厅来。马波起初还挺高兴,后来久久没见杨月,不禁奇怪。这时,他和酒糟鼻的正事谈得差不多了,就打开彩电,让客人看着,自己趁出去小解的机会,找到杨月。
杨月仍在楼下正屋沙发上看小说。
马波问她怎不上来。杨月说不想上来。
马波说怎不想上来?杨月说那客人长得太丑怪。
马波无言以对,就自个上楼去了。
庭院里花开得灿然极顶时,马波忽然听说了半坡这地方真正的故事。起初,他并不怎么在意。他是个男子汉,并且还是个比较开通和现代化的人,怎么会计较那些事呢?
但那些事总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特别是在走回半坡新居的时候,就要想起那些事;或是睡在床上沉默而未入眠的时候,也要想起那些事。
于是他看见一个姓袁的帮会头子,终于在峨眉山被抓住,用铁丝穿了肩锁骨,牵了回来,就在这半坡上,三枪才击倒,雪白的脑髓流了一地。还有许多地主乡绅,被打烂脑壳后,在半坡随便挖个坑,就埋了。
这半坡,原来是如此去处。难怪一直空着,无人来修房造屋。
就是说,他这新居,是建在掺和着脑浆的泥土上。那些花卉,长在许许多多尸骨上……
总之不是味道,总之不是那么舒服。总之闲暇时一想起,就有些郁郁不乐。
杨月问他,怎么不高兴了?
马波便哦一声。
杨月说,有啥不愉快的事,说出来嘛!
马波又唔一声。
杨月就生气了,说马波有啥秘密瞒着她,便伤心。
马波就问,你怕不怕死人?
杨月惊恐地看着他。
马波又问,你晚上敢不敢走坟地?
杨月哭了,说马波你有意吓我,你好狠心,你到底是啥用意。我好害怕,好害怕。
一边说一边往屋里退。离开大门越来越远。
马波急了,便说我闹着玩的,和你开个玩笑。我不再说这些了。杨月才止住哭泣。
那一夜,杨月睡觉的时候,紧紧地抱住马波,生怕什么东西窜进屋来了。
当然,第二天也就没事了。
花开得正好,杨月喜滋滋地请来个照相的,给她照了十余张彩照,几乎全是站在花丛中照的。
马波也在家里,他也因杨月高兴而高兴。只是时常要想到花下的泥土,那是掺和了许多脑浆的,泥土下面还有尸骨。
他这房子是承包给别人修的,不知当初凿出多少骨头来,他全然不知。
于是,便将那红的花看成了血,一滴一滴的血、一团一团的血、一摊一摊的血。而白的花就看成骨头,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一堆一堆的骨头。而蓝的花黄的花呢,仿佛就是那些死人的眼珠子,却还在眨动;仿佛就是那些死人的心脏,却还没完全死寂。
杨月喊:马波你也来一张吧!
马波说,我不感兴趣。
杨月说,马波你总有些不大高兴是啥缘故?
马波说没什么。
杨月说,我不怕你有啥事瞒着我,甚至我不怕你抛弃我,我杨月知道自己的身价,还不至于跌落到没人要的地步。
马波眉头又一皱,心口就隐隐作痛起来。
一天,马波厂里无事,闲在家中。夫妻二人便在楼底赏花。有的花凋谢了,有的花盛开了。但所有的叶,都葱茏茂盛。
杨月又要马波给她讲故事。
马波就讲道:有一个姓袁的帮会头子,刚解放逃到峨眉山,后来,被用铁丝穿进锁骨押回,脑壳打烂,脑浆迸裂。
杨月问,在哪儿打的?
马波说,在这儿。
杨月惊问:在这儿?
马波说,乡政府那边吧!
乡政府那边有一片河滩。
杨月张开的嘴巴才慢慢合拢了。
又有一天,杨月又要马波讲故事给她听。
马波说,“四大任务”时,有个地主被处死,打第一枪,打歪了,打在肩胛骨上。那地主本是跪着的,站起来就跑。又打第二枪,打在后背心,看得见血冒。但那地主还在跑。最后一个当官的拔出枪来,连补三枪,脑壳就打烂了,脑浆四溅,只剩一截没有脑袋的身子,还往前跑。跑了好几步,才栽倒。
又有一天,马波正要开口给杨月讲故事,杨月就吼叫起来:别讲了!别讲了!!我不想听!一概不想听!不要老讲那些,把这庭园搅乱了。
马波嘴唇翕动着,终于没再讲,沉默起来。
没几个月时间,几乎所有认识马波的人都知道马波娶了个好看又耐看的女人。见了马波都要赞叹一句:马波你真有眼福,娶了个花仙老婆。
马波不得不礼貌地报之一笑。
他不能不报之一笑,马波是知书达理的人。
马波常常回江村去,毕竟江村是生他养他之地,并且哥哥和母亲还在江村生活。
他回到江村,以羡慕口气和他说话的人就更多了:马波你老兄真不错。马波你娃儿真不错。马波你老弟真不错……马波你独占一片土地,修了幢那么漂亮的楼房,还有漂亮的庭园,又讨了个观音菩萨般的老婆,啧啧,福分不浅,福分不浅呀……好个马波。
马波没再说什么,不断地报之一笑,又报之一笑。他渐渐从内心深处高兴起来,嘴里似乎有了乐滋滋的甜味,绵长而悠远。直到回到半坡新居,马波也是心情舒畅的。
杨月见了,说马波几个月没见你这么天晴日朗的了,这才是过去的马波,马波就应该这样,有这么漂亮的庭园,这么鲜美纯净的花朵,还有什么不如意的?马波便拥抱着杨月,说杨月你真好你真好!就像这庭园和庭园中的花一样。
拥抱着,紧紧拥抱着,内心里喃喃自语道:别人都说好,我能不说好么?我真是……我真是……
眼泪就从他眼眶里涌出来了,沾在杨月乌黑的头发上,像早晨的露珠一般晶亮。
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