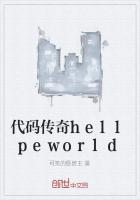在他眼里,村,如件旧衣,有了霉味。在他眼里,街镇,如领新衫,令人炫目。因此,在他眼里,去街时走着的那条路,是活的,活得长了翅膀,能飞。便早早的,拉了六指儿为伴,同去那活鲜鲜的路上扑腾。
早春,太阳好,刚出就融融的暖。
他在前。
六指儿在后面嗫嗫嚅嚅:“你有事办,可我……”
“嗨!没事我也要去的,不该上街新鲜新鲜?嗯?”
回头瞟瞟六指儿。六指儿便点头。
地气蒸发,原野上,有了些淡红的朦胧。勃勃的兴致更高了,想唱,又没词儿。
“六指儿。”
“嗯。”
“敢不敢出去跑滩?”
“干啥?”
“挣钱。”
“怎么挣?”
“像街镇东头王四。”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商行。”
“狗屁!还不是欺哄讹诈。”
“你怎么知道?”
“肯定是那样。”
这时转过竹林,见本村张二叔在路口休息。他便招呼:“二叔,走哇!”
二叔抹着额上的汗,只笑笑。
“来,我帮你挑。”
便上前。二叔感谢不迭。
“没啥,气力用了还会来。六指儿,帮我提兜兜。”
“不,我来提。”
二叔把兜兜接过去,跟在后面。
他最爱帮忙,在村人中印象颇佳。
他果真体健力大,只换一回肩,就到了渡口。二叔叫他放下,他没放,又径直挑上了船。
搁下挑子,刚要招呼艄公,一看———今日换人了。
不禁暗暗骂道:“龟儿子渡管所,一月不到,又换个人。”
管他的,照样。
便稳坐钓鱼台。
新来的艄公四十开外。开船前,挨个卖票。
“三分钱一个人,大家备零钱。”
他没理睬,昂头望对岸。仿佛看见对面花花绿绿的街面……
“买票!”
艄公的声音传进耳里。
“同志,买票。”
声音大起来。一看,才知是喊他。突然间,很感意外:怎么向他要起票钱来?这三分钱的渡口,少许特殊者都不会买票。历“朝”历“代”,他都努力跻身于特殊者行列。未料今日……三分钱事小,不被看重则事大。新来的艄公好像不吃他这套“坐功”,并且很有耐力,守在他面前就不移步。渐渐就有些抗不住了,毕竟理亏:“我……我……”
“请买票。”声音不大,却颇有威力。
“买就买!”哗一声掏出一把硬币,抛入艄公手中。
屈辱加愤懑。旋即,一个念头闪现。嗖地站起,喊道:“开船!”
便走到船头,抽起插杠,举起篙竿来。
那艄公见他帮忙,便有些和蔼,道:“小心点。”同时扬起船尾的篙竿。
常过河,都会舞弄船上行头。他耍得篙竿甚为纯熟。水不大,只中流有些湍急,和昔日的毛河大水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船入中流,只见他开头一篙,轻轻点了点河底。第二篙下去,却死死撑住河底不放。船借水势,越来越猛地逼压着篙竿。篙竿渐弯、渐弯,如弓,最后,叭嚓一声,断了。
艄公气急败坏:“你怎么搞的?你……你……”
“啥法?这篙竿不经用。”
呼一声将断篙竿丢在船头舱板上,回头对六指儿挤了下眼,闷声嘀咕道:“这才值三分钱么。”
六指儿才恍然大悟。
船靠对岸,昂头下船。留一倨傲相给那新来的艄公。心想:这下你该见识老子了!六指儿有意回头望了苦相的艄公一眼,既幸灾乐祸,又洋洋得意。
这三分钱的报复,更稳固了他在六指儿心中的形象。以至于他蹲在粮食市一个角落出售糯米时,六指儿也寸步不离。
“糯米,咋卖?”
不错,是问他。
“三角八。”他喊的是一般的行情价。
“有少么?
“你给多少?”
“要我给,就不好说。”
“你说来听听。”
“硬要我说?就只给二角。”
真他妈太抠人,几乎少一半。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只白了那人一眼。
那人却不走,说:“买卖么,就是要讨价还价才搞得成。你说说,到底少好多?”
他决心不理那人。
“这样吧,三角五。”
“不卖!”
“那么,三角六。”
“不卖。”
“好好,三角七怎样?”
他安心要气气那人,便对又一个来买米的说:“你还个价,我就卖。”
又一个人不解地看着他,顺口道:“三角三。”
“好,就卖给你。”
站起身,提起兜兜就称米去了,并不回头看那个给了三角七的人。
剩下的时间就属于他和六指儿了。哪儿去玩?先从上街走到下街。并不买什么穿戴,却也去那热闹的商店内转一转、看一看。
兴致勃勃地转过了,看过了,也议过了,便觉无味起来。走到一家餐馆门口,才想起该买点吃的犒劳犒劳陪着他的六指儿。
“吃不吃包子?”
六指儿嘿嘿直笑:“你吃我就吃。”
“对,各人来两个。”
一笼热腾腾的包子就在门口阶檐下。店老板无暇照顾这小买卖,忙乎里头大鱼大肉的大买卖去了。
便对里喊:“买包子!”
“一角五一个。把钱放在桌上,自己拿。”
他说:“买四个。”便把六角钱放在那里。一手揭开纱帕,叫六指儿先拿。
六指儿拿了两个,正要罢手,他悄声说:“多拿两个。”
六指儿看他一眼,立刻明白意思,果然又抓了两个,一起拢在手中。
离开餐馆后,二人边走边吃。他很得意,说:“反正他狗日的赚的钱多,不吃他吃谁?”
集镇太小,今日又没电影,实在没玩的地方了,便向街背后不远的火车站去了。
正一列货车停在那里。一看,是零担车,一群搬运工正从车上往下搬东西。东西有大件小件,都是各个地方托运来的。便和六指儿围着那些东西看。只见有衣柜、写字台、缝纫机、自行车、酒类、水果,还有一堆胀得圆滚滚的麻袋,不知装的什么。
六指儿摸着那衣柜,说:“做得好漂亮!是山里的好柞木。一定花了不少钱。我们要有一个就好了。”
“六指儿,踢它一脚头,你敢不敢?叫他狗日的拿回去好用。”
六指儿左右看看,摇摇头。他也左右看看。搬运工虽已去前面那个车厢下货,但用足踢的声音定能听见。便愤愤地用拳头狠抵了衣柜壁板一下。壁板只富有弹性地闪了闪,并没坏。
“有了,六指儿。”他又心生一计。
“啥?”
“你看,这是什么?”
“这叫货签。听说货主就凭这个来认领东西。”
“给他狗日的打个调。到时候,认个屁。”
六指儿说:“要得!”
于是二人便趁搬运工不注意,把自行车上的货签换到写字台上,把写字台上的货签换到酒箱上,把酒箱上的货签换到水果箱上……如此错乱一通。末了,他又把那些麻袋上的货签扯了好些张,揣在裤兜里,拉着六指儿,乐滋滋地走了。
他们沿铁路基而去。他在前,六指儿在后。走了一段路,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些货签来,先整整齐齐叠在一起,然后扯作碎片,团在手中,一把向旁边的夹竹桃丛扔去。纸屑出手,便满天飞起来,飘飘扬扬,扬扬飘飘,盘旋着,又回将过来,撒了他满头满身。他拍打着,咒骂着。六指儿见状,呵呵笑着。二人其乐无穷。
乡村公路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有卖甘蔗的。乘高兴,他又掏钱买了一根,一折为二,与六指儿各享用一半。
这良种甘蔗多汁,上下牙一挤压,凉丝丝的甜水便汩汩入喉,吞得他打嗝。甜水却还漫溢出来,沿厚厚的嘴唇滑落,点点浸入前襟。
呜———
火车来了。是快车。那绿色车厢正弯弯地滑过那一段铁轨的弧线。
“让开点!”六指儿说,“这东西太凶了,刮起那风。”
“妈的!想安安逸逸地走走也不让。”他愤愤地回过头来,逼视着弧线上滑过的那些窗口,“假洋盘,还把狗脑壳都挤在洞口上。六指儿,哪回我们也去洋盘一遭。”
“可我们,从哪儿到哪儿呀?”
他怔了,是呀,去干什么事?从哪儿到哪儿呀?总不能昏头昏脑上车、车到哪儿算哪儿。他不禁感到有点儿悲哀……
正这时,火车呼的一声从他面前扫过去,轰隆隆,轰隆隆,震耳欲聋。大地也在震抖。他想镇住自己,不动不抖。可是,他是站在大地上的,大地都在震抖,焉有他不震抖之理?
渐渐,他的视线,也因震抖而失了原先的笔直,那些一晃而过的窗口上,便出现了一张张似笑非笑、真笑假笑的脸子。那些笑,无论长与短、深与浅,全是针对他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便将手中吃剩的半截甘蔗,狠狠砸向那窗口。真巧,刚好砸在一孔窗口正中。一颗罩太空帽的头颅被击中,另一颗戴眼镜的头颅仓促缩回。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和六指儿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便齐声发出由衷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列车隆隆远去,只留那笑声不绝于耳。
在他眼里,回村那路,是死的。死得硬邦邦的,寂然无声。
六指儿在前,他在后。
转了一天,看了一天,乐了一天,他感到疲惫不堪,双腿似乎挪不动步了。
六指儿还稍有些精神。虽在前,但不远。
没对话,便沉默。
走着,六指儿掰着手指在计算什么。但那根附生在大拇指上的多余的指儿,却不能单独弯曲,只能随大拇指之曲而曲,随大拇指之伸而伸。
竹笼后,毕竟有几枝杏开花了。想不到那样的枯枝,居然也能冒出玉似的花来。
但只要是花,云霞便给它抹上些色彩,使它更美。
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