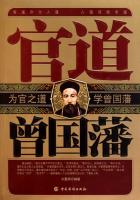中国是最早文对“人文”加以考察并得出这一概念的国家。儒家的“人文化成”观之所以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不仅是由于它从基本的原理入手,更由于它是对经验观察的一种抽绎与提升;儒家的“内圣外王”其实就始于对“人文”的认识。在儒家的经典文献《易经》中,早就开始了它对“人文”的特殊内涵与意义的关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人文化成”一语即从此段话中提炼而出。古时“文”通于“纹”,即纹理,是指交错而不乱的线条和色彩,同时又喻变化多样的修饰表现。进而言之,所谓“文”正是一种“符号”及其交错而成的形象;其实文化的开端,正在于符号及其组合变化之中。中国古人何以要通过自然纹理来喻指人为意义上的“人文”呢?《易传》如此解释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奥秘就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句,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与思考,从大自然的自身符号悟及“人为”符号的同构性及其意义,中国古人开始感觉并认识到“人文”的功能,因为人文符号可以成为真实世界的表征,通过符号,人才能认知历史与文化。这使中国古代的智者利用符号的人为建构来透视世界,从而使符号成为文化的最基本因素,这无疑为自己打开了人文意义世界的大门。钱穆先生也曾指出:“易经一书,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来探讨自然与人文之相通律则的。”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页。船山深通易理,亦深知仅言理言心,于历史文化终未为足也,故于人文历史各领域,广成其论,广构其说。对此,唐君毅与船山似心心相印,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故朱子之言理,阳明之言心,于论道德为足者,于论文化历史,则皆未必足。”而“王船山则不然,王船山之学之言理言心,固多不及朱子阳明之精微。盖犹外观之功多,而内观之功少。然船山之所进,则在其于言心与理外,复重言气。……船山言心理与生命物质之气,而复重此精神上之气,即船山之善论文化历史之关键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413页。唐君毅以其特有的洞察力透见到:善论文化历史之关键,除了须把握儒家心性义理,还须把握“气”论,尤为重要者是“精神之气”。以船山之深刻与广博,当得起以此气论而广涉乎人文化成之各领域者;这是唐先生
的结论,故其以“船山精神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一语概括船山,实为中的之论。
唐氏坚认:船山之所以力主乾坤并建,宗旨毕竟落实于宇宙人生历史之日新而富有之人文演变。他深中肯綮地阐述船山此论“如乾之既继坤以更起,而坤亦自寄于新起之乾。日新富有,相依而进,日生者日成,日成者亦日生,但有新新,都无故故,方可见此天地之盛德大业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此亦即人文化成之深义所在。更有进者,船山“缘是而其命日降、性日生之说,乃得以立,而更有其人之精神之死而不亡之义。”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死而不亡之义究何在?其对人文化成之大业有何意义?对此,唐氏自有卓见:
人之性命日生日成,其日新富有,相依而进,故船山又有死而不亡之义。船山谓人亡之后,其气或精神,非一逝而不还,恒能出幽以入明,而感格其子孙;圣贤英烈之逝,即以其精神,公之来世与群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此日生而日成,日新而富有;尤其是其气或精神,可大往大来于此世界,这真正造就了世间人文化成之大业。所以唐君毅极赞船山重精神上之气,即为船山善论历史文化的最关键之处。唐氏以人文化成之视角进一步阐释了船山所以重乾坤并建之旨:“船山所谓乾坤并建之义,乃谓此天地之健皆存乎顺,天地之顺皆存乎健;天地之阳皆存乎阴,天地之阴皆存乎阳;……与此阴阳乾坤之德,乃时在日新中,一切生人之命之性之德之道,亦时在日新之中,以益归于富有之实义者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日新而富有,合以成事业,有此理念乃有船山之精神,乃有船山精神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也。
更为重要者,是唐君毅极为出色而到位地论述了船山以一生学力凝结而成的“历史文化意识”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诚如其所言,此种历史文化意识的价值所在,能使“我之心量日宏,我之气得真浑合于天地古今之气,使我之为我之特殊个体之精神,与天地古今中其他特殊个体之精神,融凝为一,使我之精神真成绝对不自限之精神;然后我此心此理之为一普遍者,乃真贯入一切特殊之个体,成真正具体之普遍者也。斯义也,阳明朱子之哲学中,实尚未能具有之,而船山则深知之。”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所谓“具体之普遍”,实为黑格尔揭示具体真理与普遍真理关系时作出的一个新命题。而在唐君毅的眼中,船山与黑格尔不期然而同之“具体之普遍”,其最为紧要的精神实质即在以“我此心此理之为一普遍者,真贯入一切特殊之个体,成真正具体之普遍者也”。实际上,这也就是成就普遍的人文化成之大业的一个根本前提。此为船山亦为唐君
毅的根本理念。眼光之同、精神之同,此所以船山、君毅为不同代之大儒也!然而他们同为自己的时代注入了“现代”精神。
以此“具体之普遍”,我们便能很好地透入并理解唐君毅为何要极力倡言“所谓文化教育道德之进步,乃所以改进个人。”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没有个体便没有整体,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整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前提;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君毅、船山同具此现代性深识,然唐君毅更为深重的感觉当在个体基础上的人类发展之趋向,他似乎担忧这一趋向或路子走歪,所以他要说:“人类的精神之向外扩展膨胀,如吹胰子泡,在泡上花纹,次第展开,若兴趣无穷,而实际上内部之空虚愈来愈大。”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1页。据此,他大力强调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从而成为一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创造者与施与者,此处笔者想说的是,唐君毅所说“真正精神上的施与者与创造者”,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最好写照:
如何成为真正精神的施与者、创造者,我想还可有许多话可说,多少工夫可作。
吾思之,吾重思之,我相信,我们一切知识分子之病痛之免除,系于知病痛,而由反求诸己以互相赦免中,互相施与中,另长出一积极的通贯古今、涵育人我的精神,而此精神表现之形态,则不能全同于过去,而须兼照顾到由中西社会文化之相遇所发生之新问题的的文化要求。而且须转化一切由西方传入而表面与中国儒家思想不同而冲突的思想,以为展开儒家精神之用……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湾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258—259页。
处在现代的知识分子,要能真正“知”其病痛之所在,要能关照中西文化遭遇中的新问题,更要能创造性地“转化”不同思想,以成现代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