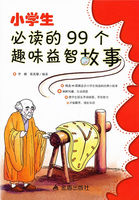那天夜里,大眼猴从农场逃跑出来以后,直奔天津卫。他哪里有什么做买卖的表哥,这都是为了鼓动小黑马开小差,顺口瞎编的。
到了天津,他就跑到一个叫王大傻的家里找李三麻子。那王大傻是三麻子的把兄弟,三麻子当不成乞丐头,就和王大傻合伙,在他家的地窨(yìn)子里,秘密地开了个赌博场,专门吸引附近一些不三不四的坏人,在地窨子里推牌九、打麻将、抽大烟……干坏事儿。大眼猴来了以后,三麻子很高兴,叫他白天出去偷东西,晚上,就给那些赌鬼、烟鬼提茶壶,跑跑腿儿。大眼猴觉得在这儿不用劳动,又不要学习,也用不着什么批评检讨的,倒怪“自在”。
有一天,大眼猴正在街上逛游,忽然听见有人喊他:
“大眼猴,大眼猴!”
大眼猴回头一看,原来是小黑马的妈妈。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袄,青夹裤。以前脑后吊着个蓬蓬乱乱的“纂(zuǎn)儿”(妇女的发髻)。也铰掉了,头发剪得齐齐整整的,上上下下,弄得干净利落,一只手提了个大包袱,一只手托着四串冰糖葫芦,在向他点头招呼。大眼猴心里暗暗想:“奇怪,这娘儿们儿变了!”就随口问道:
“周大婶,多日不见了,你如今在哪儿干事由呢?”
大婶子笑嘻嘻地说:“我在被服厂干活,给人做棉衣。你如今在哪儿呢?”
“我在农场。”大眼猴厚着脸皮说。
“你长生兄弟呢?”
“也在农场呀,我俩一直在一块儿。”
大婶子知道儿子的下落非常高兴,就说:
“来我家坐坐吧,来吃冰糖葫芦吧!”
大眼猴应着,他俩一前一后,转了个弯儿,来到一家朝南的两间小屋门口。那里面的一小间,窗户支了起来,窗口的架子上,摆了许多纸烟,大婶子的丈夫——独眼龙周宝成坐在窗口卖纸烟。大眼猴一看见他,就低声问:
“周大婶,我听说周大叔不是给他们抓起来了吗?”
“是啊。判了八个月的徒刑,放出来了,”大婶子微笑着,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欢,“你看他现在多老实,不打人,不骂人,酒也戒了,连纸烟都不抽了,成天守着这个小摊子做买卖,有多好,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要是早改过来,我家长生也不会跑出去要饭!这可怜的孩子,受了多少罪啊……”
周大婶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赶快让大眼猴在外屋坐下,拿冰糖葫芦给他吃;又打开那个大包袱,原来是趸(dǔn)的货,一条条的纸烟和一包包的洋火,都捧到里间,然后走出来问:
“大眼猴,你们是在哪一个农场干活呢?”
“在芦台国营农场。”
“哦,原来你们是在芦台国营农场啊!”
“是啊,我们在农场的青年队里干活。”
“那可好。青年队就是在我们被服厂定做的棉衣。今年你们都能穿上三面新的棉袄棉裤啦。你长生兄弟长高了么?身子骨结实么?”
“长高了,比我只矮这么一点儿。大婶子,我告诉你个话儿,你可别着急。长生兄弟病了,病得挺厉害!”
周大婶一听,可就是非常着急,忙问:“什么病,要紧不要紧?”
“这病啊,叫个什么‘胡拉拉’,肚子疼得要命呢。”
“那怎么办?我能去看看他么?听说坐一个多钟头火车就到了。”
“你不用去看,下了火车还要过几道河,走很远呢。他现在已经好些了,就是没钱花,农场吃得很苦,常吃不饱。他现在可瘦呢,瘦得一把骨头。”
当妈妈的一听,眼泪就止不住地淌下来了,越擦,越往外涌。大眼猴心里可乐了,他说:
“大婶子,最好你给他捎几个钱,让他好好养病,明天我就回农场,可以给你捎了去。”
“好!”周大婶一扭身回到里屋,和她丈夫嘁嘁喳喳商量去了。
大眼猴吃了人家两串糖葫芦还不够,趁主人不在,他自己动手,又拿一串吃起来,一面吃,一面东张西望。这屋子虽然小,可是收拾得一干二净,窗台上还养了一碟子绿葱葱的蒜苗儿,小桌子上擦抹得一点尘土也没有。忽然,他一眼望见桌子上放了个眼镜盒,他放下糖葫芦,轻轻地打开眼镜盒,里面是一副老花眼镜,这眼镜是周大婶戴的,她每天给被服厂做活,不戴上这副眼镜就看不清。大眼猴可不管人家的死活,他心想:
“这玩意儿还能值几个钱。”就偷偷把眼镜装在自己口袋里,仍然把眼镜盒盖好,还得意地想:
“不到用眼镜的时候,你总想不起打开盒子看看,嘿嘿!”
他又拿起糖葫芦大吃大嚼,好像没那回事似的。
周大婶出来了,赔着笑脸问:
“大眼猴,你明天回农场么?”
“我不是说过了,明天早车就走!”
“你和我家长生是在一个队里么?”
“不在一个队,我怎么知道他生病?”刁钻的大眼猴心里想:这娘们还不放心哩,我得拿拿她。说着,站起身就走,嘴里说:“我还要给农场买好些东西,忙着哩,咱们回见!”
周大婶着急地拉住他:
“别忙呀,你这是怎么着啦?说走就走!你和我家长生也是患难兄弟,你就一点也不关心他?”
“不是我不关心他,是怕你大婶子信不过我呢!”狡猾的大眼猴索性说穿了,故意激她。大婶子忙说:
“哪能信不过你呀!实在是……唉,攒一点钱不容易!”她掏出一大沓用猴皮筋捆好的小票子,说:“这是十万块钱人民币,是我和他爹攒了四个月才攒下的,托你捎给我家长生,叫他好好养病。你点点数吧。”
“不用点,错不了,我保证给你捎到!”大眼猴把钱收了起来。周大婶又叮嘱说:
“告诉我家长生说,如今他爹转变了,变好了,要不,哪舍得掏出这些钱呢。叫他别再和老头子斗气啦,收到钱,赶快给家回个信!……”
大婶子唠唠叨叨说了许多,大眼猴哪里听得进去,哼哼哈哈地应付一阵,就带着这一笔款子和那副眼镜,到小白楼下馆子,大吃大喝去了。
小黑马可苦了。
他到以前住过的小店,没有找到大眼猴;到劝业场、三不管、小白楼……也没有碰见他。要饭又很难要,人们总说:
“怎么现在还有要饭的!”
“小伙子,不瘸不瞎,为什么不劳动呢?”
“到农场去吧,那儿有活干,有饭吃,不比要着强!”
小黑马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说。牛大爷给他的饽饽早吃完了,嘴巴又不能挂起来,天气又一天天地冷了,他把老头捎给牛牛的夹袄穿上,也不顶事。每到夜里,他像个小狗似的“卧”在人家屋檐底下,冷得直打哆嗦……
有一天清晨,无情的露水打湿了他的单薄衣裳,把他冻醒了。他忽然想起了妈妈,一想起亲爱的妈妈,心窝里就热乎乎的。
“不论怎么着,也得去看看她!”
一想起这个念头,全身就像着了火,马上往家里跑,忘了饿,忘了冷,跑呀跑的跑出了一身汗水。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不走了。他躲在一根电线杆的后面,远远地望过去。支起的窗口后面摆列着一排排的纸烟,却不见一个人影儿。等了一阵,窗外来了一个人,窗口也出现了他那一只眼的后爹。小黑马想起他以前发酒疯,拿着棍子打他娘俩的情形,心里冒火,暗暗骂道:
“还卖纸烟呢,老不死的独眼龙!”
忽然,外屋的门吱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又反身把门带上。她穿着灰夹袄,青夹裤,剪发头,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子,蹙(cù)着眉,一脸的忧愁,低着头走过来了。呀,这是妈妈么?是她,可又不像她。小黑马的心咚咚地跳着,他的感情很复杂:又想迎上去,投到妈的怀里,痛痛快快哭一场,让眼泪把这几年的痛苦、委屈冲洗干净;又想远远地逃走,逃到深山野林里,一个人也不见。既然妈和独眼龙“相好”了,不要儿子了,儿子还要妈作什么……一霎时,两种矛盾感情在他小心眼里交织着、激战着。他脸色煞白,呼吸急促,贴着电线杆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
妈迈着小碎步,闷着头,竟从他的旁边擦身而过!
“是她没有看见我呢,还是故意不理我呢?”小黑马望着她的背影,痛苦地想,两只光脚板,不知不觉跟着她。跟她走到电车站,看见来了一辆蓝牌电车,看见她随着一些人挤上电车;上了电车,她似乎还朝这边望了望呢,难道她睁着两只大眼睛,竟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么?
小黑马望着那辆越走越快的电车,呆呆地站了好久,过路的人撞了他一下,他才慢慢地走开。走呀走的,脚步子越走越重,脑袋瓜子越走越沉,身上还一阵阵地打寒战,糊里糊涂走到海河边上,拣了个有太阳又不惹眼的角落,躺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