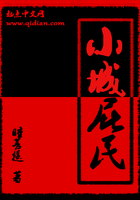自1927年本雅明提出巴黎拱廊的研究计划后,这一计划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几乎成为他后来所有论著的中心和出发点。1930年,他在给朔勒姆的信中写道:“《巴黎拱廊研究》……这是我的全部斗争和全部思想的舞台。”流亡法国后,他在1934年重新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1935年,他向迁到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提交了一篇提纲,以此申请资助。1937年,在得到社会研究所批准后,本雅明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可以说,正是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本雅明不愿离开法国和欧洲,乃至付出了生命。《巴黎拱廊研究》最终没有完成,但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中一小部分是1927—1928年做的)和三篇论文(包括1935年的提纲)。
为了《巴黎拱廊研究》,本雅明埋头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做了大量的笔记。其中既有他摘录的文字资料,也有他随时记录下的思考。这些笔记写在一张张的纸上,分门别类地放在一起。后人根据本雅明的编号分类,将这些笔记整理成900页的《笔记和资料》。其目录如下:
A 拱廊,时新服饰商店,店员
B 时尚
C 古老的巴黎,地下墓穴,破坏,巴黎的衰落
D 沉闷,周而复始
E 奥斯曼化,街垒战
F 钢铁建筑
G 展览会,广告,格兰维尔
H 收藏家
I 居室,痕迹
J 波德莱尔
K 梦幻城市和梦幻住宅,未来之梦,人类虚无主义,荣格
L 梦幻住宅,展览馆,室内喷泉
M 闲逛者
N 知识理论,进步理论
O 卖淫,赌博
P 巴黎的街道
Q 全景画
R 镜子
S 绘画,青春艺术风格,新奇
T 各种照明
U 圣西门,铁路
V 密谋,手工业行会
W 傅立叶
X 马克思
Y 照相术
Z 玩偶,机器人
a 社会运动
b 杜米埃
c……
d 文学史,雨果
e……
f……
g 股票交易所,商业史
h……
i 复制技术,石印术
j……
k 公社
l 塞纳河,老巴黎
m 闲散游惰
n……
o……
p 人类学唯物主义,宗派史
q 综合工科学校
从《笔记和资料》的目录,我们可以窥见本雅明的宏大构架。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的文学研究,而是一个视野广阔的社会文化研究。
在这些笔记中,“N”项具有特殊的地位,包含着本雅明的方法论和历史哲学思考,是理解整个研究计划的一把钥匙。早在1930年,本雅明在给朔勒姆的信中就写道:“对于这部著作,需要一个导言来讨论认识论,尤其需要讨论历史知识理论。”从笔记“N”看,他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阿多诺、霍克海默、柯尔施、杜尔哥、洛采等人的著述,并在这种对话中提出自己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渗透进已完成的论文中。
在已完成的三篇论文中,1935年的提纲概括了《巴黎拱廊研究》的基本设想。这个提纲的最初标题是《巴黎拱廊街:一个辩证的意象》,本雅明定稿时将标题改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他在给朔勒姆的信中把这一研究与《德国悲剧的起源》做了比较:“正如关于巴罗克的著作是从德国的角度考察17世纪,这部著作是从法国的角度考察19世纪。”“这里的重心也是展开论述一个原有的概念:如果说前者是悲剧概念,那么在这里将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他在给阿多诺的信中进一步解释说:“辩证意象不过是其拜物教性质被集体意识所领悟的方式……意识的内在性本身在19世纪表现为异化这种辩证意象。”也就是说,本雅明力图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的基础上,分析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所造成的扭曲的社会文化形态。
辩证意象是本雅明的一个主要分析范畴。他在笔记“N”中指出,辩证意象是“基本历史现象”。这是基于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历史的理解。他再三强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历史是辩证的“实现”;每一历史时刻都是对立斗争的角斗场。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线性进步观,因为对“历史进步”的盲目信念使得人们看不到在变迁和进步现象下的历史退步。他的研究具有现实针对性,即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威胁。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不是突然的退步,而是由“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所准备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中都有野蛮因素,今天的野蛮植根于过去,法西斯主义照亮了19世纪后期的历史。
本雅明把每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体系称之为辩证意象。他认为,文化符号体系是由经济体系决定的,但又不是简单地像镜子那样反映经济体系。这种符号体系既是经济体系的文化表达,又是每个时代的梦幻。它们既是幻象,但又不是纯粹的虚妄,其中也包含着被压抑的愿望,既有压抑因素,也有乌托邦因素。因此,他继续发挥关于历史沉睡和觉醒的观念,把这种文化表达的辩证意象说成是集体的梦幻意象。梦幻会被觉醒即辩证思想打破:“辩证思想是历史觉醒的工具。每个时代不仅梦想着下一个时代,而且在梦想时推动其觉醒。它在自身内孕育了它的结果,而且正如黑格尔早已认识到的,借助诡计揭示它。”资本主义时代的梦幻同样具有历史的暂时性。
就19世纪而言,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决定了其文化符号体系,从而构造了一个梦幻世界。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现象,欧洲由此再次陷入沉睡和开始做梦——导致神话力量的复苏。”但是在这种辩证结构中,无产阶级的觉醒将会打破这种梦幻—神话力量的统治。
本雅明认为,分析历史的方法应该是辩证法,而展示这种分析成果的方法应该是“文学蒙太奇”。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解不应“以牺牲形象直观性为代价”,“唯物主义的历史展示应该比传统历史编纂学具有更高的形象直观性”。其次,如同分析巴罗克时代一样,他认为同一时代的文化意象具有“相应性”(correspondence,一致,感应)和“特定的可辨认性”。这些意象总体上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辩证意象。他指出:“对于新的生产手段的形式——这个首先要涉及的问题仍然是由老马克思统治着——有与之相应的新旧交融的集体意识中的各种意象。”在历史著述中运用蒙太奇原则,对于本雅明来说,就意味着既要大量地展示意象,又要把各种意象拼贴在一起,万花筒式地展示19世纪的社会文化。
《巴黎,19世纪的首都》共有6章。前4章《傅立叶与拱廊》、《达盖尔与全景画》、《格兰维尔与世界博览会》和《路易·菲利普与居室》旨在展示19世纪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4种梦幻场景:拱廊,全景画,世界博览会和中产阶级的居室。
拱廊是19世纪“豪华工业的新发明”:钢架玻璃顶棚,大理石地面,吊在顶棚的汽灯,两侧排列着高雅豪华的商店。拱廊既是“奢侈品的交易中心”,又是钢铁建筑超越艺术的象征。
全景画是大型立体景观。它是艺术和技术的关系中的一次革命,也是新的生活态度的表现。全景画最初是试图把自然风景引入城市生活,后来在全景画中城市也变成了一种风景。全景画通过照相术也预示了电影这一现代梦幻的到来。
世界博览会是“膜拜商品的圣地”。它们制造了一个商品的世界,打开了一个梦幻场景,目的是使人们赏心悦目。
中产阶级第一次把居室与工作地点区分开。他们在办公室里埋头于实际事务,而要求自己的居室有助于幻觉。这种居室“不仅是个人的整个世界,而且也是他的樊笼”。
拱廊是以上4种梦幻场景的交汇点。因为它不仅是永恒的商品世界,而且是“室内和街道的交接点”,是集体沉睡的空间。
但是,梦幻中也产生出各种乌托邦。本雅明指出,傅立叶恰恰把拱廊作为其乌托邦法伦斯泰尔的建筑模式。这是因为傅立叶的乌托邦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基于抗议商品社会的不道德而设计的和谐的无阶级社会,另一方面它是力图彻底控制人的情感的、由人构成的机器。
在后两章中,本雅明试图展示19世纪的觉醒过程。
第5章《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表明,精神骚动首先发生在高雅的文学艺术中、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如同波希米亚人一样,波德莱尔式的个人知识分子在现代商品化的城市中找不到家园。他们犹如“闲逛者”。在刚刚步入市场经济时的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导致这些人的不稳定的政治地位,由此产生了职业密谋家。无产阶级真正领袖的出现结束了这种政治现象。知识分子又聚集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下。
第6章《奥斯曼与街垒》进一步描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精神骚动。第二帝国时期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主持改建了巴黎,旨在消除构筑街垒的条件,保证巴黎免于内战。他自称“拆毁艺术家”。巴黎公社则用更高、更牢固的街垒做出回答,结束了控制着无产阶级自由的那种梦幻,打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同资产阶级携手完成1789年事业的错觉。公社失败时巴黎公社战士纵火焚城是奥斯曼的破坏工作的结论。
总之,在本雅明看来,19世纪的巴黎既是梦幻都城,又是革命中心。知识分子的敏感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本雅明最后总结道:“巴尔扎克是第一个说到资产阶级废墟的人。但最早让自己的目光在这片废墟上巡视的是超现实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把前一个世纪的愿望象征变成了碎石,这甚至发生在代表它们的纪念碑坍塌之前……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我们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纪念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
巴黎拱廊的研究提纲——《巴黎,19世纪的首都》——得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热烈支持。然而,本雅明原想首先完成一个方法论的导言,批判荣格和克拉格斯的“原始意象”的观点,阐述关于辩证意象的理论,却遭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反对。究其原因,一种说法是,霍克海默认为这侵犯了社会研究所的另两名成员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研究领域;另一种说法是,阿多诺怀疑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
1937年3月,霍克海默在回信中建议:“(我们)早就需要有一篇用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如果你能首先写你的研究计划中的这一部分,我将极其高兴。”于是,本雅明开始埋头于第5章的研究和写作。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本雅明发现,这一章的内容不断地膨胀,可以形成一部专著的结构。他把这部专著定名为《夏尔·波德莱尔: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抒情诗人》,并且得意地声称,《巴黎拱廊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都汇聚在这里面;这是一部微型的《巴黎拱廊研究》。
根据本雅明给霍克海默的信以及本雅明的笔记,这本书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原标题为《理念与意象》,后改为《作为讽喻家的波德莱尔》。这一部分是艺术理论分析,将揭示波德莱尔的艺术理论的矛盾:在关于“自然的通感”(象征)理论和“对自然的拒斥”(讽喻)之间的摇摆。坚持传统美学观念的评论家关注的是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象征因素,“不加批判地赞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天主教因素”。针对这种倾向,本雅明打算论述“讽喻对于《恶之花》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讽喻想象是如何建构的”。
第二部分原标题为《古代与现代》,后改为《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这一部分是对波德莱尔作品内容的直接社会批判解释,将“展开论述作为这种讽喻想象的一种结构性因素的淡入—淡出效果。作为这种效果的一个后果,在现代性中揭示了古代性,在古代性中揭示了现代性。这一过程决定了《巴黎风光》”。本雅明强调,城市中的人群决定性地影响了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形象:“(首先)人群就像是闲逛者面前的一层纱幕:它是孤独个人的最后一剂毒药。其次,人群抹去个人的一切痕迹:它是被社会排斥者最新的避难所。最后,人群是城市迷宫中最新和最不可捉摸的迷宫。前所未闻的幽灵形象通过它镌刻在城市画面上。——诗人把揭示巴黎的这些方面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一部分要把波德莱尔的作品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展示波德莱尔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现代性特征,分析波德莱尔的批判及其局限。
第三部分原标题为《新奇与永恒》,后改为《作为诗人对象的商品》。这一部分将更深入一步地分析波德莱尔的作品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本雅明强调,波德莱尔的成就在于他对资本主义下商品拜物教的尖锐反应。“商品是波德莱尔讽喻想象的实现。”波德莱尔的讽喻表明:“所谓新奇的东西,即打破永恒体验——诗人在这种体验的魔法下陷入忧郁——的东西,不过是商品的光环。”在这一部分里将有两段插论。一段将探讨“青春艺术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波德莱尔关于新事物的观念。另一段将论述妓女作为商品是如何成为讽喻想象的最好对象。
总的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第一部分是艺术理论,第二部分是“资料内容”即作品意象的分析,第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论。
由于交稿时间紧迫,本雅明仅完成了第二部分《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这篇论文共有3章。第1章《波希米亚人》分析了波德莱尔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本雅明肯定了马克思的结论:19世纪的法国社会产生了一批“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为波希米亚人(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人群”。在本雅明看来,法国大革命后文人在社会中边缘化了,他们与以小酒馆为家的职业密谋家和沦落为流氓无产阶级的工人都属于社会的弃儿,有着相似的不稳定的社会地位、相似的行为方式。职业密谋家中发迹的路易·波拿巴与随心所欲、放荡不羁的文人波德莱尔构成了两个对立而同构的形象。波拿巴的政治活动总是保持着翻云覆雨、突然袭击的密谋习惯,而波德莱尔的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1848年革命后,当犬儒主义弥漫了整个社会时,路易·波拿巴走向权力顶峰,而波德莱尔只能走向市场,为商业化的报刊写作。
第2章《闲逛者》分析了波德莱尔诗歌的社会内容。在这里,本雅明特别强调了波德莱尔在19世纪大城市的人群中的“惊颤”体验。波德莱尔的“人群”体验既揭示了现代人在大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又反映了波德莱尔本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同样作为文人,“雨果把人群颂扬为现代史诗中的英雄,而波德莱尔则为他的英雄在大城市的大众中寻找一个避难所。雨果把自己作为公民放在人群中,而波德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个英雄从人群中分离出来”。
第3章《现代性》继第2章进一步分析了波德莱尔作品中的主体意识与现代性的关系。本雅明指出,波德莱尔本人并非“闲逛者”,而是以古代“斗剑士”的英雄精神挑战现代世界。但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渣滓提供了大城市的英雄”,“英雄便是用这种材料制造作品的诗人”。因此诗人在作品中扮演了“闲逛者、痞子、丹蒂以及拾垃圾者”等多种角色。与此一致的是,“他的技巧是暴动的技巧”。因此,“他把讽喻当作自己的心腹”;“在死神、回忆、懊丧或邪恶出现的地方就是诗的战略中心”。本雅明在论文结尾处把波德莱尔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布朗基联系起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布朗基的行动是波德莱尔梦想的姐妹”。
今天看来,《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中一篇开创性的论文。除了其论述方法外,在对现代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心态以及波德莱尔的分析方面,它都有深刻独到的洞见。
这也是一篇有着强烈现实针对性的论文。本雅明在写作时声称:“我是在同战争赛跑。”书中关于路易·波拿巴的描述及对其社会环境的分析,无疑影射着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精神漂泊和政治流亡使他对波德莱尔产生共鸣或者说有着较深刻的理解。当然,我们不能把他与波德莱尔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他所理解的)是本雅明分析的指导思想。他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斗争。
1938年9月,本雅明将《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寄给社会研究所。尽管他对霍克海默等人是否会有误解不无担心,但是当他11月收到阿多诺措辞严厉的回信时仍然感到意外。阿多诺在信中表示,霍克海默和他研究后一致否定了这篇论文。本雅明事先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说明这篇论文仅仅是整部著作的一个片段,仅仅是“资料内容”。但阿多诺仍然批评道:“各种主题被聚集在一起,但没有得到阐释。”“全景画和痕迹,闲逛者和拱廊,现代性和永恒性,都没有理论解释。难道这就是可以耐心等待而不会被其自身的灵韵消耗的‘资料’吗?”更重要的是,在本雅明的论文中“看不到全部社会进程的中介”,“你肤浅地把一种揭示力量赋予一堆资料,但这种力量从来不属于一种实用指涉,而属于理论建构”。阿多诺认为,本雅明在理论上根本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所以本雅明想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贡献,这既委屈了本雅明,也委屈了马克思主义。阿多诺代表社会研究所希望本雅明重写这篇论文。
本雅明在回信中对阿多诺的批评逐一做了反驳,但为了与社会研究所保持思想上的一致,他很不情愿地同意改写这篇论文。
1939年7月,本雅明寄出了修改稿《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简称《主题》)。与《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相比,尽管使用的资料有些相同,但这几乎是一篇新作。本雅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声称,这篇文章显示了“弯到最大极限的哲学之弓。而我痛苦地使之适应一种平庸的、甚至是土气的哲学阐述方法”。这篇文章“试图把我的关于(机械)复制的文章和关于讲故事的人的文章中的关键主题与《巴黎拱廊研究》的同类主题结合起来”。
《主题》一文是以“惊颤(shock)经验”为中心,揭示波德莱尔作品中所反映的个人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本雅明强调:“惊颤属于那些被认为对波德莱尔的人格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之列。”与《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相比,《主题》更进一步地指出,惊颤经验不仅是城市人群在个人心中引起的“害怕、厌恶和恐怖”,而且也是现代工业的机械化生产中的劳动经验:“行人在人群中的惊颤经验与工人的机器旁的‘经验’是一致的。”惊颤经验也决定了机械复制艺术的特点:“一种对刺激的新的迫切需要,终于被电影满足了。在一部电影中,惊颤作为感知形式已被确立为一种正式原则。”另外,《主题》第10和11节也运用灵韵理论阐明波德莱尔的艺术观念。
《主题》获得社会研究所的认可,发表于当年《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上。这使本雅明感到一些欣慰。1940年1月,他在给朔勒姆的信中写道:“无论我们所信托的未来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所发表的每一行文字都是与黑暗势力搏斗的一个胜利。”